- 2022-09-27 发布 |
- 37.5 KB |
- 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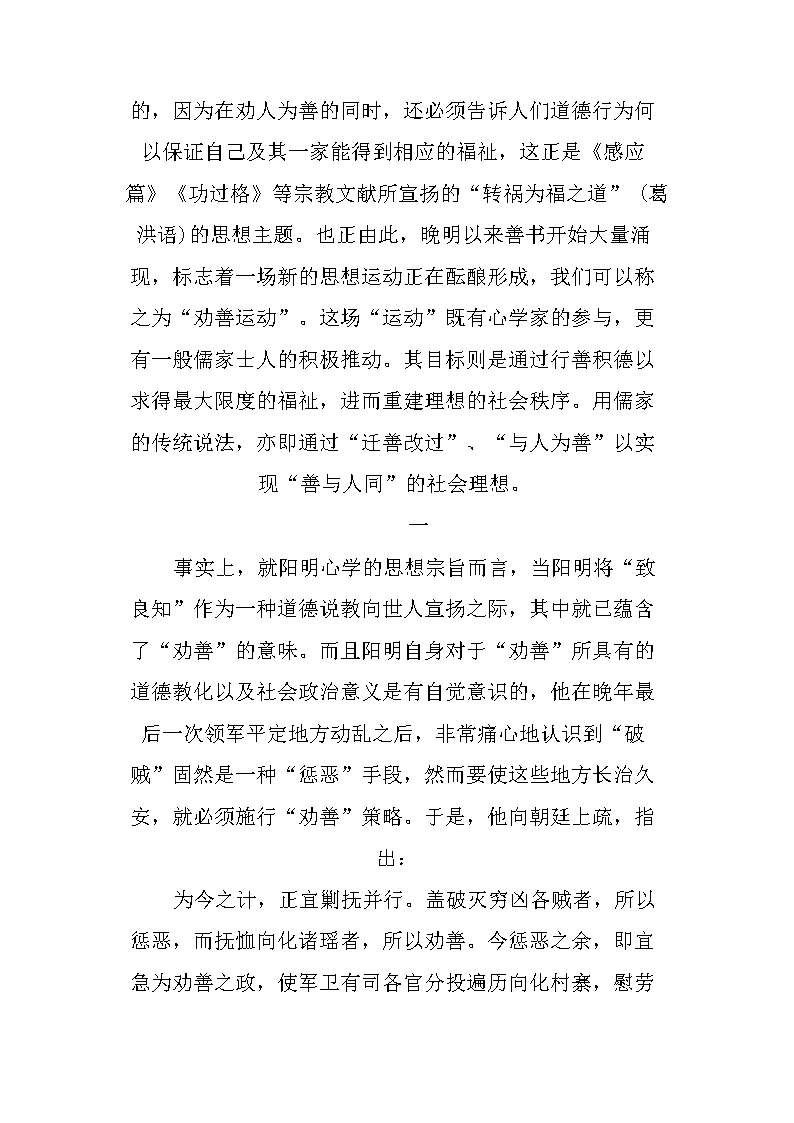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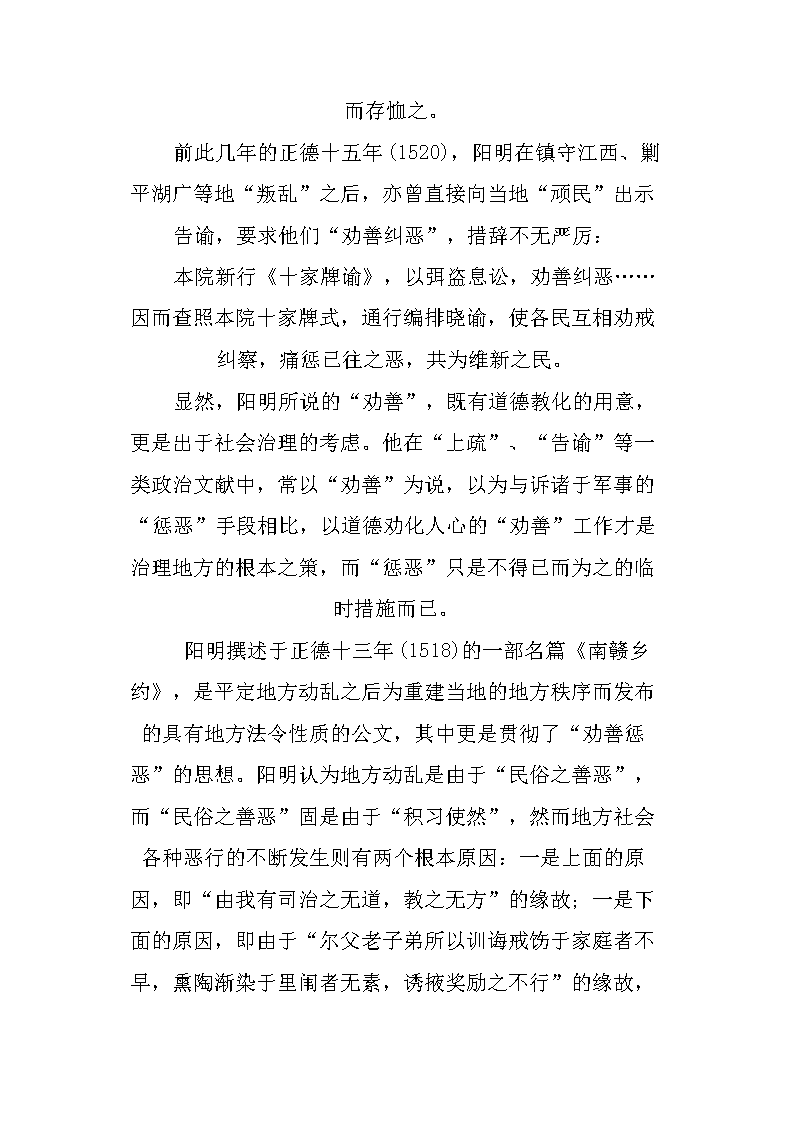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浅论阳明心学与劝善运动
浅论阳明心学与劝善运动 关键词:阳明心学;明代劝善运动;报应;德福一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ZX026);复旦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07FCZD018) 简介:吴震,男,江苏丹阳人,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知道,晚明时代以《功过格》《阴骘文》等大量善书的出现为背景,形成了一股“道德劝善”的思想运动,而这场“运动”是在16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阳明心学家所推动的心学运动之后而出现的。那么,阳明心学与道德劝善有何思想关联呢?其实,“劝善”是中国伦理学历史上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议题,尤其是自宋代晚期随着《太上感应篇》将“劝善”主题进一步凸显出来以后,逐渐在明代学术思想界受到关注,不仅在心学运动中,“道德劝善”是其重要内容,而且与心学运动相关联,大多数地方儒者士绅以及官僚士人都在关注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端正人心、整治风俗、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n 依心学理论,良知是内在的,所以每个人只要通过致吾心之良知就可改善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进而改善一家一乡乃至改善一国天下。然在晚明亦有一种思想观点认为,仅仅依靠良知内在这一抽象的心性理论是不够的,因为在劝人为善的同时,还必须告诉人们道德行为何以保证自己及其一家能得到相应的福祉,这正是《感应篇》《功过格》等宗教文献所宣扬的“转祸为福之道”(葛洪语)的思想主题。也正由此,晚明以来善书开始大量涌现,标志着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酝酿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劝善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心学家的参与,更有一般儒家士人的积极推动。其目标则是通过行善积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进而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用儒家的传统说法,亦即通过“迁善改过”、“与人为善”以实现“善与人同”的社会理想。 一 事实上,就阳明心学的思想宗旨而言,当阳明将“致良知”作为一种道德说教向世人宣扬之际,其中就已蕴含了“劝善”的意味。而且阳明自身对于“劝善”所具有的道德教化以及社会政治意义是有自觉意识的,他在晚年最后一次领军平定地方动乱之后,非常痛心地认识到“破贼”固然是一种“惩恶”手段,然而要使这些地方长治久安,就必须施行“劝善”策略。于是,他向朝廷上疏,指出:\n 为今之计,正宜剿抚并行。盖破灭穷凶各贼者,所以惩恶,而抚恤向化诸瑶者,所以劝善。今惩恶之余,即宜急为劝善之政,使军卫有司各官分投遍历向化村寨,慰劳而存恤之。 前此几年的正德十五年(1520),阳明在镇守江西、剿平湖广等地“叛乱”之后,亦曾直接向当地“顽民”出示告谕,要求他们“劝善纠恶”,措辞不无严厉: 本院新行《十家牌谕》,以弭盗息讼,劝善纠恶……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编排晓谕,使各民互相劝戒纠察,痛惩已往之恶,共为维新之民。 显然,阳明所说的“劝善”,既有道德教化的用意,更是出于社会治理的考虑。他在“上疏”、“告谕”等一类政治文献中,常以“劝善”为说,以为与诉诸于军事的“惩恶”手段相比,以道德劝化人心的“劝善”工作才是治理地方的根本之策,而“惩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而已。 阳明撰述于正德十三年(1518)的一部名篇《南赣乡约》,是平定地方动乱之后为重建当地的地方秩序而发布的具有地方法令性质的公文,其中更是贯彻了“劝善惩恶”的思想。阳明认为地方动乱是由于“民俗之善恶”,而“民俗之善恶”固是由于“积习使然”,然而地方社会各种恶行的不断发生则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上面的原因,即“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的缘故;一是下面的原因,即由于“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里闱者无素,诱掖奖励之不行”\n的缘故,因此为从根源上防患于未然,阳明指出: 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犀之俗。 他指明建立“乡约”无非就是为了“协和尔民”,同时也是为了推动互相之间的“彰善纠过”之实践,最终目的则是为了重建“仁厚”的一方风俗。 为了更有效地推动“乡约”治理,阳明还做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最具鲜明特色的措施是:“置文簿”三本,除一本为“名册”——即“会员”登记本以外,其余两本分别为“彰善簿”、“纠过簿”,实即善行恶行的记录本,这是为了“劝善规过”之用的,可见他的秩序重建的设想乃是以道德为核心的。须指出的是,阳明的这套“乡约”设计,对明代中晚期的“乡约”运动影响甚大,成为后世地方治理的基本文献之一。 令人关注的是,阳明的乡约设计不仅汲取了宋代吕大钧《吕氏乡约》中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宗旨,采用了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中立“记善籍”、“记过籍”的方法,并且吸纳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颁布的《教民榜文·圣谕六言》的内容:“\n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对照阳明《南赣乡约》所云,可看出除“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两条未被引用之外,其余均被阳明纳入“乡约”之中。 从明代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看,将《圣谕六言》与《乡约》相结合,以便进一步加强“劝善规过”的教化作用,应当说这是阳明的首创。只是阳明在《南赣乡约》中没有直接点出《圣谕六言》之名,到了他的弟子王艮那里,便直言不讳地宣称:“钦惟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为先,诚万世之至训也”。 心斋之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王栋、颜均、罗汝芳,以及浙中王门的周汝登、北方王门的尤时熙等人也非常关注《圣谕六言》对于道德劝善、社会治理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而在早期的王门讲学运动中,也有不少心学家特别关注《圣谕》的重要性。 至于《圣谕》的通俗解说书,在晚明更是到了洪水泛滥的地步,而且不仅仅是将《圣谕》与《乡约》相结合,还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将律法及报应思想融入其中。例如,隆庆辛未(1571)进士方扬于万历年间担任随州州守期间,撰有《乡约示》一文,主张在讲乡约时,应结合《圣谕》,并配之以相应的法律条文,同时还可以辅助《为善阴骘》之类的宣扬果报思想的劝善书,以“\n利害并陈,祸福具列”的方式向民众进行宣讲。 二 话题再回到《南赣乡约》。上面提到《南赣乡约》设立“彰善”、“纠过”二簿,这说明阳明在讲求“迁善”的同时,还注重“改过”,其中阳明提到了一个观念,涉及“迁善改过”的行为依据问题,值得注意,其云: 每当“乡约”举会之日,由约长带头,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如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表面看来,这里讲述的是举行“乡约”之会的仪式问题,其实这当中令人注目的是“神明诛殛”这句誓言,因为在这句誓言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重要观念:人的善恶行为必由“神明”作出最后审判。所以,凡是加入“乡约”之人都必须作出庄重的许诺:对自己的善恶行为不能有丝毫隐瞒,而且还必须对神明发誓。这个说法已经含有善恶报应必由神明主之的涵义。用阳明的另一说法,又叫做“鬼神阴相之”或“鬼神阴殛之”,他在《谕俗四条》中便这样说道: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n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所谓“相之”、“殛之”,实即“善报”、“恶报”之意,所谓“余庆”、“余殃”,不用说,这是出自《易传》,反映的是“善恶报应”的一种思想。 关于《谕俗四条》,这里须略赘几句。从文献学上说,《谕俗》属“谕俗文”,这类文献的出现可上溯至唐代,如《大唐诏令集》卷110记载了数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谕俗文》,然而由地方官员的儒家士大夫亲自制作发布这类公文,则始于北宋而盛行于南宋,如北宋陈襄于皇佑年间(1049—1053)发布《劝谕文》便是开端;至南宋朱熹不仅为其作注,而且亲自撰有名文《告南康榜文》,而那位自称喜刻“善书”的朱学传人真德秀更是擅长此道,此不具述。要之,那些“谕俗文”虽以维护乡村秩序、家庭伦理为核心内容,其中并未以善恶报应作为主要观念,但其中所突出的道德伦理诉求仍是十分强烈的,在这一点上,与后来流行的“善书”又有相通之处。到了阳明那里,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有必要将“余庆余殃”等报应观念与家族伦理的诉求结合起来,一并容纳进《谕俗文》当中,从而使得《谕俗文》也带有了《劝善书》的味道。\n 很显然,阳明作为一位儒学大师,在他的文字中竟然也有善恶相报的观念表述,这引起了后世的一些善书思想家的极大关注,例如刊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的胡宗洵编《省身集要》卷4“善恶类”,便全文收录了阳明《谕俗四条》的上述文字。另一部刊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9)的林有麟编《法教佩珠》,虽未引用上述阳明之言,却转引了阳明的另一个说法,其云:“阳明先生曰:为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归身后福,取报若市道然,吾实耻之。使无祸福报应,善可不为耶?”按,《法教佩珠》之特色在于大讲祸福报应,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该书纂于万历甲寅(1614),杂糅先儒格言与释道果报之说而成,观书中之语,知非虚言。然其所引阳明语,经查《王阳明全集》的电子版,未见出处,或许阳明另有佚文,亦未可知。不过,细按阳明所言,他在这里表明的观点实是反对祸福报应的,他主张行善不当为“身后福”所计,亦非为“取报”所计,否则道德行为便犹如“市道然”。这个说法与上述“鬼神阴相”、“鬼神阴殛”之说有所不同,引人注目,以下稍作分析。 先从“市道”一词说起。这个词是有由来的,它的原意是指商业性的交易行为。在汉代刘向《说苑》中曾出现这个词,用来讨论报恩行为如何成为政治运作之基础的问题,其曰: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n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臣不复君之恩,而尚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本也。夫祸乱之源,皆由不报恩生矣。 这里“市道”一词很值得回味,原意是指商品交易。依其语脉来看,该书主张君臣“相与”之道犹如“市道”那样,服从“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的交易规则。显然,认为人君与臣子的实际状态毋宁可以用“以市道接”——“报恩”来加以规定。应当说,的出发点不是道德而是政治,故以“市道”来肯定君臣之间的“报恩”关系。令人颇感有趣的是,当晚明清初某些正统儒家士大夫批评“功过格”运动中出现的“善恶相抵”之观点时,正是以“市道”一词来指明“善恶相抵”无疑就是一种商业行为的观点,将严肃的道德行为看做可以“与鬼神交手为市”、“与天地鬼神为市”的行为。这一批评是建立在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之基础上的。 再就上述阳明的观点来看,他主张“为善自是士人常分”而反对“取报若市道然”,应当是儒家伦理的一个基本立场,尤其是符合为善不求报这一“义”\n的道德标准。根据阳明的良知学说,人之为善的依据乃是良知本心之自觉,而不能夹杂为“身后福”所计的目的。倘若行善是为求“身后福”,那么这种行为无异于变相的市场买卖行为,从根本上违反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主义立场,理应为儒者所耻。也就是说,善的行为是发自本心之必然,而与“祸福报应”无关。这应当是阳明良知学的一个基本立场,这一点毋庸置疑。可见,在阳明的劝善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他的良知理论,而不是什么因果报应学说。因此在阳明留下的文字中,有关善恶报应的论述并不多见。 应当说,这既是人心的现实问题,也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乃是阳明所关心的“终极”问题,亦即阳明欲以良知学说改变人心的现实状态,进而改造社会、安排秩序。所以,对阳明来说,如何“导民化俗”便是其思想所内含的重要议题。举例来说,清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的陈宏谋在其所辑《训俗遗规》卷2《王阳明文钞》亦录上述阳明《谕俗》之文,并于卷末摘录阳明“今之戏子”的议论,以示阳明在现实问题上,视“化俗”、“劝善”为其思想的旨趣所在: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n《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 阳明以为“戏子”(意指戏本)只要去除“妖淫词调”而“取忠臣孝子故事”,那么“戏子”同样具有道德教化的意义。这段议论很值得注意,这当中涉及究竟应如何正面评价“通俗文化”的社会作用等问题。依阳明之见,无疑以“戏子”为代表的“通俗文化”,是可以起到“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之社会效应的。显而易见,阳明的这一观点,同样是从“劝善”的角度立论的。 然而对于小说戏剧的社会功能,历史上不乏有严厉的批评性意见,认为它伤风败俗,是不宜提倡的,特别是入清以后,这类意见不绝于耳,例如钱大昕便指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日小说”,以为明代“小说”之盛行到了三教外另立一教的地步,他指出:\n 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 在钱大昕的眼里,“小说”在三教九流之外俨然已成“一教”,在当时社会上的流传及其影响远超过佛老的说教,但其现实意义却远不如“释道”之教,这是因为“释道犹劝人以善”,而清代以来的“小说”则已滋长出“杀人”、“渔色”诸弊,结果却是“导人以恶”,令人“丧心病狂”。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部给事中刘楷则上疏请禁小说,并获批准,疏称:“自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真学术人心之大蠹也”。据传,刘还提出了包括150余种小说的书单。几乎与刘楷同时,理学名臣汤斌则在其巡抚江苏(1684—1686)的任地,出示了一篇《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非常严厉地写道: 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若仍前编刻淫词小说戏曲,坏乱人心、伤风败俗者,许人据实出首,将书板力行焚毁。 可见,禁毁传奇小说俨然是清朝政府的文化措施之一。 相比之下,晚明时代的风气则要宽松开放得多。就在上引阳明论“戏子”条后,陈宏谋还摘录了一条刘蕺山的语录,其意颇与阳明相近,蕺山说:\n 梨园唱剧至今日而滥觞极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废,但其中所演传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从此设法立教,虽无益之事,未必非转移风俗之一机也。先辈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乐章也。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观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百倍。至于《渡蚁》《还带》等剧,更能使人知因果报应秋毫不爽。杀盗淫妄,不觉自化,而好生乐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则虽戏而有意者也。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牒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帏其妇人而观之,见其淫谑亵秽,备极丑态,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闲,犹恐有渎伦犯义之事,而况乎宣淫以道之?试思此时观者,其心皆作何状,不独少年不检之人,情意飞荡,即生平礼义自持者,到此亦不觉津津有动,稍不自制,便入禽兽之门,可不深戒哉! 按,陈宏谋在该条末附说明称录自蕺山《人谱类记》,然经查《人谱杂记》,未见此条。另据邱嘉穗(约康熙五十六年前后在世)《订音律》以及杨恩寿《词余丛话》所引,自“今之院本”至“深可痛恨”,当为陶石梁(名奭龄,1565—1640)语,可见石梁的上述观点影响颇为深远。\n 首先,蕺山承认“梨园唱剧至今日而滥觞极”,其中“有邪正之不同”,然而同时他也承认在当今世俗社会,这些“梨园唱剧”的文学作品已然“必不能废”,只要利用得好,小说戏剧未必“非转移风俗之一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先辈陶石梁”的一段话,来引证“今之院本”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已经远非“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可比,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宣扬的“孝子悌弟、忠臣义士”的悲壮故事以及“因果报应,秋毫不爽”的果报思想是极易感化人心的。当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淫秽唱本及戏剧则应严加防范,是绝不可入眼或入耳的。要之,小说一类的作品具有正面积极的教化意义,在这一点上,蕺山、石梁的观点正与上述阳明所言相同。重要的是,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于“戏子”的劝善功能、化俗作用。 诚然,依阳明的心学理论,劝人为善固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人之所以必然向善,乃是出于良知自觉,而非出于外力的强制,更非出于求得好报的目的,因此“使无祸福报应,善可不为耶”这一问题的设定,对于阳明来说,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换言之,为善与“祸福报应”并无任何理论上的必然关联。但是阳明对于《周易》“余庆余殃”说的肯定,乃至对“戏子”\n的劝善化俗之功能的肯定,却从另一方面说明,阳明(包括后来的石梁、蕺山)意识到良心自觉的口号必落实在人人为善的社会实践上。也正由此,阳明着眼于“戏子”的劝善功能,认为它具有感化人们“良知”的正面意义。而在阳明后学之一员的陶石梁看来,问题更直截了当:正是由于小说唱本这类文学作品大多提倡“因果报应,秋毫不爽”的观念,因此对于教化人心、移风易俗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从阳明“神明殛之”到石梁“因果报应”,表明在心学的道德劝善思想中,已不免涉及“报应”一类的宗教问题。特别是从阳明学发展到阳明后学,“因果报应”思想已发生了由隐至显的转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正被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道德的善恶与人生的祸福是否必然关联。这个问题正是晚明以降道德劝善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可看出,“德福”如何一致应是儒学(包括阳明心学)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