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7 发布 |
- 37.5 KB |
- 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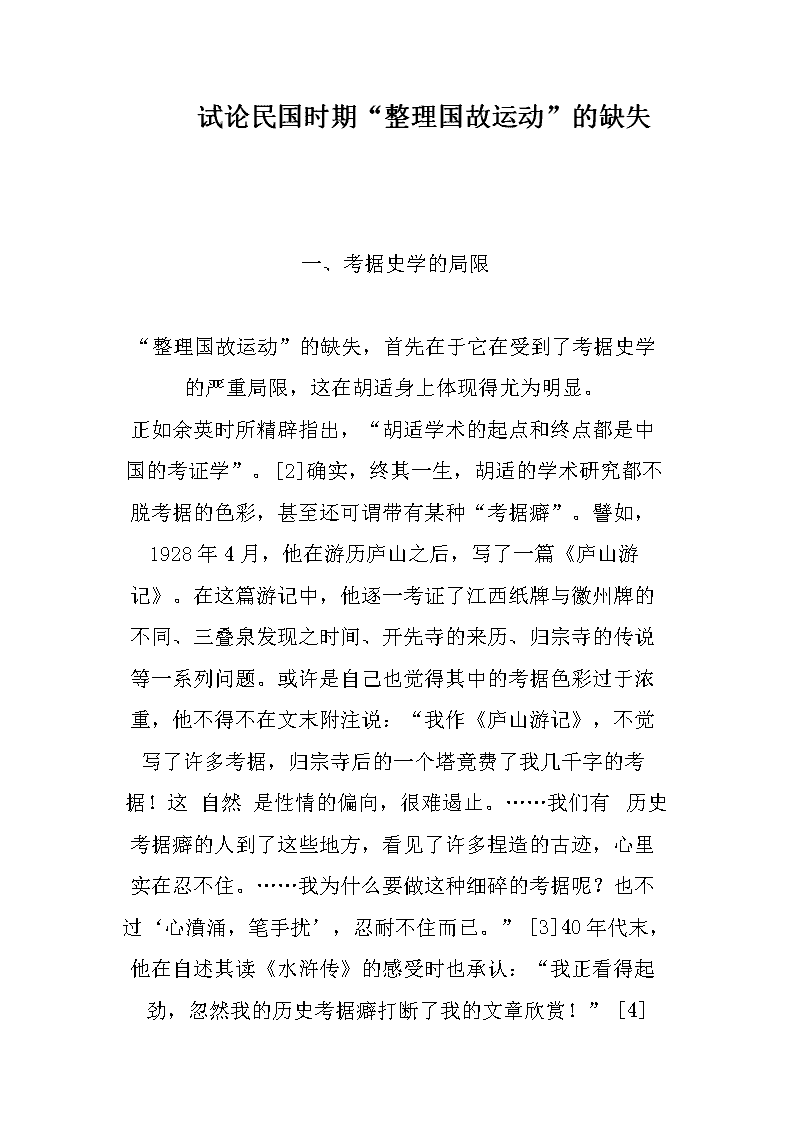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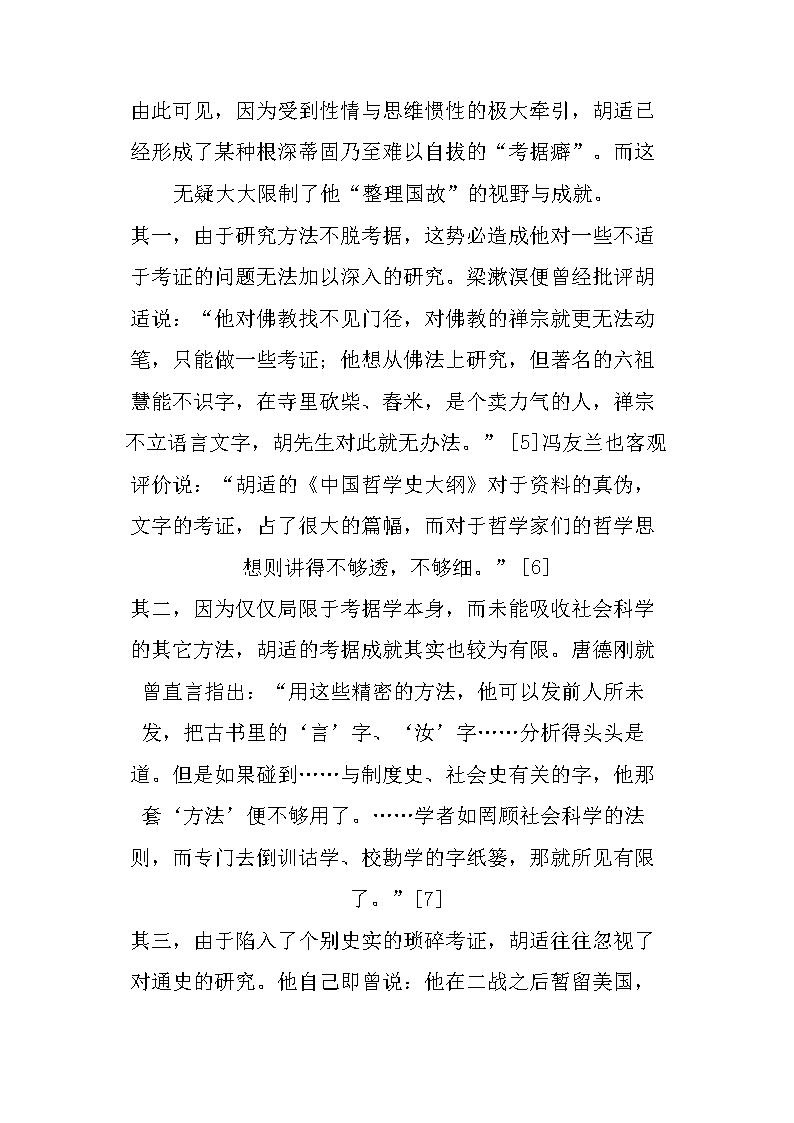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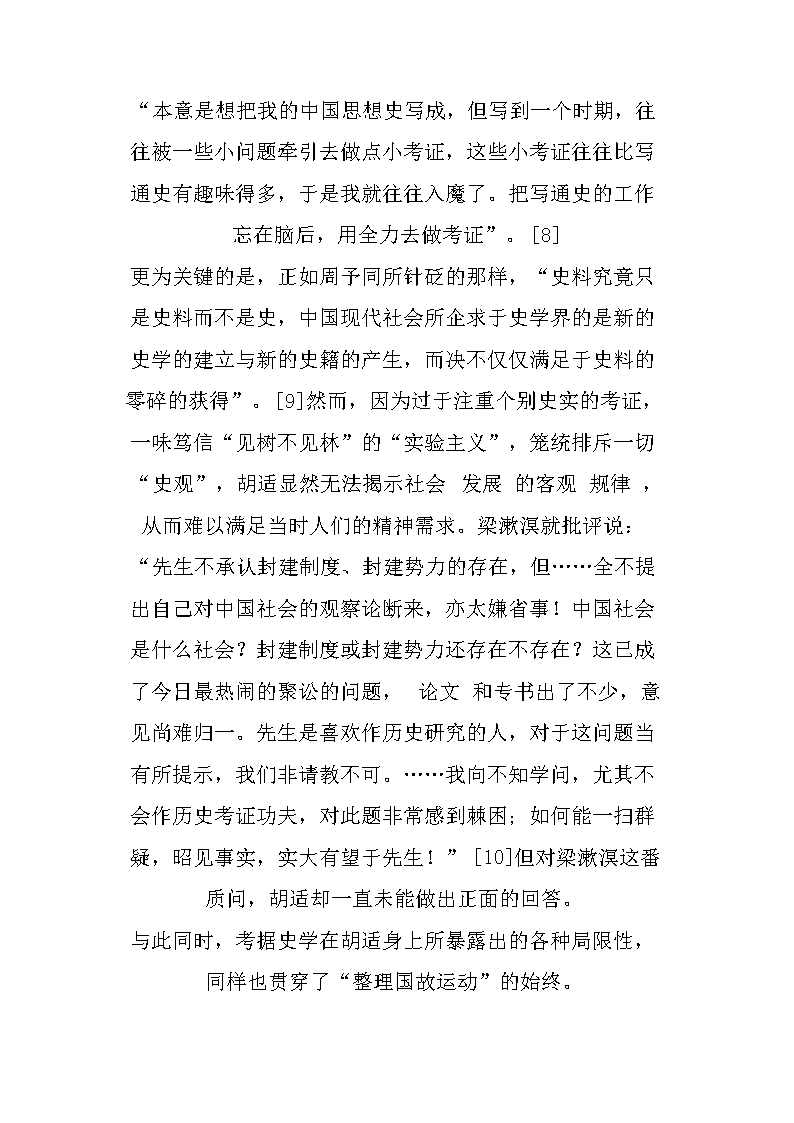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一、考据史学的局限“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首先在于它在受到了考据史学的严重局限,这在胡适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余英时所精辟指出,“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2]确实,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研究都不脱考据的色彩,甚至还可谓带有某种“考据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历庐山之后,写了一篇《庐山游记》。在这篇游记中,他逐一考证了江西纸牌与徽州牌的不同、三叠泉发现之时间、开先寺的来历、归宗寺的传说等一系列问题。或许是自己也觉得其中的考据色彩过于浓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说:“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3]40年代末,他在自述其读《水浒传》的感受时也承认:“我正看得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4]\n由此可见,因为受到性情与思维惯性的极大牵引,胡适已经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乃至难以自拔的“考据癖”。而这无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国故”的视野与成就。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脱考据,这势必造成他对一些不适于考证的问题无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经批评胡适说:“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能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5]冯友兰也客观评价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6]其二,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学本身,而未能吸收社会科学的其它方法,胡适的考据成就其实也较为有限。唐德刚就曾直言指出:“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的法则,而专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纸篓,那就所见有限了。”[7]其三,由于陷入了个别史实的琐碎考证,胡适往往忽视了对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说:他在二战之后暂留美国,\n“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8]更为关键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针砭的那样,“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国现代社会所企求于史学界的是新的史学的建立与新的史籍的产生,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零碎的获得”。[9]然而,因为过于注重个别史实的考证,一味笃信“见树不见林”的“实验主义”,笼统排斥一切“史观”,胡适显然无法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难以满足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梁漱溟就批评说:“先生不承认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亦太嫌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提示,我们非请教不可。……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事实,实大有望于先生!”[10]但对梁漱溟这番质问,胡适却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与此同时,考据史学在胡适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种局限性,同样也贯穿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始终。\n其一,因为片面强调考据,导致了许多大学国文系课程明显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的鉴赏。[11]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针对清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状况评论说:“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乃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骗。”[12]其二,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13]确实,由于过于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对疏通与推论,“整理国故运动”在某些缺乏史料的问题上,难免显得无能为力。譬如,史语所虽在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毕竟无法将中国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复原,而它又向来以所谓“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相标榜,[14]以至于长期以来,一部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始终付之阙如。有鉴于此,李济晚年就曾反思说:“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说得简单一些,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应该根据科学的事实写历史,同时也应该用文学的手段写历史。……\n因此,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15]其三,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订整理为主,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它欠缺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不可能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目的。[16]关于这一点,牟润孙曾经十分尖锐地针砭说:“综观此一时期之史学,当其初也,沿袭五四以来之积习,仍多以考据为专业,而偏重材料。……治史者咸致力于寻求罕见之典籍文物,苟有所获,则不问事之巨细,题之轻重,旁徵广引、附会渲染以为文章。……今日史学之衰,在于舍义而言事,抑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寻琐屑之事为务,诚所谓未闻大道也。”[17]尤其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些机构与团体,十分强调史学的自然科学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n的口号。[18]这一方面,固然大大增强了史学研究的科学色彩;但另一方面,这种将史学径直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做法究竟是否妥当,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客观来看,在史学研究中,引进或借鉴自然科学的一些工具和方法,无疑有助于我们收集与分析史料;不过,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本身是既往已逝的,不可直接观察和重复实验,这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供直接观察和反复实验,无疑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也由此决定了这两种学科的不同特点。因此,如果简单地将史学研究视为自然科学的一种,显然并不合适。而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看法则“不仅是一种瘟疫性的错误,而且对历史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危险”。[19]二、疑古思潮的偏颇除了考据史学的局限之外,“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还反映在疑古思潮的偏颇上。毋庸置疑,由“古史辨运动”所激起的疑古思潮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古史体系的不可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谓凿破鸿蒙、廓清迷雾,给长期处于凝固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极大推动了古史研究的进展[20]和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21]同时也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反迷信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22]胡绳就曾评价说:“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23]李学勤也客观指出:“\n由中国当时的思想史来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因为这一思潮的兴起,有利于冲决封建思想的网罗,和后来‘打倒孔家店’也有联系,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应给以充分的肯定。”[24]不过,正如李学勤所同时提出,“我们今天加以回顾,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25]的确,由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敬意”,[26]“古史辨运动”也存在着不少的偏颇。第一,在辨伪的范围和内容上,“古史辨派”陷入了很大的误区。首先,“古史辨派”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伪书”与“辨伪史”之间的界限。[27]不可否认,鉴于“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28]因此伪书既然为“伪”,[29]其所记载的历史当然也值得怀疑。不过,这种怀疑还需要进一步详加考辨,并不直接意味着“伪书”中的历史就一定是“伪史”。但顾颉刚却径直断言:“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30]概言之,“伪书”中记载的历史皆是“伪史”。[31]客观来看,这一结论显然断之过勇,[32]以至于当时便有一些学者辩驳:“判定‘古史’的真伪,只是依赖古书的真伪,这就算是‘史学方法’么?……‘\n真书’、‘伪书’,那能和‘真史’、‘伪史’的观念相混!”[33]其次,由于“古史辨派”曾经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一度造成了古史的空白。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来载记历史。在这些传说中,固然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神话”,但是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过详细考辨,将它们加以具体的区分。然而,“古史辨派”却将古史“传说”混同于“神话”,认为皆是“有意造伪”而成,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古史的空白。从当时学术界对于“古史辨派”的批评来看,有很大一部分的批评意见正是针对“古史辨派”这一偏颇而发。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就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34]徐旭生也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35]他并批评“古史辨派”说:“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36]此外,钱穆也提出:“\n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他并且还进一步分辨说:“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以其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37]或许正是由于受到了上述批评,“古史辨派”也不得不加以了深刻反思。[38]1935年,顾颉刚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便说:“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39]相比此前的一概否定,他这种观点显然有所改变。而杨宽更是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一文中,对中国古史的传说进行了系统的讨论,甚至提出了一种“民族神话史观”,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于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40]对于这一见解,童书业也呼应说:“我们知道: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41]不难看出,“古史辨派”后期对古史传说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而这种反思恰恰映衬出了原来观点的偏颇。第二,在辨伪的理论与方法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罅漏。首先,从理论前提来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正是建立在崔述所谓“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n这一质疑的基础之上。[42]这也就是说,“层累说”认为“所闻宜略”的后人不可能比前人知道更详细的古史;如果“反益详”,那就一定是“造伪”。显而易见,这一理论前提完全排除了后人可以掌握比前人更多史料的可能性,未免太过于武断。[43]其实,“世益远”而其所闻“反益详”的情形,在世界历史上往往屡见不鲜。即以《老子》一书为例,魏晋时人仅得见王弼注本与河上公注本,而北齐武平间开项羽之妾冢,便获已佚之《老子》抄本,当时寇谦之也得安丘望本,仇狱又有所传河上丈人本。至唐初,傅奕遂据此数种版本,校订成《老子古本篇》,其中对《老子》原貌的了解,无疑较此前更为全面。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发现汉初帛书《老子》甲、乙本,近人据此对《老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更有了新的认识。又如,古代埃及虽拥有悠久的文明史,但由于历经劫难,特别是因为其象形文字已成为一种死文字,不再使用,也无人能辨识,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埃及的古代文明知之甚少。而到了近代,通过众多学者对象形文字的释读,这种状况则发生了明显改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基本重建了埃及史。[44]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它们都论证了在历史研究方面,后人完全有可能通过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获得比前人更多更新的认识,而这显然也说明了“层累说”理论前提的偏颇。\n其次,“古史辨派”由于在辨伪方法上,过多地运用了“默证法”,从而直接导致了某些结论的不当。1925年4月,张荫麟在《学衡》上发表了《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敏锐指出顾颉刚的研究方法犯了无限度地使用“默证”的错误。所谓“默证”,他解释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fromsilence)”。他还阐明:“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他同时还引述法国历史学家色诺波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是以默证方法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之想象甚力,而必当入于之观念中。”而在他看来,顾颉刚仅据《诗经》、《尚书》中没有记载尧、舜的事迹,便轻率断定“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45]\n1930年,梁园东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一文。在此文中,他同样也针对“古史辨派”的“默证法”强调:“绝不应只因为他所说的某时历史,不见于某时记载,就都认为是他的假造,是骗人的,这个‘辨伪的方法’,就离开历史的研究十万八千里了!”[47]此后,徐旭生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时,也指出“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偏颇,“主要的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48]与此同时,“史学二陈”也分别对“默证法”提出了批评。据周祖谟回顾,陈垣常对学生宣讲,判断要审慎,如研究讨论一事,在证据不足时,决不可妄下断语,要把“未见”与“未有”分别清楚,不能将“未见”误为“未有”。[49]而据罗香林回忆,陈寅恪也曾对他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n,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50]总之,“古史辨派”的辨伪,无论是在范围和内容,还是理论与方法上,都带有很大的偏颇。同时也正因此,一度相当兴盛的疑古思潮开始逐渐消退。胡适在1933年便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of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51]次年,他更是通过撰写《说儒》一文,对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做了较大修正。[52]对此,有论者即指出:《说儒》的出现是民国以来疑古风潮的一个大转变,“不但是胡适自己宣告脱离这股疑古的风潮,也是为整个疑古风潮的终止做了预先的宣告”。[53]至于作为“古史辨派”灵魂人物的顾颉刚与钱玄同,他们二人在此期间的观点也有较大的转变。钱穆就观察到:顾颉刚在抗战时期主持齐鲁大学时,“实有另辟蹊径,重起垆灶之用心”;他还曾回忆:“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54]柳存仁在1940年10月所撰的《纪念钱玄同先生》一文中,更是针对“古史辨派”这种转变,系统总结说:“自从钱先生和其他的‘辨伪’\n的学者们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来,十余年间,古史的研究,因着参加者的进行方法和实际工作的不同,已经转变过好几次了,转变的途径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55]显然,这一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意味着“走出疑古时代”的开端。综上所述,由于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1922年8月28日,胡适曾在日记中感慨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56]此处所谓“半新半旧”,说明胡适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承担的过渡角色,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而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无疑更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深刻的思考和总结。[1][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2]\n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3月18日),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3]胡适:《庐山游记》后记(1928年4月20日),《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4]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997页。[5]梁漱溟:《略谈胡适之》(1987年4月12日),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12页。[7]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他还尖锐批评胡适:“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的‘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Scholarship)的窠臼。”同上,第133页。[8]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1944年7月17日),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9]\n周予同:《治经与治史》(1936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10]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6月3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11]关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设置,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曾承认:“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不过,他这一反省并未能扭转当时所盛行的风气。[12]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8年12月22日条,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2页。[13][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5页。[14]傅斯年就提出:“\n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页。[15]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年1月11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16]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甚至严厉地批评说:“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17]牟润孙:《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1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第183页。[1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20页。[20]郭沫若便承认顾颉刚一系列的古史辨伪“的确是个卓识。……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郭沫若:《评<古史辨>——\n<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六节》,1940年2月,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63页)。钱穆也说:“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0页。[21]余英时即曾提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42页。[22]白寿彝先生就认为顾颉刚“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像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23]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2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尹达也曾说顾颉刚“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25]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39页。[26]关于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民国学术界时有提倡。梁启超即倡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n(《欧游心影录》,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页)。钱穆后来在《国史大纲》中更提出:“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27]胡绳就曾指出“古史辨”的辨伪,“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他认为:“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因而不能“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增订本),第145页。[2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29]其实,究竟何为“伪书”,也缺乏一个明确标准。李学勤即曾列举了古书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十种情况,即佚失无存,名存实亡,为今本一致,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他因此说:“对古书形成和流传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n二字来判断的。”《对古书的反思》,《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30]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年6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5页。[31]当然,“古史辨派”并未完全否认“伪书”的史料价值,他们并且对此曾有多次申述。所以“古史辨派”的“疑古”并非“蔑古”。因该问题不在本文范围内,只能另文探讨了。[32]王元化便说:“以怀疑精神探究古史本无可非议,但以辨伪规范古史,则未免过于简单。”《谈考辨古史》,《清园夜读》(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33]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1930年10月15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22号,1930年11月25日。王汎森也说:“这个运动最大的盲点之一是把书的真伪和书中所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伪书中便不可能有真史料。”《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7年版,第295-296页。[34]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n[3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3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6页。[37]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修订本),第8页。[38]“古史辨派”的反思,或许还受到时局的触动。有论者认为:“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与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于是,自‘古史辨’以来所掀起的历史研究法的热潮,逐渐冷了下来。”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页。[39]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4页。[40]此据童书业的评述,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1940年8月30日),《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2-3页。[41]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5-6页。[42]\n崔述:《无闻集》卷三《<曹氏家谱>序》,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页。[43]杨宽便认为层累说“颇多疏略;亦且传说之演变不如是之简单”(《中国上古史导论》,1938年1月,《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104页)。顾颉刚也自承:“论断或落于主观,以致有武断及深文周纳之处,又如引用材料或有错误,以致所作的记载有不合事实之处”,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一》(1930年1月3日),《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页。[44]详参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7页。[45]张荫麟:《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顾颉刚编《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271—273页。张荫麟后来还曾申明:“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评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古史辨》第2册,第15-16页。[46]绍来:《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n质顾颉刚的<古史辨>》(1928年11月28日),《古史辨》第2册,第419页。[47]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续)》(1930年10月15日),《东方杂志》第27卷第24号,1930年12月25日。[4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3页。[49]周祖谟:《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50]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张洁、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51]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67页。[52]梁启超就曾经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6页。[53]赵润海:《胡适与<老子>的时代问题》,转引自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n[5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229页。[55]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1940年10月),《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3页。[5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1922年8月28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