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7 发布 |
- 37.5 KB |
- 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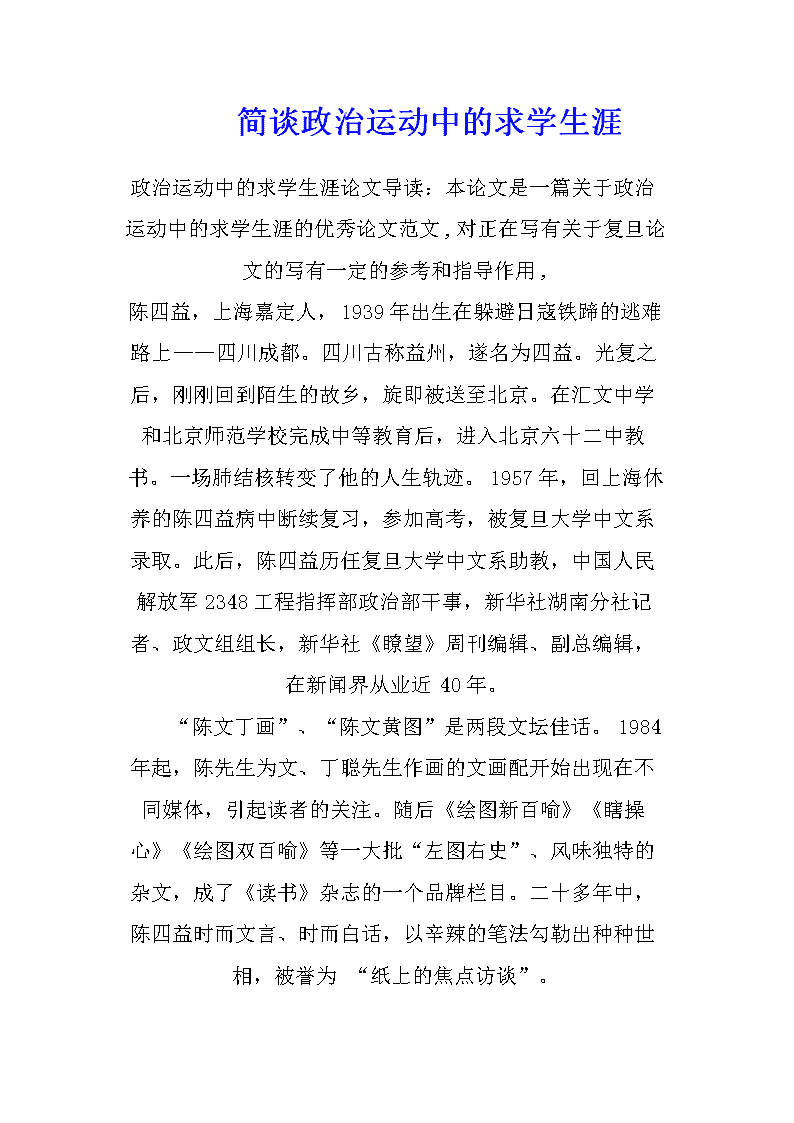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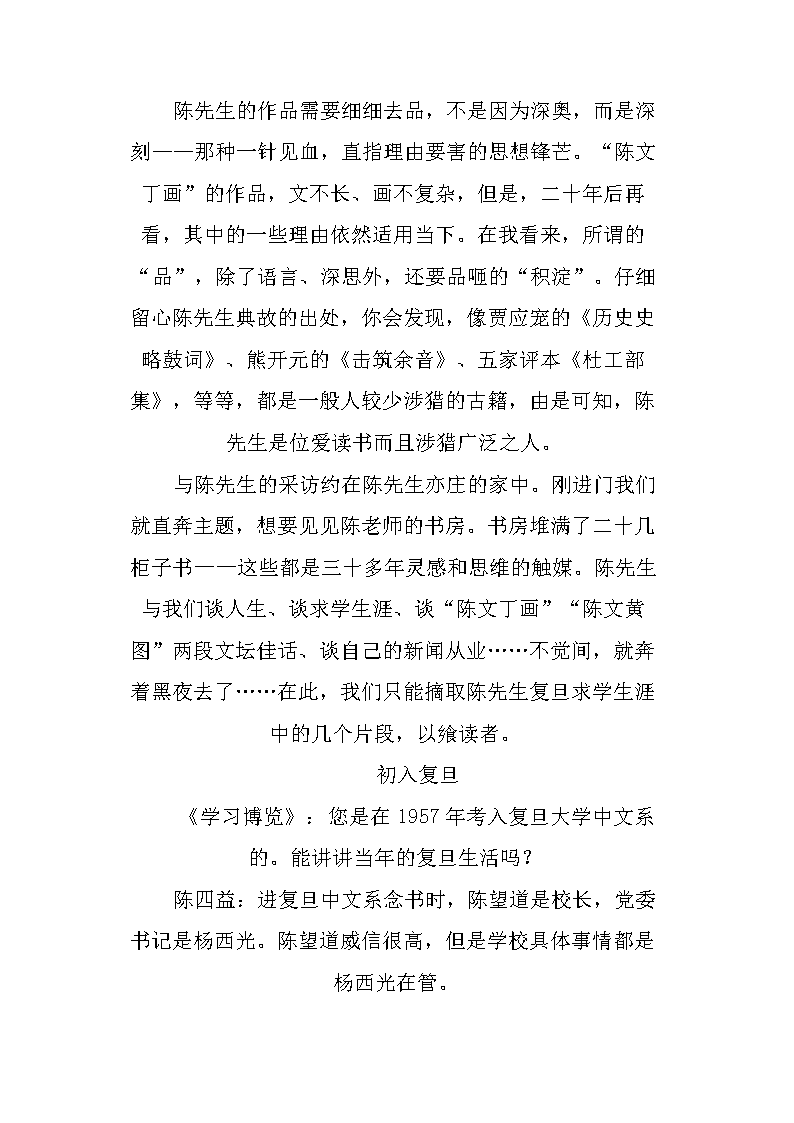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简谈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
简谈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复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陈四益,上海嘉定人,1939年出生在躲避日寇铁蹄的逃难路上——四川成都。四川古称益州,遂名为四益。光复之后,刚刚回到陌生的故乡,旋即被送至北京。在汇文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完成中等教育后,进入北京六十二中教书。一场肺结核转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57年,回上海休养的陈四益病中断续复习,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此后,陈四益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助教,中国人民解放军2348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干事,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政文组组长,新华社《瞭望》周刊编辑、副总编辑,在新闻界从业近40年。 “陈文丁画”、“陈文黄图”是两段文坛佳话。1984年起,陈先生为文、丁聪先生作画的文画配开始出现在不同媒体,引起读者的关注。随后《绘图新百喻》《瞎操心》《绘图双百喻》等一大批“左图右史”、风味独特的杂文,成了《读书》杂志的一个品牌栏目。二十多年中,陈四益时而文言、时而白话,以辛辣的笔法勾勒出种种世相,被誉为“纸上的焦点访谈”。\n 陈先生的作品需要细细去品,不是因为深奥,而是深刻——那种一针见血,直指理由要害的思想锋芒。“陈文丁画”的作品,文不长、画不复杂,但是,二十年后再看,其中的一些理由依然适用当下。在我看来,所谓的“品”,除了语言、深思外,还要品咂的“积淀”。仔细留心陈先生典故的出处,你会发现,像贾应宠的《历史史略鼓词》、熊开元的《击筑余音》、五家评本《杜工部集》,等等,都是一般人较少涉猎的古籍,由是可知,陈先生是位爱读书而且涉猎广泛之人。 与陈先生的采访约在陈先生亦庄的家中。刚进门我们就直奔主题,想要见见陈老师的书房。书房堆满了二十几柜子书——这些都是三十多年灵感和思维的触媒。陈先生与我们谈人生、谈求学生涯、谈“陈文丁画”“陈文黄图”两段文坛佳话、谈自己的新闻从业……不觉间,就奔着黑夜去了……在此,我们只能摘取陈先生复旦求学生涯中的几个片段,以飨读者。 初入复旦 《学习博览》:您是在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能讲讲当年的复旦生活吗? 陈四益:进复旦中文系念书时,陈望道是校长,党委书记是杨西光。陈望道威信很高,但是学校具体事情都是杨西光在管。\n 大学一年级业务课只有四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艺学引论、语言学引论。后两门引论由蒋孔阳、濮之珍夫妇担任。所以,系主任朱东润曾戏谓蒋濮二先生可以将住处起名“双引楼”。 因为中学在北京待了几年,到上海我就成了普通话讲得好的了。濮先生讲推广普通话,讲到北京的儿化音,她念不出来。虽然江南的下江官话,如杭州话里也有“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由写论文的好帮手.提供,.儿”,但说起来并不“化”。比如,荡荡-儿、耍耍-儿。濮先生是安徽人,也化不起来,于是就叫“陈四益,你给他们念一念”。我当然就“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地念起来了。于是,我就成了《语言学引论》的课代表。 普通话说得好,也有“麻烦”,一是那时读中文系的都想读文学专业,但到分专业时,因为会说普通话,就被“理所当然”地分到了语言专业;二是到了1959年之后,全国性的大饥荒开始显现。杨西光想通过丰富校园生活,缓解一下学生对生活困难的不满,也为了让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落到实处,在复旦抓了两件事,体育抓了一个排球队,文艺抓了一个话剧团。演话剧要说普通话。于是,我又“理所当然”地被选到话剧团。话剧团和排球队是学校重点抓的,起先都有一位党委副书记“挂帅”\n,采取集中住宿的办法。这一集中,班里的课余活动我基本上就不能参加了。 《学习博览》:进了话剧团,需要排戏,还要公演什么的,课程没落下? 陈四益:所有课都上,没有落,该交的作业都交。不过,外语需要花时间去背,有的时候一忙也就没有背,虽能应付考试,终究成为工作的短项,这是终生的遗憾。 参加话剧团占用的时间确实不少,但是班上念书的同学花在其他各种运动、劳动中的时间也不少。另外,参加课余活动也有课程中学不到的东西。譬如戏剧艺术的表导演体系之类,如果不参加话剧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与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了。 各种指标 《学习博览》:那时的劳动,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陈四益:学生时期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有好处,可以了解社会,了解民情,不过当时参加劳动更多是着眼于“思想改造”。比如,大粪是农家肥,有用,但大粪是臭的,这也是客观存在。那时为要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一定要说大粪是香的,或者说一想到粮食丰收就不觉得臭了,否则就是没有工农感情,这是逼着人说假话。其实农民自己也都说大粪“臭得来”。\n 《学习博览》:50年代政治运动频仍,那时高校除了学习、劳动外,还有些什么运动? 陈四益:我们是1957年下半年进校的。进校不久就碰到“反右”扫尾和补课,我们年级也有两位同学因原单位转来“材料”,被补划为“右派”,此后颠沛一生。到了1958年上半年,又有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复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动的年代”,你们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陈四益:在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师生关系就比较紧张。在大学,我们对老师实在是不太好,而这背后又有时代的理由。 1957年进校,基础课还是好好上的,到1958年老人家要“解放思想”。还发了个材料,说周瑜在多少岁,诸葛亮在多少岁,便已功成名就,连西厢记里的小红娘也在其中,因此得出了历了“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要学生给领导贴大字报。经过了1957年“反右”,谁还敢贴?但领导下了指标,一天要写满一百张才能睡觉。这样才能造成声势。写什么呢?“食堂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整天在嘀嗒水,也没有人修。这是谁负责的?浪费水!”“哪个地方的路灯白天还亮着,这也是浪费”。实在没得写了,就看别人写了什么,回来变化一下词句又算一张。\n 农村里面粮食高产也是一样的。把公社书记都叫到县里面去开会,“明年亩产多少多少斤”。公社书记说“不可能”。不可能就留在县里不许回家,什么时候说可能,才可以回去。验收的时候把几亩田的水稻都弄到一亩田里面去,最后亩产超万斤。“要多少给多少,完成多少算多少”。反正吹牛当不得死罪,不吹牛活罪难逃。我们班上也吹过“亩产萝卜一万斤”的牛,最后上面的兴趣点变了,指标也就没人再问了。 当时还提出过要“全班摩托化”,全班都要会骑摩托车。这个事儿还是比较有用,但要全班每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都学会,也不容易。班上还有很多“调干生”,年纪最大的已经三十多岁,自行车都不会骑,学摩托就比较难了。开车不会拐弯,车头撞到操场边的竹篱笆里面,也不会停,还有把足球球门撞断的。等到学校开运动会,入场式时前面要有一队骑摩托车开道,便选一些开得比较好的,本人忝列其中。这样就算“摩托化”了。还有全班通过劳卫制——\n劳动与保卫祖国的体育制度。体育锻炼有指标,比如说百米多少秒,引体向上要拉多少个,俯卧撑要做多少个。这又难了。三十多岁的老大哥,怎么跑百米?眼看着别人都敲锣打鼓去党委报喜去了,怎么办呢?从学校门口邯郸路桥的斜坡上跑下来。还不合格。两边派两个跑得快的同学拉着他往前跑。再不行,最后,这边发令枪一打,开始跑,那边掐表的过几秒再掐,这头还没跑到,那头已经停止计时。这样全班就通过劳卫制了——弄虚作假也是指标逼的。 “除四害”也有指标。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数老鼠尾巴,蚊子、苍蝇要装在火柴盒子里面最后点数。蚊子打不到那么多,怎么办?学校后面有一条臭水沟,河边有很多草,晚上蚊子成团。我们就拿脸盆,抹点肥皂,一抡胳膊,蚊子就被粘在肥皂水上了。这样才能够数。开始大家还真数脸盆上有多少个蚊子,后来看到上面也不追查,就胡乱报个数交差。抓苍蝇,不够数,怎么办呢?当时说,要找根本:苍蝇会下崽,要在苍蝇还是蛹的时候就要把它挖出来,不让它孵出来。学校里面哪里有蝇蛹?就跑到农村去。农村粪缸旁边的土里面不都是蝇蛹吗?就跑到那儿挖去。臭啊!挖完回来,卫生习惯好的同学洗完手再去吃饭,有的同学直接去吃饭,后来发现得了急性传染性肝炎。 好多大好光阴,被这些事情给耗费掉了。 愧对恩师 《学习博览》:身处在这个“运动的年代”,你们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如何呢?\n 陈四益:在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师生关系就比较紧张。在大学,我们对老师实在是不太好,而这背后又有时代的理由。 1957年进校,基础课还是好好上的,到1958年老人家要“解放思想”。还发了个材料,说周瑜在多少岁,诸葛亮在多少岁,便已功成名就,连西厢记里的小红娘也在其中,因此得出了历史上总是年轻的战胜年老的,总是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云云。于是,号召我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们刚刚上完基础课,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要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了。 张世禄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在一年级的时候教我们《古代汉语》,讲课极好。要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什么呢?当时认为语言学的正宗应该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由》。张世禄先生过去介绍过瑞典语言学家、汉学家高本汉的学说,高本汉算是“资产阶级语言学家”,我们就批判“张世禄贩卖了高本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观点”。 那时候我们哪看过高本汉?年轻教师给我们讲高本汉几个主要的“错误观点”,我们对照斯大林的语言学,就批判张先生。前些时,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在北京的旧书店里看到一本《张世禄资产阶级语言学批判》,里面有你的文章。我说当然有咯,无知者无畏嘛。 “文革”\n以后,我从湖南回上海,看望张世禄老师。张先生那时岁数已经很大了。一看见我,让我进屋,给我倒水,倒水的时候他的手都在抖,我说:“张先生,我自己来倒。”“不不不,我给你倒。”他还说:“我前两年到长沙,想去找你,但是没有找到。”尽管那个时候我们写文章批判他,但是老师还记得我,到湖南还想来看看我! 《学习博览》:在当时这种浮夸、冒进的氛围里,高校中的老师如何自处? 陈四益:1958年大跃进,工厂、农村都在放卫星,科研也要放卫星。系里开跃进会,催促老教授们超前完成著作,要他们表态“跃进”。中文系系主任是朱东润教授。朱先生拟定要完成三部著作:《陆游传》《陆游诗选》《陆游研究》,准备五年完成。台下的学生高呼“不行,五年太保守了”。朱先生说:“那就四年吧。”“不行,四年也太保守,要跃进!”结果朱先生非常痛苦地说:“这个已经很困难了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复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就是蒋先生整理的。蒋先生第一次上课说:“我以前的学生都给我写一份他们的简历。我的箱子里面保存着我历届学生的履历,希望你们也都写一份给我,这样我会记得你们。”老师其实蛮好的。 但是我们是在“反右”之后进学校的,又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时候,觉得\n“凭什么我们的履历要给你一个资产阶级教授”?结果班上没有。这样吧,三年。再也不能提前了。”才算勉强通过。其他的同学、年轻教师牛皮吹得很大,最后很多跃进指标都没实现,早就把这个事儿忘掉了。但朱先生确实是三年内把那三本书写出来了。他是真学者。真学者不能吹牛,可惜现在吹牛的学者太多了! 《学习博览》:“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学生打倒了老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论文资料由.提供,地址.师,除了张世禄先生外,复旦中文系还“打倒”了谁? 陈四益:蒋天枢先生。蒋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陈寅恪最后的著作就是蒋先生整理的。蒋先生第一次上课说:“我以前的学生都给我写一份他们的简历。我的箱子里面保存着我历届学生的履历,希望你们也都写一份给我,这样我会记得你们。”老师其实蛮好的。 但是我们是在“反右”之后进学校的,又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时候,觉得“凭什么我们的履历要给你一个资产阶级教授”?结果班上没有一个人写。蒋先生说过两次,后来看还是没有人交,他也就不说了。他的箱子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就再也没有新履历了。\n 复旦中文系的教授本来很多,但是有一些教授我们一直没有见过,比如说陈子展。湖南人,脾气鲠,1957年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就被划成右派,从此陈子展先生不进复旦大门,连工资都不去领。不过,每个月系里还是把工资送到他家里面去。 写《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章培恒先生。“反胡风”时,因为跟贾植芳先生走得比较近,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也给抓了起来。后来放回学校,还是不让他教书,“发配”到图书馆去好几年,一直到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才允许他出来做蒋天枢先生的助教。 这些都是很有才华的人,但上面并不珍惜,随便一个罪名,就把他们最好的时光给糟蹋了。 《学习博览》:1961年、1962年那两年政策发生“调整”,又号召大家向老专家学习。你们如何面对已经被打倒过的老师呢? 陈四益:政策一调整,说法就转了一百八十度。有领导说了,“要用过去学徒给师父倒夜壶的精神向老专家学习”。但是在内部,对待知识分子的看法依旧没有变。目标是要剥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财产”。“资本家的财产是有形的,是可以剥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财产’都在他的脑子里面,你剥夺不了。所以要把他的知识学过来,然后再打倒他。”甚至说“派一百个人去学,就是九十八个人都烂掉了,有一两个学出来也是胜利”\n。把老专家当成是腐蚀青年的人了。老师们也都明白,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跟他们学或者做他们的研究生,他们还真带。政治运动中的求学生涯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