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7 发布 |
- 37.5 KB |
- 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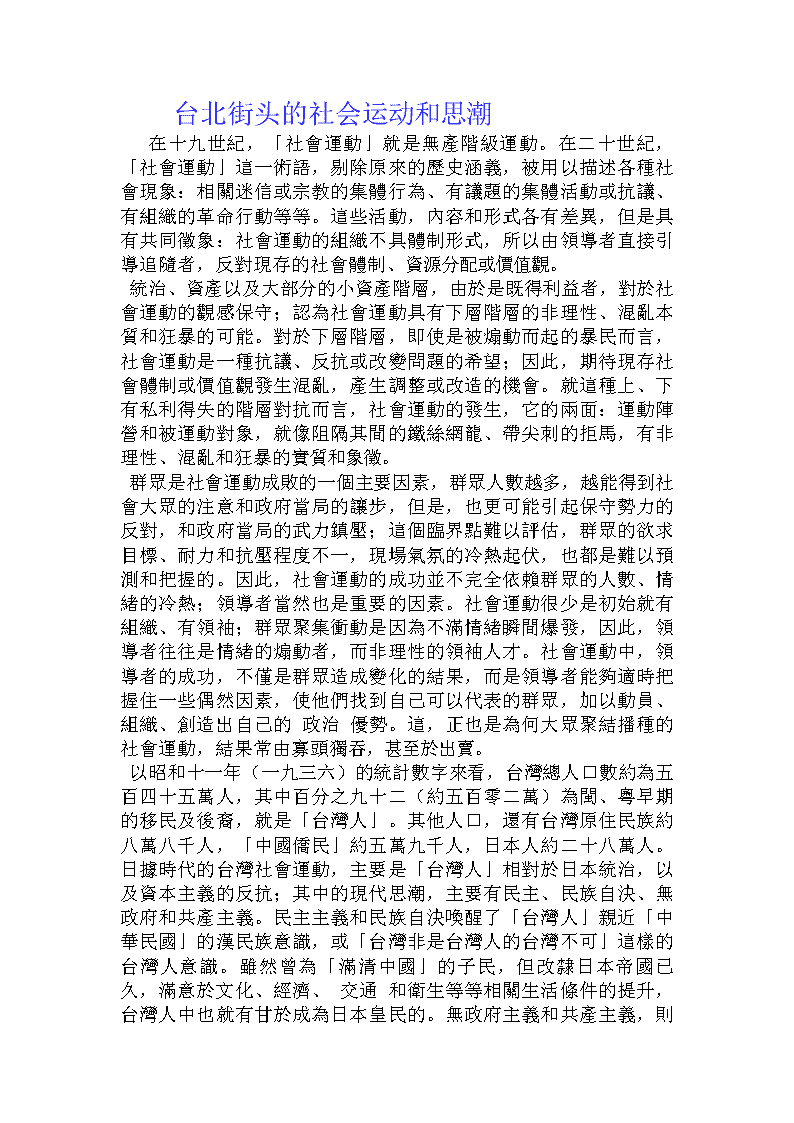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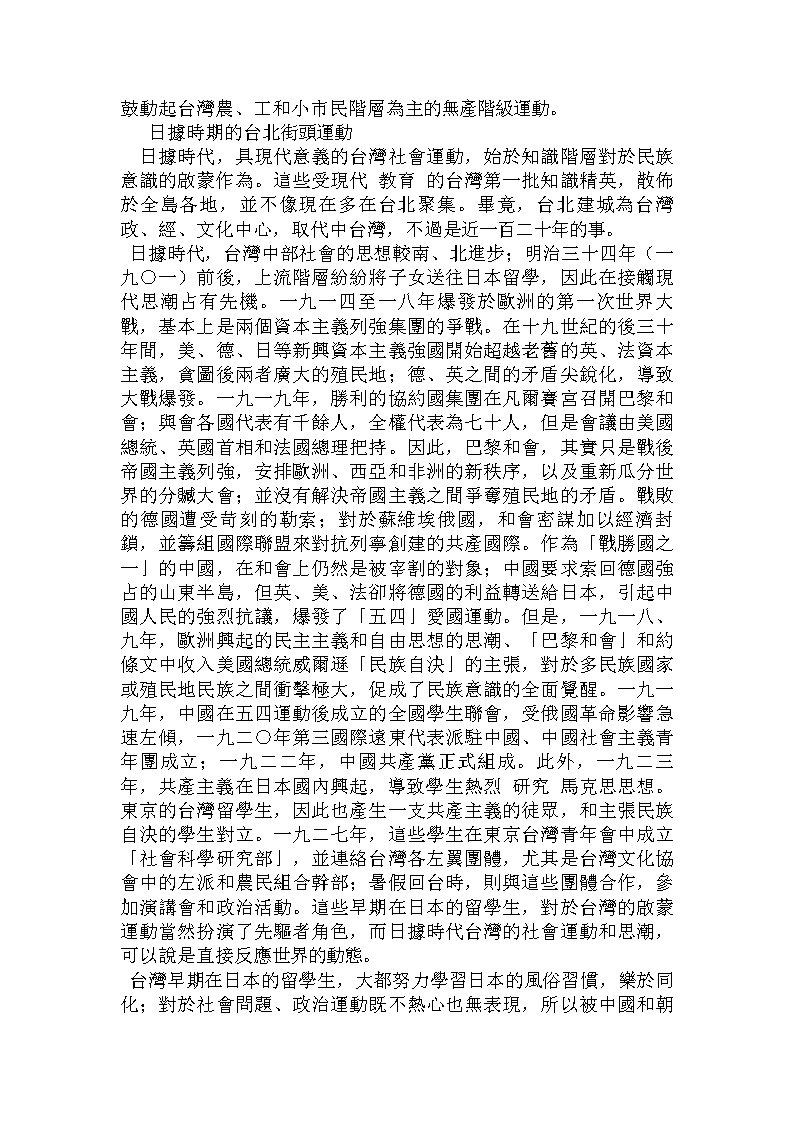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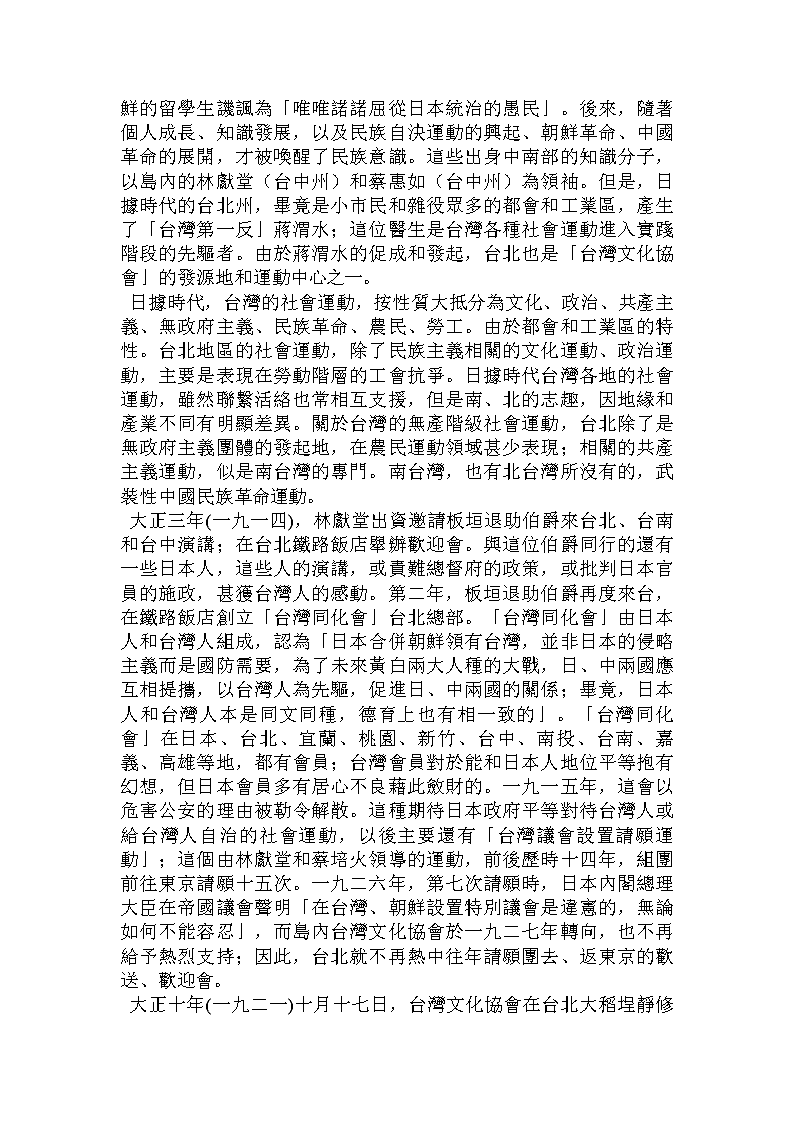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台北街头的社会运动和思潮
台北街头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在十九世紀,「社會運動」就是無產階級運動。在二十世紀,「社會運動」這一術語,剔除原來的歷史涵義,被用以描述各種社會現象:相關迷信或宗教的集體行為、有議題的集體活動或抗議、有組織的革命行動等等。這些活動,內容和形式各有差異,但是具有共同徵象:社會運動的組織不具體制形式,所以由領導者直接引導追隨者,反對現存的社會體制、資源分配或價值觀。統治、資產以及大部分的小資產階層,由於是既得利益者,對於社會運動的觀感保守;認為社會運動具有下層階層的非理性、混亂本質和狂暴的可能。對於下層階層,即使是被煽動而起的暴民而言,社會運動是一種抗議、反抗或改變問題的希望;因此,期待現存社會體制或價值觀發生混亂,產生調整或改造的機會。就這種上、下有私利得失的階層對抗而言,社會運動的發生,它的兩面:運動陣營和被運動對象,就像阻隔其間的鐵絲網龍、帶尖刺的拒馬,有非理性、混亂和狂暴的實質和象徵。群眾是社會運動成敗的一個主要因素,群眾人數越多,越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注意和政府當局的讓步,但是,也更可能引起保守勢力的反對,和政府當局的武力鎮壓;這個臨界點難以評估,群眾的欲求目標、耐力和抗壓程度不一,現場氣氛的冷熱起伏,也都是難以預測和把握的。因此,社會運動的成功並不完全依賴群眾的人數、情緒的冷熱;領導者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社會運動很少是初始就有組織、有領袖;群眾聚集衝動是因為不滿情緒瞬間爆發,因此,領導者往往是情緒的煽動者,而非理性的領袖人才。社會運動中,領導者的成功,不僅是群眾造成變化的結果,而是領導者能夠適時把握住一些偶然因素,使他們找到自己可以代表的群眾,加以動員、組織、創造出自己的政治優勢。這,正也是為何大眾聚結播種的社會運動,結果常由寡頭獨吞,甚至於出賣。以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的統計數字來看,台灣總人口數約為五百四十五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約五百零二萬)為閩、粵早期的移民及後裔,就是「台灣人」。其他人口,還有台灣原住民族約八萬八千人,「中國僑民」約五萬九千人,日本人約二十八萬人。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運動,主要是「台灣人」相對於日本統治,以及資本主義的反抗;其中的現代思潮,主要有民主、民族自決、無政府和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自決喚醒了「台灣人」親近「中華民國」的漢民族意識,或「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樣的台灣人意識。雖然曾為「滿清中國」的子民,但改隸日本帝國已久,滿意於文化、經濟、交通\n和衛生等等相關生活條件的提升,台灣人中也就有甘於成為日本皇民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則鼓動起台灣農、工和小市民階層為主的無產階級運動。日據時期的台北街頭運動日據時代,具現代意義的台灣社會運動,始於知識階層對於民族意識的啟蒙作為。這些受現代教育的台灣第一批知識精英,散佈於全島各地,並不像現在多在台北聚集。畢竟,台北建城為台灣政、經、文化中心,取代中台灣,不過是近一百二十年的事。日據時代,台灣中部社會的思想較南、北進步;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前後,上流階層紛紛將子女送往日本留學,因此在接觸現代思潮占有先機。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爆發於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兩個資本主義列強集團的爭戰。在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間,美、德、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強國開始超越老舊的英、法資本主義,貪圖後兩者廣大的殖民地;德、英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導致大戰爆發。一九一九年,勝利的協約國集團在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與會各國代表有千餘人,全權代表為七十人,但是會議由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把持。因此,巴黎和會,其實只是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安排歐洲、西亞和非洲的新秩序,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贓大會;並沒有解決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矛盾。戰敗的德國遭受苛刻的勒索;對於蘇維埃俄國,和會密謀加以經濟封鎖,並籌組國際聯盟來對抗列寧創建的共產國際。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和會上仍然是被宰割的對象;中國要求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但英、美、法卻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但是,一九一八、九年,歐洲興起的民主主義和自由思想的思潮、「巴黎和會」和約條文中收入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對於多民族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衝擊極大,促成了民族意識的全面覺醒。一九一九年,中國在五四運動後成立的全國學生聯會,受俄國革命影響急速左傾,一九二○年第三國際遠東代表派駐中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此外,一九二三年,共產主義在日本國內興起,導致學生熱烈研究馬克思思想。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因此也產生一支共產主義的徒眾,和主張民族自決的學生對立。一九二七年,這些學生在東京台灣青年會中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並連絡台灣各左翼團體,尤其是台灣文化協會中的左派和農民組合幹部;暑假回台時,則與這些團體合作,參加演講會和政治活動。這些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對於台灣的啟蒙運動當然扮演了先驅者角色,而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和思潮,可以說是直接反應世界的動態。\n台灣早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努力學習日本的風俗習慣,樂於同化;對於社會問題、政治運動既不熱心也無表現,所以被中國和朝鮮的留學生譏諷為「唯唯諾諾屈從日本統治的愚民」。後來,隨著個人成長、知識發展,以及民族自決運動的興起、朝鮮革命、中國革命的展開,才被喚醒了民族意識。這些出身中南部的知識分子,以島內的林獻堂(台中州)和蔡惠如(台中州)為領袖。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州,畢竟是小市民和雜役眾多的都會和工業區,產生了「台灣第一反」蔣渭水;這位醫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進入實踐階段的先驅者。由於蔣渭水的促成和發起,台北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發源地和運動中心之一。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運動,按性質大抵分為文化、政治、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革命、農民、勞工。由於都會和工業區的特性。台北地區的社會運動,除了民族主義相關的文化運動、政治運動,主要是表現在勞動階層的工會抗爭。日據時代台灣各地的社會運動,雖然聯繫活絡也常相互支援,但是南、北的志趣,因地緣和產業不同有明顯差異。關於台灣的無產階級社會運動,台北除了是無政府主義團體的發起地,在農民運動領域甚少表現;相關的共產主義運動,似是南台灣的專門。南台灣,也有北台灣所沒有的,武裝性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林獻堂出資邀請板垣退助伯爵來台北、台南和台中演講;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辦歡迎會。與這位伯爵同行的還有一些日本人,這些人的演講,或責難總督府的政策,或批判日本官員的施政,甚獲台灣人的感動。第二年,板垣退助伯爵再度來台,在鐵路飯店創立「台灣同化會」台北總部。「台灣同化會」由日本人和台灣人組成,認為「日本合併朝鮮領有台灣,並非日本的侵略主義而是國防需要,為了未來黃白兩大人種的大戰,日、中兩國應互相提攜,以台灣人為先驅,促進日、中兩國的關係;畢竟,日本人和台灣人本是同文同種,德育上也有相一致的」。「台灣同化會」在日本、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台南、嘉義、高雄等地,都有會員;台灣會員對於能和日本人地位平等抱有幻想,但日本會員多有居心不良藉此斂財的。一九一五年,這會以危害公安的理由被勒令解散。這種期待日本政府平等對待台灣人或給台灣人自治的社會運動,以後主要還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個由林獻堂和蔡培火領導的運動,前後歷時十四年,組團前往東京請願十五次。一九二六年,第七次請願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在帝國議會聲明「在台灣、朝鮮設置特別議會是違憲的,無論如何不能容忍」,而島內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轉向,也不再給予熱烈支持;因此,台北就不再熱中往年請願團去、返東京的歡送、歡迎會。\n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子中學舉行成立大會。意於指導及推行民族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當然懷有政治目的;但是,這會的宗旨書,避諱政治,僅寫相關啟蒙台灣文化的意思。台灣文化協會宗旨書的要義,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似可用;它說:「現今的文明是物質萬能的文明,現在的思想則呈混沌、險惡的情勢……日本的海水通達歐美,台灣海峽實在是東西南北船舶往來的關口,也是世界思想遲早將匯合之處(但是,台灣時常不能跟隨世界的進步)……現今島內的新道德尚未建設好,舊道德卻已經逐漸衰退,因此,社會的制裁力量失墜於地,人情僥薄,人人唯利是圖,無智蒙昧之細民固不待言,身屬上流者也概以揣摩迎合為能事,以博取一身之榮達為最終目標;另一方面,青年人多安於眼前的小成,薄志弱行,更沒有確實的大志……一想到此,台灣的前途實在不禁令人寒心……」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教化運動,以發行《會報》,設立報章、書、刊閱覽所、開辦文化書局,辦理各種講習會、演講,放映附帶講解的電影,推行新劇等來運作。一開始,台灣文化協會就幾乎聚集了當時全島各地,以及各種思想的精英為幹部和會員,形成統一的民族戰線,因此它的活動立即顯現出反抗日本統治的態度。由於對於社會大眾及學生具有影響和號召力,聲勢浩大,以至於日常接觸的警察、鄉鎮官吏及學校職員,執行職務時常會遲疑和畏縮;台北師範學校學生的騷動就是一例。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三日,有學生在大稻埕新街派出所附近,當著警察面前靠右側行路(規定是左側),二月五日下午五時也有數十名學生在東門街派出所前故意右行;這些學生均不服糾正,且以言詞挑釁。當晚,其中一位執勤警察利用休息時間前往學校要求校方訓誡學生,學生就在宿舍踐踏地板喧鬧惡罵,甚至於對他丟石頭;最後,演變成六百名學生的騷動,結果遭到警察署長在內的七位警察的鎮壓。\n台北的「無產青年」團體,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七月三十日,在台北市太平公學校(太平國小)舉辦同學會,企圖成立「台北青年會」;廈門留學生翁澤生在席上以台語演講,造成混亂。後來,歷經一九二五年的籌辦列寧追悼會(一月),台北青年體育會(三月)、籌辦五一勞動節示威運動(五月)、以及推動台北青年讀書會的恢復(該會例行在淡水河泛舟開會)等等活動的歷練和轉演,終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台北市大正町大正公園(南京東路一段、長安東路一段)協議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這個聯盟的台北無產青年主要為王萬得、周和成、王詩琅、洪朝宗等。這個秘密結社的聯盟,致力於宣傳民族解放、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對他們來說當時這兩種思想並無分別)。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另一批主力是彰化無產青年;這個聯盟,利用台灣文化協會陣營推廣無政府主義思想,所以也是全島性的運動。但是,它在台北以外的地方並不具組織。這個團體積極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反對台灣文化協會當時的運動路線。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遭受檢舉和禁止,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遂被共產主義運動取代,僅殘餘新劇運動(改良風俗、打破迷信、諷刺勞資關係)和放映電影。台北共產主義的抬頭,始於台北市人連溫卿;他在彭華英、謝文達等人在上海和北京推行共產主義時期,就常和她們有聯繫。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他和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蔡式穀等人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以後又取得台灣文化協會的指導權。台灣共產黨的組黨推手林木順和翁澤生都是中國共產黨員;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二十八日,他們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組黨大會,它的名義卻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組黨大會當天,有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代表參加,日本共產黨因為選舉正忙未派代表,所以希望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十一月,台灣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謝雪紅受日本共產黨指令,在其台北市御成町(中山北路二段)租住處,與中央委員林日高、莊春火開會,成立組織部和宣傳部;這是台灣共產黨在島內的中央機關雛形。因為需要處理黨務和落腳,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市太平町(延平北路一、二段)租下店鋪計畫開辦國際書局,販賣左翼報紙和書刊;書局在一九二九年元月開幕,一九三○年搬到京町(博愛路)。台灣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團體一樣,在島內也沒有組織,也是完全透過轉向後的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擴大影響,漸及全島,尤其是青年知識階層。起先這種影響只及台灣青年,但是隨著日本國內共產運動的蓬勃以及經濟的不景氣,在台灣的日本青年中也出現共產主義團體,和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都有聯絡;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台本市古亭町(南昌街、晉江街)出現「第一線讀書會」的集會所,這是「赤色俱樂部」的秘密結社,會員聚此每晚研究共產主義。\n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元月三日,台灣文化協會在臨時總會中終於分裂,由激進工農無產階級運動的勞農派共產主義思想者連溫卿一派,取得文化協會的指導權。蔣渭水、蔡培火以及同情無產階級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左派,只好另闢蹊徑;歷經台灣自治會、台灣同盟會、台灣民黨等組織的嘗試,終於七月十日在台中成立「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政黨。雖然派系有別,但是在蔣渭水派下,一方面發展聯合農工商各階層的民族運動,一方面也認為應該結集勞動者和農民大眾推行階級鬥爭;他們初期在爭取勞動團體農民團體的指導權,或者推動這類團體的成立,頗有成效。台灣民眾黨,在台北州的支持勞動團體有土木工友會、台北土木工友會、台北石工工友會、台北店員會、台北裝箱工友會、台北洋服工友會、台北木工工友會建具指物部、基隆運送從業員會、基隆木工工友會、基隆店員會、蘭陽總工友會;一般團體有汐止民生俱樂部、台北勞動青年會、艋舺勞動青年會;農民團體有蘭陽農業組合。台灣民眾黨,在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各州都擁有勞動團體的支持,除高雄外各州也擁有一般團體的支持,但是在農民團體方面,只有新竹農友組合支持;這因為農民運動,當時已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台灣農民組合」在全島運作,且和轉向的台灣文化協會連結,使得台灣民眾黨難有表現空間。昭和二年的調查,台灣工廠的總數是三千三百四十六家,其中百分之七十七點五,是職工人數不滿十五人的小工廠,一百人以上的工廠僅一百零四家,兩百名以上僅五十八家;礦山總數兩百二十三家中,經常雇傭技工、職工兩百名以上的僅二十二家。工業這樣不發達,因為農林業的發展使得農村過剩人口較少,低工資勞工難得。以後,隨著公共汽車事業的發展,相關交通運輸的產業才有明顯增加。台灣當時的產業分別有紡織、金屬品、機械器具、窯業、化學、食料品、木製品、印刷;其中食品工業(大部分為製糖業)占大半以上,也反映台灣被作為農產地的特性。在這些產業中,台灣人企業主以小企業居多,而就股份公司和合資公司資本額的比較,日本人的資本遠超過台灣人。雖然大正八年起(一九一九),日本勞工運動勃興,其指導思想來自第二共產國際或工團主義,且漸次轉向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中國也開始有工會組成和勞工運動的發展。但是,台灣勞工在台灣總勞動人口中算是極少數(一九三○\n年,台灣的勞工總數為五十七萬七千七百人,其中四十二萬人是流動頻繁的雜工和日薪勞工);由於技術職工為少數日本人占有,台灣勞工的作業主要是加工性質,產業地位很低,甚至於不如農業,因此缺少自發性階級自覺、爭議和團結條件。一九二七年起,由於轉向的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競爭,台灣勞工運動逐漸加深激烈鬥爭的精神,但主要爭議仍在於提高工資、不景氣時反對降低工資等等消極要求。台北勞工運動的樣態,以一九二七年的演講會為例:台灣民眾黨、蔣渭水和五名指導者,在建成町(後火車站)新舞台舉辦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紀念演講會,因言論激進且群眾附和喧鬧,受到解散命令。文化協會台北支部、台灣機械工聯合會等六個團體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台北港町(貴德街)文化講座辦理。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等華僑勞工團體,舉辦中國人勞工團體紀念運動演講會;雖然事先已有不許可之警告,仍然在蔣渭水指導下開會,所以開會同時即遭命令解散。基隆文化協會、平民俱樂部、基隆機械工會、無產青年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基隆市聖王公廟舉辦。以罷工為例:一九二七年,台北工業株式會社所屬採砂石船夫同盟,為排除中間商壟斷而罷工;但,會社因有大量庫存,且臨時雇用十六艘大型採石船採砂,對罷工完全漠視,罷工船只好哀求無條件復工。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罷工和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的勞資爭議,也效果不彰。相關五一勞動節的活動,當然也可參考:一九二八年的勞動節前幾天,台灣民眾黨所組成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向各工場、職場發出全體休業的通知,並計畫室外集會和示威遊行,均被下令禁止,只准往年例行的室內集會演講。基隆市內敲鑼宣傳演講會散佈兩大傳單,將市內參加演講會的各團體會員集合在各工友會事務所,企圖前往會場途中進行示威活動。一九二九年的勞動節,因為去年台灣農民組合遭檢舉、台灣共產黨東京支部及學術研究會瓦解,本島左翼運動遭受極大打擊,文化協會及其指導下的工會也處低迷的狀態;台灣民眾黨雖想乘機擴張,卻無成效。這一年,勞動節的活動大抵僅是休業一天:上午舉行典禮、下午演講、晚間同樂欣賞節目。一九三○年的勞動節,台北在李友三、黃白成枝等工友總聯盟幹部指導下,以登山為名,聚會台北自由勞動者聯盟、台北砂石船友會、台北土木工友會、台灣塗工工友會等團體幹部,在圓山動物園後合唱勞動歌;後來因為舉辦示威運動,被解散,幹部十一人遭拘禁。文化協會系之台灣工友協助會,則在台北川端町(濱新店溪,今廈門街、詔安街、同安街、金門街、水源路一部分)一帶集合,企圖在新店溪泛舟示威運動。一九三一年,台灣民眾黨遭受勒令解散;文化協會台北支部、農民組合台北出張所、台灣工友協助會、台北機械工會、台灣塗工會、台北維新會等左翼團體,召開「五一鬥爭委員會」的募捐組織,乘機擴張影響力。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台北市八甲町(萬華)經營書畫骨董的日籍商人在自宅掛上「高千穗聯盟總部」的招牌,另在九月十三日召開記者會陳述他們的理念。這個聯盟有日籍律師和醫生支援,九月二十四日召開政談演講會。這類在台北的日人右翼團體,另有若竹町(貴陽街二段)四國民報台灣分社社長組成的「台灣租屋人組合」和「社會問題研究會」、惟神教團台灣分社負責人組成為新社、預備及後備役陸海軍受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刺激組成「台北在鄉將校會」、料理店業者組織「大日本正義團台灣支部」……\n這些右翼團體的主張雖有暴力和溫文的差異,基本上仍以日本國粹為主,抗議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和左翼,主張日本政府應強化在台灣的統治;特別是對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引起的國際情勢變動,使日本人有感台灣這個帝國南進基地對於日本國防的重要。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外交上的世界強權表現,就有許多台灣人(包括向來支持民族主義、左翼的知識分子),對日本產生新的幻想,被動或主動的參加「台灣人皇民化」以及「亞細亞民族大團結」的運動;這些台灣人的日本右翼運動,在台北有太平町(延平北路)的「大同促進會」、台北鐵路飯店內的「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在蓬萊閣創立的「大亞洲黎明協會」。由於中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日據時代主要的台灣社會運動,大抵都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起,全面遭受鎮壓逐漸偃旗息鼓。光復後的台北街頭運動十九、二十世紀交替時,日本先後戰勝中國和俄國儼為東亞霸主,再乘歐洲大戰的機會,完成重工業建設而躍為現代化國家。昭和初期起(一九二六),日本國勢已是世界強權,但是先後對中國和美國發動戰爭,終於一九四二年起開始敗退;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八月二十六日,中國宣佈台灣地區日軍受降地點在台北。九月十四日,中國空軍飛來接收台北機場;飛機抵達台北時,低空飛繞市區一周,飛機降落後,機場上和日本機構的日本國旗全被撤去,中華民國國旗冉冉升起。當時,在台灣有日本軍人和警察約二十多萬;其中一些官兵不甘戰敗,叫囂要和台灣同歸於盡,更有法西斯少壯派軍官熱心聯絡台灣人鼓吹獨立。在這種壓力下,中國派出六個師、二十艘軍艦和兩個飛行大隊來台接收;十月十七日,中國陸軍七十軍第七十五師浩浩蕩蕩開進基隆港。軍隊乘火車開赴台北途中,道旁台灣同胞綿延不斷;火車進入台北,三十萬市民給予熱烈歡迎。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台灣各界扶老攜幼擁向台北公會堂(中山堂);門口高掛「慶祝台灣光復」六個大字。上午九時,開始中國戰區台灣省接受日軍投降的典禮;日本對台灣長達五十一年的占領,在鐘聲九響中成為歷史。受降典禮當天下午,台北各界召開慶祝大會,次日又舉行環城大遊行;許多家庭還舉行隆重家祭。\n但是,諸多因素隨即引起混亂,有教養且寶刀未老的台灣思想家,和熟悉各種社會運動的群眾,儼然再次面對「總督府」的巨大陰影,激起了嫉惡的憤怒、正義的血氣,而昔時抗日的中國民族主義轉以「中國」為帝國加以對抗。一批批台灣現代菁英,卻在這段時期中身受即使是在日本異族統治的時代,都不曾目睹的集體屠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隔海對抗中,在台灣的共產黨人(無論中共、台共),下場同樣。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甚至於到戒嚴末期,台北街頭或任何隱密的角落,都因為強力掃蕩,看不到或暗藏任何社會運動的現象或跡象。但是,有些歷史影像和思想,仍然透過私人藏書或口語,繼續流傳;或者因為藏書人過世,沒有思想或無意再思想的子女清除其書房或書架,往舊書攤傾倒,而流傳更廣。隨著中國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北又新進了一批「外省人」(這其實沒什麼可作文章的,每隔一陣子或數十年,台灣島上就會瞬間湧進大批的外國人和外省人);在台北的外省人流亡學生、教職、文化工作者,無論左翼、右翼或自由主義,都有相當表現;但是,比較昔時台灣的現代思想家,那些艱辛奮鬥而提早夭折的逝者,在世界觀以及思想的多元,並無特別超越的。因為同文、同種、同處烽火亂世,算是以倖存者的代表身分,表現出一個消逝時代的偉大餘韻和微光。無論如何,在戒嚴的體制下,台北街頭雖然再看不到社會運動,卻有熱鬧的各種遊行:年度例行的元旦升旗、童子軍、中學儀隊、軍樂隊、好人好事、國軍英雄、模範政士、提前入營青年、雙十國慶、總統華誕、國父誕辰、台灣光復、國貨遊街展;偶發性的美國總統來訪(四十萬人上街歡迎)、菲律賓總統來訪(三十萬人上街歡迎)、奧運選手奪標、亞運選手奪標、女籃國手凱旋、少棒青少棒及青棒英雄奪冠返國……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這些臥薪嚐膽、鼓舞士氣、強化信心或者想給沉悶生活注入一點歡樂喜氣的遊行,多已不再也不必舉行。宗教性的遊行,特別是具有濃厚民俗信仰的大規模信眾遊行,容易被引發為社會運動,也早就被預防性禁絕;時光久遠,台北人忘了自己也曾擁有同樣歷史悠久的,場面隆盛的神明護城消災或繞境祈福慶典:關渡媽祖市區遊行(一九六二)、霞海城隍老爺出巡(一九六三),以至於也想不到再造為社區總體福氣的可能。在法律邊緣以內活動,是社會運動的極限。就此標準來看,最嚴苛的條件下,台北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年間,還有《自由中國》雜誌社等等自由主義者,公開扮演反對者的角色,為後繼的實踐運動暖身。一九七○年代多元勢力、不分省籍、不分統獨的「黨外人士」,開始躍上社會運動闊別久違的台北街頭,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家和藝術工作者,也揮灑筆墨為台灣的民主進步發展推波助瀾;包括一九七八年「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後的「政團」,以及左翼、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作家。議會黨團和政黨理論的建構,也是高雄事件後至一九八二年間,「黨外人士」串聯的佳作。這些社會運動者的堅持努力,以及跟隨在街頭流汗、流淚、流血的各種群眾,踏平了台北街頭的荊棘,才可能有一九八四至八六年,海內外反對人士在康莊大道上整合為民主進步黨的過程。一九八六年的前後,台灣社會已有極大變化;經濟復甦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台灣已經從一個落後、貧困以及面臨經濟崩潰和依賴美援的海島,發展成大量出超、外匯存底近六百億美元的經濟巨人。在政治\n上解除戒嚴、黨禁、報禁等等一連串的作為,也使台灣社會從封閉和管制中解放,自由朝向多元發展。台灣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這樣成功的表現,被國際刮目相看;稱為奇蹟。這經驗顯示,條件充分的情況下,自由的市場經濟也有可能在獨裁專制的政府中快速產生,這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拉丁美洲、東歐以及南亞不成,而在東北亞及新加坡可行的重要因素;癥結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優先順序。中國大陸,目前正循台北和漢城的發展模式。世界在二十世紀末,經歷慘烈且富戲劇性的實驗以後,選擇了自由經濟的制度,並以整體市場運作。回顧人類三種經濟制度:自然經濟、計畫經濟、自由經濟(或混合型經濟),也可以了解台灣在戰後的民主政治發展。台灣全面放任自由經濟之前,採行計畫經濟,實際上帶有中國國民黨原有的社會主義色彩。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社會,除原始社會外大抵都是集權主義的政體;因為,要把分散的自然經濟單位整合為一個體系,要把有關聯且互動的複雜體系加以指導,都必須由「專家」來進行,而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則必須有「總指揮」擔當。這種情況在從計畫經濟過渡到自由經濟體制,也同,因為需要同樣的專權,才能明快解決既得利益團體和階級的強大阻力。這可以是蔣經國具有獨裁推手、早期白色恐怖執行人這樣角色的解釋;但是,正因為他曾經是這樣一個警察國家的首腦,所以他的政權和平轉移,無論有意或偶然,都是他專握大權的最光輝表現。前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JAYTAYLOR),一九六○年代早期,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任職。他曾經在一篇論文中表示,自己本來完全無法想像,中國國民黨那種穩定的獨裁體制,怎麼可能將政權和平轉移給台灣人。後來他調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觀察員」,同時能夠認識兩岸的發展,也知道一些秘聞,而自己做了結論。他說:一九八○\n年代,部分人士開始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終會造成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大震盪;其中一位就是蔣經國。當時,蔣經國以為自己的歲月還很充裕,私下派代表去見即將接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李潔明,告知他自己的政治藍圖,包括自由普選,以及普選後不可避免的「台灣本土化」的結果。當時,大多數島內外的觀察家都還無法預見,接下來的八年中,台灣即將發生的政權和平轉移。其實,自由經濟本身就意味著分權,這是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礎;它也建立在各種團體、各種個人的欲求與意志的自由實現。自由經濟的市場主要原則之一是等價交換,實行等價交換必須承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意志自由、地位平等;在交換的過程中,可以討價還價,但不允許超經濟的權力。法律首先要對自由經濟起保障作用,創造外部的民主環境,限制權力左右市場;在法律這個層面及基礎上,政治的遊戲規則也就同樣適用。這樣的總體環境中,以一九八七年為例,全島一年之間就發生一千八百三十五件群眾運動,動員了近二十七萬三千人次警力;在法律邊緣上,朝野之間有失有得。其中衝突劇烈時,好比示威群眾如果衝撞武警,就可能會被警盾擠壓或警棍悶打得頭破血流、抬上警車,或被噴水車的水龍擊倒在地打滾;有時街上也會冒出示威群眾游擊的瓶裝汽油彈火,或反翻了警車加以焚燒,或喪失了生命。但是混合遊行、演講、鞭炮、煙火、陣頭、舞獅和鑼鼓、演唱或演奏、各種小吃攤檔(二○○四年這種小吃新增了漢堡這樣的菜色),有時的群眾活動,即使是令社會驚心動魄的政治活動,也帶有那種古老台灣同樂熱鬧的廟會喜氣(雖然台灣民間最廣眾的宗教崇拜是「鬼」神信仰)。台灣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除了中壢事件(一九七七)、高雄事件(一九七九),都出現在台北;因為,繼日據時期再續戰後近半世紀的經營發展,台北已經實質成為台灣政、經及文化的中心,街頭上的動靜均為國際觀瞻。自然經濟和計畫經濟,主要是著眼於滿足人的需求;需求是有限度的。自由經濟則著眼於滿足人的欲求;欲求是無止境的。資源分配的老問題,就增加了新的層面和變數,變得更加複雜。而台北這樣的大都會,還有城市問題。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最早出現於奴隸社會,迅速發展於工業革命後,並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加速發展;現代城市,以繁密的交通、通訊以及各種相關生命的資源網絡,聚集了大量甚至於超量的小市民,在其中生產、消費、生老病死。所以,解嚴前後,台北街頭的社會運動除了政治內容,還有別的形色:救援雛妓嚴懲人口販子「彩虹專案」、牙醫上街頭發聲爭取就業權及保障、新約教會教徒車隊(一九八七)、雲林農權總會發動農民赴北請願爆發流血衝突「五二○農民事件」(一九八八)、無住屋團結組織「無殼蝸牛」露宿忠孝東路抗議房租房價不合理(一九八九)、野百合三月學運、萬人街頭遊行反對軍人組閣(一九九○)、要求撤銷核四計畫「反核大遊行」、原住民高喊「還我土地」運動、多個同志團體連辦數場「促進同性戀人權」公聽會(一九九三)、新聞界「為新聞自主而走」(一九九四)、「四一○教改聯盟」全國教師教改遊行、多個社運團體「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一九九五)、彭婉如遇害「女權照夜路」大遊行(一九九六)、白曉燕命案「五一八用腳愛台灣」抗議治安敗壞、為台灣而走「讓青少年站出來」(一九九七)……直到抗議「兩顆子彈等等不公正的總統選舉」藍營選民占領凱達格蘭大道(二○○四)等等。\n有些社會運動,確實是出自「理性」的,像那些出自薪資階層、婦女團體或少數民族,在相關公領域的運動;但是,這種溫和且多歸徒勞的活動,正好說明社會現況是一種難以動搖的巨大實體,而個人是多麼的渺小無力。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