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7 发布 |
- 37.5 KB |
- 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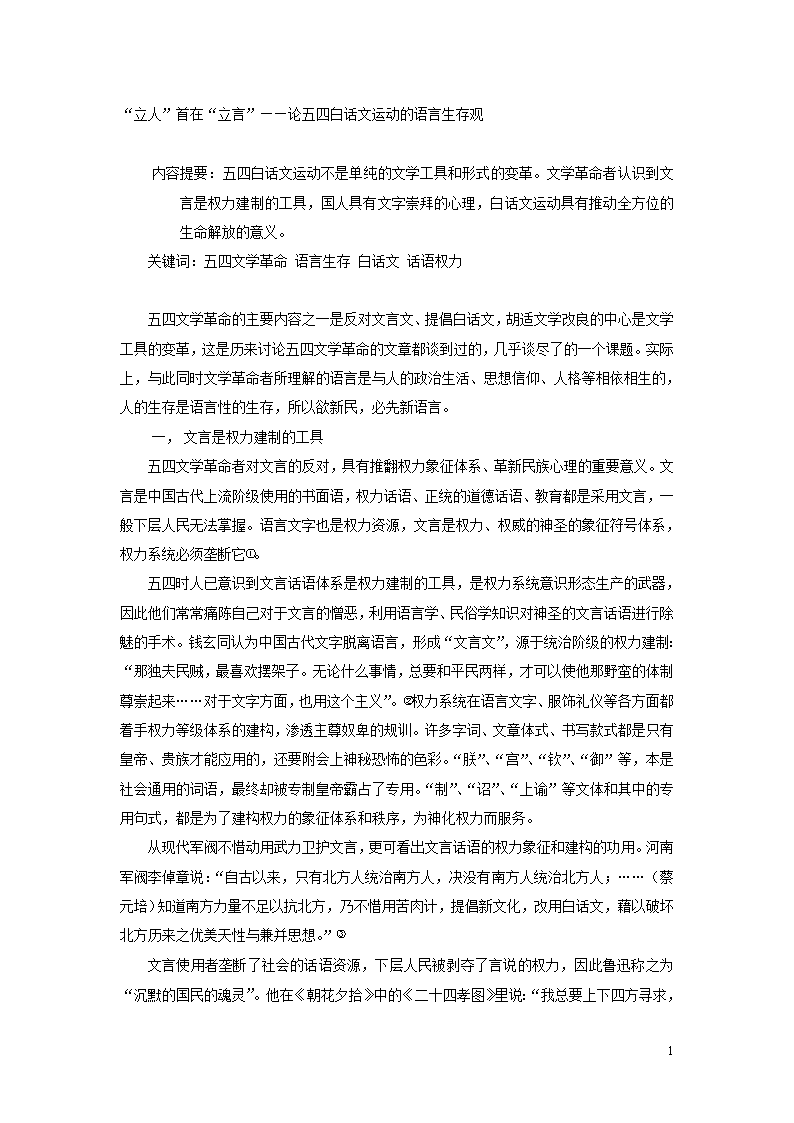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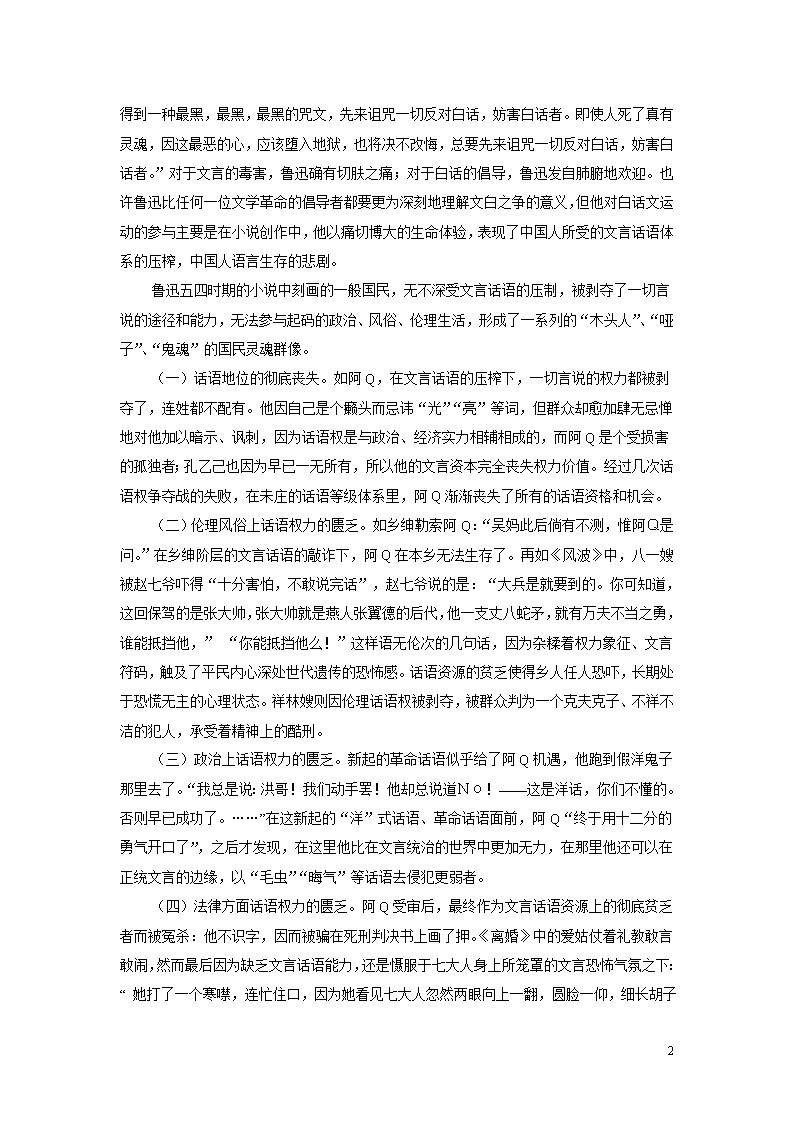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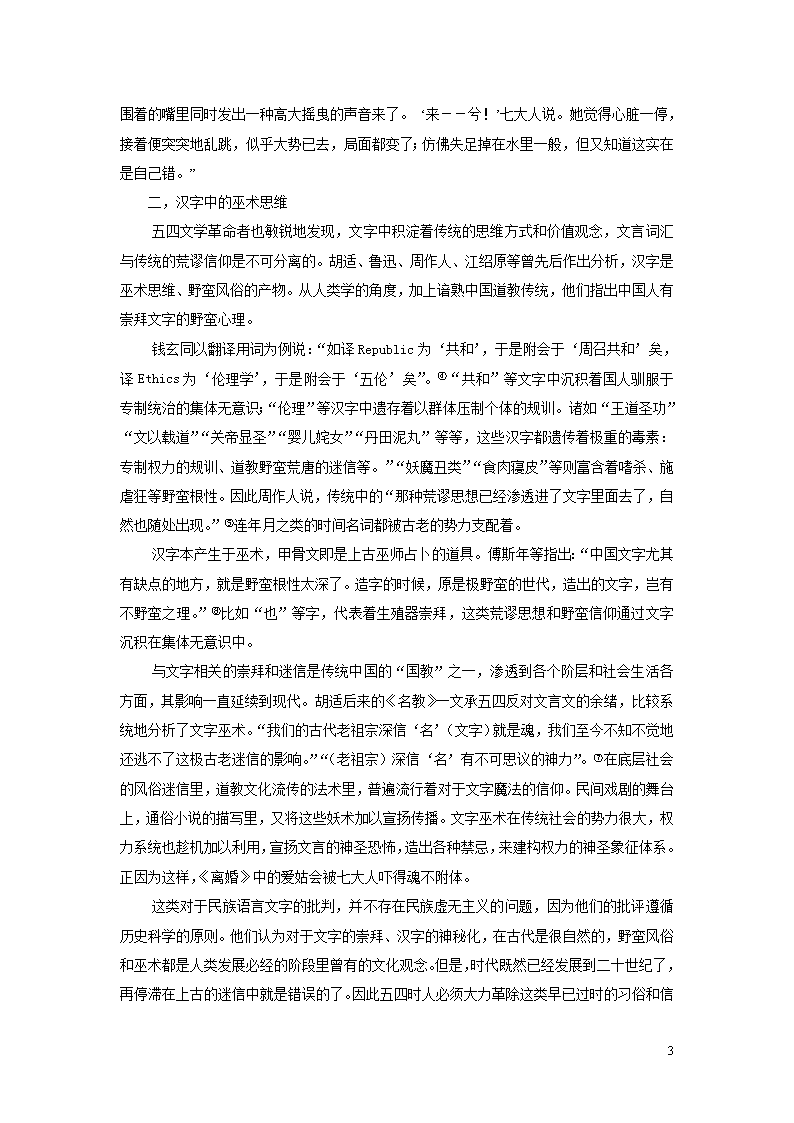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已发表】“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观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内容提要: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语言生存白话文话语权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文学改良的中心是文学工具的变革,这是历来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文章都谈到过的,几乎谈尽了的一个课题。实际上,与此同时文学革命者所理解的语言是与人的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等相依相生的,人的生存是语言性的生存,所以欲新民,必先新语言。一,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五四文学革命者对文言的反对,具有推翻权力象征体系、革新民族心理的重要意义。文言是中国古代上流阶级使用的书面语,权力话语、正统的道德话语、教育都是采用文言,一般下层人民无法掌握。语言文字也是权力资源,文言是权力、权威的神圣的象征符号体系,权力系统必须垄断它【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五四时人已意识到文言话语体系是权力建制的工具,是权力系统意识形态生产的武器,因此他们常常痛陈自己对于文言的憎恶,利用语言学、民俗学知识对神圣的文言话语进行除魅的手术。钱玄同认为中国古代文字脱离语言,形成“文言文”,源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建制:“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一卷文学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页权力系统在语言文字、服饰礼仪等各方面都着手权力等级体系的建构,渗透主尊奴卑的规训。许多字词、文章体式、书写款式都是只有皇帝、贵族才能应用的,还要附会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朕”、“宫”、“钦”、“御”等,本是社会通用的词语,最终却被专制皇帝霸占了专用。“制”、“诏”、“上谕”等文体和其中的专用句式,都是为了建构权力的象征体系和秩序,为神化权力而服务。从现代军阀不惜动用武力卫护文言,更可看出文言话语的权力象征和建构的功用。河南军阀李倬章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决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蔡元培)知道南方力量不足以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与兼并思想。”玄珠:《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35页文言使用者垄断了社会的话语资源,下层人民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力,因此鲁迅称之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在《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里说:“5\n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对于文言的毒害,鲁迅确有切肤之痛;对于白话的倡导,鲁迅发自肺腑地欢迎。也许鲁迅比任何一位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都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文白之争的意义,但他对白话文运动的参与主要是在小说创作中,他以痛切博大的生命体验,表现了中国人所受的文言话语体系的压榨,中国人语言生存的悲剧。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中刻画的一般国民,无不深受文言话语的压制,被剥夺了一切言说的途径和能力,无法参与起码的政治、风俗、伦理生活,形成了一系列的“木头人”、“哑子”、“鬼魂”的国民灵魂群像。(一)话语地位的彻底丧失。如阿Q,在文言话语的压榨下,一切言说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连姓都不配有。他因自己是个癞头而忌讳“光”“亮”等词,但群众却愈加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暗示、讽刺,因为话语权是与政治、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而阿Q是个受损害的孤独者;孔乙己也因为早已一无所有,所以他的文言资本完全丧失权力价值。经过几次话语权争夺战的失败,在未庄的话语等级体系里,阿Q渐渐丧失了所有的话语资格和机会。(二)伦理风俗上话语权力的匮乏。如乡绅勒索阿Q:“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在乡绅阶层的文言话语的敲诈下,阿Q在本乡无法生存了。再如《风波》中,八一嫂被赵七爷吓得“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赵七爷说的是:“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你能抵挡他么!”这样语无伦次的几句话,因为杂糅着权力象征、文言符码,触及了平民内心深处世代遗传的恐怖感。话语资源的贫乏使得乡人任人恐吓,长期处于恐慌无主的心理状态。祥林嫂则因伦理话语权被剥夺,被群众判为一个克夫克子、不祥不洁的犯人,承受着精神上的酷刑。(三)政治上话语权力的匮乏。新起的革命话语似乎给了阿Q机遇,他跑到假洋鬼子那里去了。“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在这新起的“洋”式话语、革命话语面前,阿Q“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之后才发现,在这里他比在文言统治的世界中更加无力,在那里他还可以在正统文言的边缘,以“毛虫”“晦气”等话语去侵犯更弱者。(四)法律方面话语权力的匮乏。阿Q受审后,最终作为文言话语资源上的彻底贫乏者而被冤杀:他不识字,因而被骗在死刑判决书上画了押。《离婚》中的爱姑仗着礼教敢言敢闹,然而最后因为缺乏文言话语能力,还是慑服于七大人身上所笼罩的文言恐怖气氛之下:“5\n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七大人说。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二,汉字中的巫术思维五四文学革命者也敏锐地发现,文字中积淀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言词汇与传统的荒谬信仰是不可分离的。胡适、鲁迅、周作人、江绍原等曾先后作出分析,汉字是巫术思维、野蛮风俗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加上谙熟中国道教传统,他们指出中国人有崇拜文字的野蛮心理。钱玄同以翻译用词为例说:“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Ethics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一卷文学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第164页“共和”等文字中沉积着国人驯服于专制统治的集体无意识;“伦理”等汉字中遗存着以群体压制个体的规训。诸如“王道圣功”“文以载道”“关帝显圣”“婴儿姹女”“丹田泥丸”等等,这些汉字都遗传着极重的毒素:专制权力的规训、道教野蛮荒唐的迷信等。”“妖魔丑类”“食肉寝皮”等则富含着嗜杀、施虐狂等野蛮根性。因此周作人说,传统中的“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透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周作人:《思想革命》,钟叔和编《周作人文类编①·中国气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连年月之类的时间名词都被古老的势力支配着。汉字本产生于巫术,甲骨文即是上古巫师占卜的道具。傅斯年等指出:“中国文字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49页比如“也”等字,代表着生殖器崇拜,这类荒谬思想和野蛮信仰通过文字沉积在集体无意识中。与文字相关的崇拜和迷信是传统中国的“国教”之一,渗透到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胡适后来的《名教》一文承五四反对文言文的余绪,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文字巫术。“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极古老迷信的影响。”“(老祖宗)深信‘名’有不可思议的神力”。胡适:《名教》,《胡适文存三集·一》,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91页在底层社会的风俗迷信里,道教文化流传的法术里,普遍流行着对于文字魔法的信仰。民间戏剧的舞台上,通俗小说的描写里,又将这些妖术加以宣扬传播。文字巫术在传统社会的势力很大,权力系统也趁机加以利用,宣扬文言的神圣恐怖,造出各种禁忌,来建构权力的神圣象征体系。正因为这样,《离婚》中的爱姑会被七大人吓得魂不附体。这类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批判,并不存在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批评遵循历史科学的原则。他们认为对于文字的崇拜、汉字的神秘化,在古代是很自然的,野蛮风俗和巫术都是人类发展必经的阶段里曾有的文化观念。但是,时代既然已经发展到二十世纪了,再停滞在上古的迷信中就是错误的了。因此五四时人必须大力革除这类早已过时的5\n习俗和信仰,它们不独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也渗透在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三,白话的建立有助于个体生命的解放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批评胡适的白话文改革是形式主义的,胡适自己的表述也导致了人们的误解,因为他一贯强调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第一步是工具的革命。其实胡适等人非常深刻地涉及到了白话所具有的生命解放的价值。反对文言文,即是将国人从专制权力的符号体系的威压、文字巫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它也是语言生存的革命、心理的革命、个性的全方位解放。人的生存是语言生存,他的思想、人格、感情、欲望、社会政治生存等等,全都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承认白话的价值,主张白话使用的权力,事实上即意味着白话话语主体的被发现和确立。由于现代人即语言动物,语言在生命各层次渗透的深刻性、根本性,所以白话文革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营白话生存的人民的革命:从心理、思想感情、欲望到社会政治生存,全都得到独立的权力。从此,个体有可能无所顾忌的自由表现和传达自己的情感、思想、印象,个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借语言直接表述出来,再也没有不必要的障碍。外部的社会革命里,“民国公民”的政治身份被承认;与之相比,白话文革命带来的心理、感情、人格等全方位生命解放的可能,则具有更重大深远的意义。语言与生命合一,立人首在立言。由于白话文革命关涉到诸如民族个体生命的全方位独立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林纾会跑出来,反对“都下引车卖浆之徒”“京津之稗贩”使用的语言有作为书面语、文学语言的价值,正可见林纾等维护权贵既有地位的潜意识,根深蒂固的独享文化特权的保守性,这些特权和权威的魅力便首先集结在神圣的文言符号体系上。章士钊称文化的精华只“为最少数人之所独擅,而非士民众庶之所共喻”,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98页则更是暴露了士人的国师情结,他们仍然幻想掌控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专制分享权力。所以吴稚晖一针见血批评反对白话者,“只有那班亡国大夫,瘟国官僚,借着他那种提倡‘上圣德颂’的精神,暗暗欢喜,可以巩固他们的老局面。……保固‘学士大夫’的局面……”吴稚晖:《友丧》,《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08页平民口中的语言既然可以取代过去上流阶级的文言,也就意味着上流阶级在权力身份、心理优越感方面的丧失。白话文革命也利用日渐“当权”的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构造自己的合法性。胡适力斥文言是枯死的,而“乡曲愚夫、闾巷妇稚”的语言却是活的。谈的虽然是语言的变迁,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价值重估:普通平民的精神生活价值、文化生产能力其实是高于贵族、文人学者的!胡适所谓言语必须“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多少利用了平民主义话语来为白话文壮威。早年胡适总是不忘对平民大唱颂歌,“国语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文人与文法学者全不曾过问。……我们对于这种玄妙的变化,不能不脱帽致敬……”胡适:《国语与国语文法》,《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32页附:作者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暨南大学真茹23号415室510632电子邮箱:zengfeng499@sohu.comyedu49@tom.com电话:13244847755020382148775\n白话文革命的理论前提是胡适及五四时人对于现代国民的想象:人格独立的、有文化、富理性的公民。其中暗含着对现代民族个体的构想,有比较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到后来各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相继产生影响,新作家便更企图以人人都懂的白话文学来消融个体之间的隔阂,以造人人平等独立的大同社会。自然,白话文话语权力的确认,只是带来了生命解放的部分可能性,因为一则生命解放是系统的、多方面的,不是单有语言、文学革命就能竟全功的;二则白话本身虽然具有重大的生命解放价值,但它也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它的词汇、实际的言语应用,同样是传统的结晶,也可能充斥着负面信息,并没有一种“纯洁的正确的”的白话;第三,五四时所谓的“平民”有很重的幻想色彩,白话文运动的主体和受众里实际上很少下层平民,而主要是各类知识分子。5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