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4-28 发布 |
- 37.5 KB |
- 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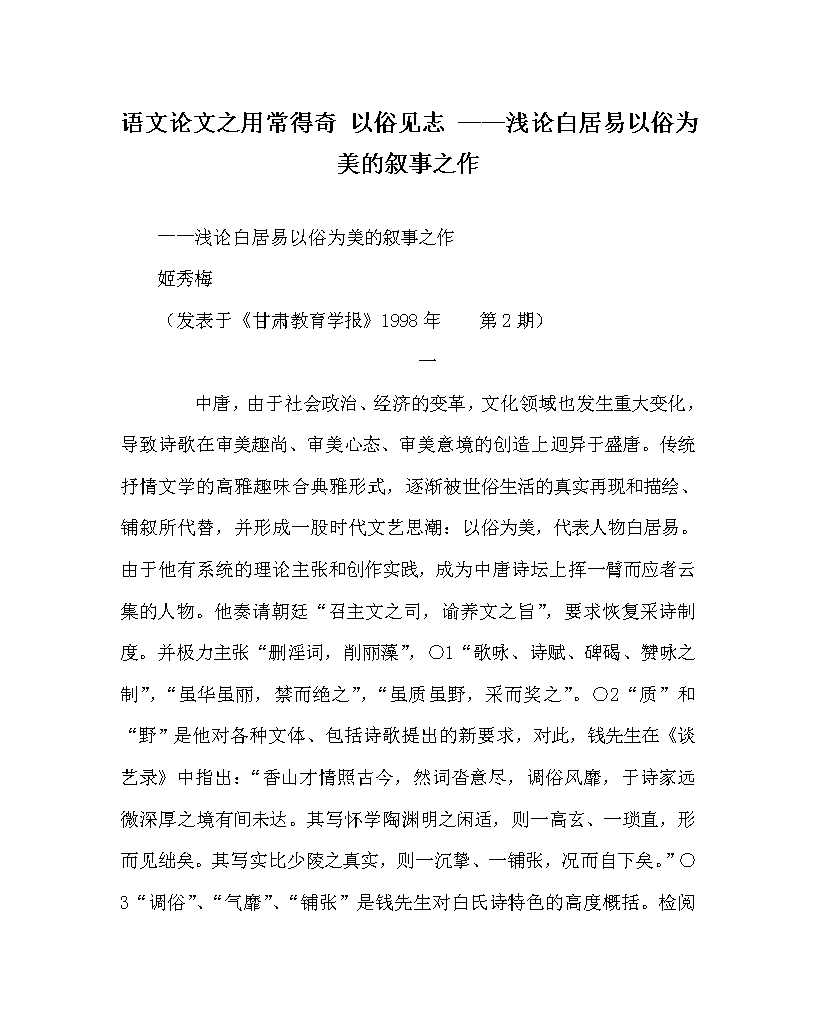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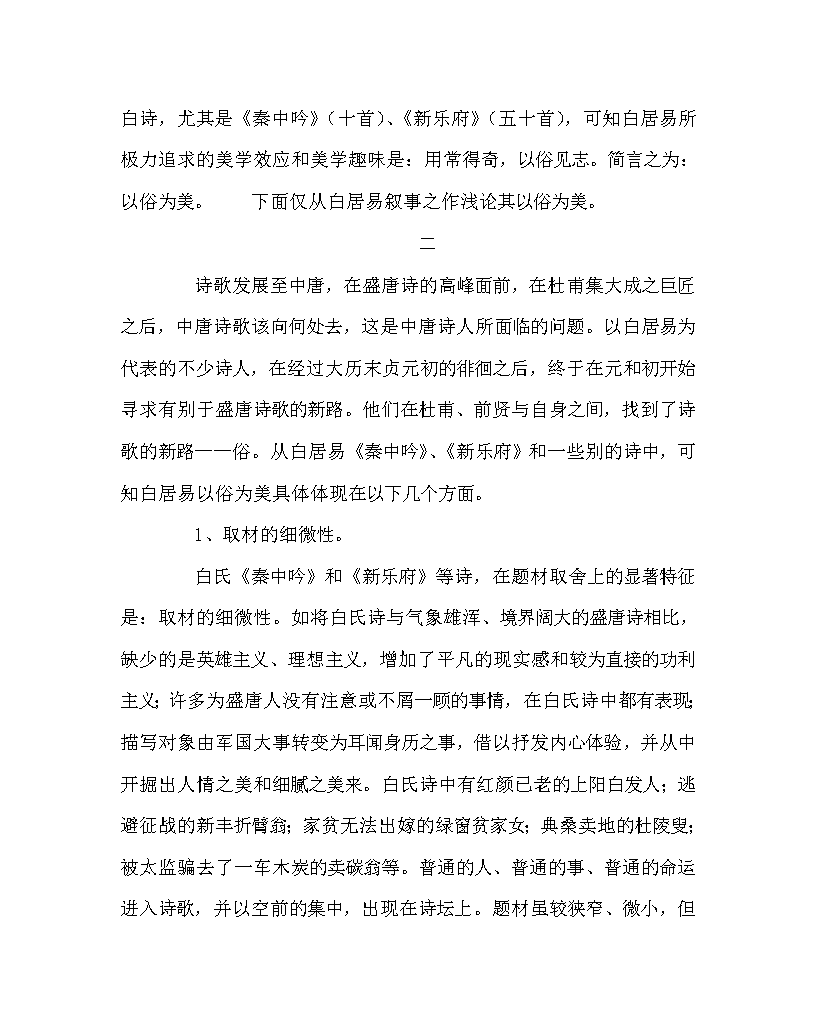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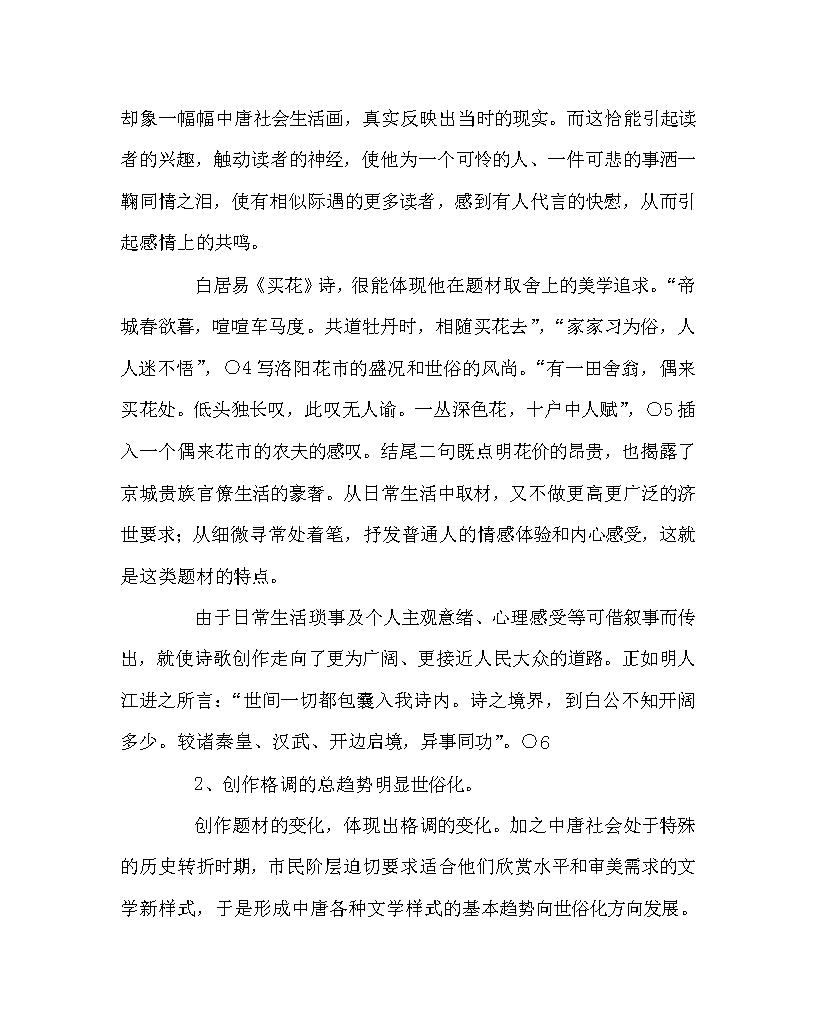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语文(心得)之用常得奇 以俗见志 ——浅论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叙事之作
语文论文之用常得奇 以俗见志 ——浅论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叙事之作 ——浅论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叙事之作 姬秀梅 (发表于《甘肃教育学报》1998年 第2期) 一 中唐,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文化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诗歌在审美趣尚、审美心态、审美意境的创造上迥异于盛唐。传统抒情文学的高雅趣味合典雅形式,逐渐被世俗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描绘、铺叙所代替,并形成一股时代文艺思潮:以俗为美,代表人物白居易。由于他有系统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成为中唐诗坛上挥一臂而应者云集的人物。他奏请朝廷“召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要求恢复采诗制度。并极力主张“删淫词,削丽藻”,○1“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虽质虽野,采而奖之”。○2“质”和“野”是他对各种文体、包括诗歌提出的新要求,对此,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指出:“香山才情照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风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陶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实,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3“调俗”、“气靡”、“铺张” 是钱先生对白氏诗特色的高度概括。检阅白诗,尤其是《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可知白居易所极力追求的美学效应和美学趣味是:用常得奇,以俗见志。简言之为:以俗为美。 下面仅从白居易叙事之作浅论其以俗为美。 二 诗歌发展至中唐,在盛唐诗的高峰面前,在杜甫集大成之巨匠之后,中唐诗歌该向何处去,这是中唐诗人所面临的问题。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不少诗人,在经过大历末贞元初的徘徊之后,终于在元和初开始寻求有别于盛唐诗歌的新路。他们在杜甫、前贤与自身之间,找到了诗歌的新路——俗。从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和一些别的诗中,可知白居易以俗为美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取材的细微性。 白氏《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诗,在题材取舍上的显著特征是:取材的细微性。如将白氏诗与气象雄浑、境界阔大的盛唐诗相比,缺少的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增加了平凡的现实感和较为直接的功利主义;许多为盛唐人没有注意或不屑一顾的事情,在白氏诗中都有表现;描写对象由军国大事转变为耳闻身历之事,借以抒发内心体验,并从中开掘出人情之美和细腻之美来。白氏诗中有红颜已老的上阳白发人;逃避征战的新丰折臂翁;家贫无法出嫁的绿窗贫家女;典桑卖地的杜陵叟;被太监骗去了一车木炭的卖碳翁等。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普通的命运进入诗歌,并以空前的集中,出现在诗坛上。题材虽较狭窄、微小,但却象一幅幅中唐社会生活画,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现实。而这恰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触动读者的神经,使他为一个可怜的人、一件可悲的事洒一鞠同情之泪,使有相似际遇的更多读者,感到有人代言的快慰,从而引起感情上的共鸣。 白居易《买花》诗,很能体现他在题材取舍上的美学追求。“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4写洛阳花市的盛况和世俗的风尚。“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5插入一个偶来花市的农夫的感叹。结尾二句既点明花价的昂贵,也揭露了京城贵族官僚生活的豪奢。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又不做更高更广泛的济世要求;从细微寻常处着笔,抒发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这就是这类题材的特点。 由于日常生活琐事及个人主观意绪、心理感受等可借叙事而传出,就使诗歌创作走向了更为广阔、更接近人民大众的道路。正如明人江进之所言:“世间一切都包囊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6 2、创作格调的总趋势明显世俗化。 创作题材的变化,体现出格调的变化。加之中唐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市民阶层迫切要求适合他们欣赏水平和审美需求的文学新样式,于是形成中唐各种文学样式的基本趋势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众多的眼光不再向上,而是向下,向世俗化、大众化着眼。同样,白居易为代表的作家群也以世俗的眼光评价生活、反映生活。苏轼再评论此时白氏作品时说:“乐天善长篇,但格制不高”○7。张戒也说他:“其气卑弱,其辞浅近”○8。“格制不高”和“其气卑弱”恰好点出了白氏诗在格调上的特征,换言之,浅切而缺乏风骨。他着眼于某个普通人的命运,而非军国要事。有的只是春种秋收的生活现实和一身、一家、一地平安富庶的愿望,缺少高远宏伟的人生理想和豪迈奋激的追求、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当年一小吏的老杜犹有“窃比稷与契”的理想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9的广阔胸怀,而在白诗中却只见“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10的小惠。其《新丰折臂翁》最能体现其诗格调之特色。诗中所写之人是“深夜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垂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11的一老翁,并非希冀在边庭建功立业者;是一个为免“不然当时沪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12的自折手臂免去征役之苦的世俗之人,并非战死疆场名垂青史的英雄。虽此一管,可窥白氏诗格调之全豹。 3、语言的浅直和写法的“肆”。 白居易对乐府诗的创作提出了诸多原则。其中对语言的要求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13;体制上的要求是:“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创作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4。与之同趣的元稹则说:“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旁古人”○15。不求“高”、“奇”,而要用“当时语”,此乃白氏诗之语言特色。细观白居易《秦中吟》和《新乐府》可知,其诗语言浅俗晓畅,没有或很少有普通百姓难于理解的意象,看不到雕琢的语句,过多的典故、华丽的词藻,而以精心提炼的口头语,表达一种质朴的、与普通民众切近的心理体验与情感。 白氏诗中,语言的浅俗俯拾即是:“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西凉使》);“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杜陵叟》);“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上阳白发人》);“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红线毯》)等等。如上诸诗读来平浅易懂,写法上灵活自由,不拘一格;不拘泥于诗格、平仄的限制和束缚,充分体现出“肆”的特点。读其诗,似觉不经意、不惊人,但蕴含十足,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官与民之间的尖锐矛盾。 正因如此,白氏诗流传极广。这除其它原因之外,主要因素当属语言的浅显易懂了。在彭乘《墨客挥犀》中有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乃录之;不解,则又易之。”○16故事的真实性权且不论,但从侧面可见白居易在语言的大众化上所下的功夫、取得的成就;用平显的语言取得最佳的艺术效果,用袁梅的话说:“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哉,此妙谁探?”⒄ 4、体制的合乐可歌性。 白氏诗歌能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能拥有鲜有人比的众多读者,除上述三方面因素之外,诗的合乐可歌性也是不可忽视的。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阐述乐府诗体制上的特色时明确指出“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府歌曲也”。可以播于乐章歌曲是其《秦中吟》、《新乐府》的显著特征。这一点,也和当时社会市民阶层追求享受、娱乐的口味相适应。这个新兴的阶层,要求不高,品味也不算高雅。而白氏诗在题材、格调、语言、体制的配乐哥歌性上正好满足了当时这一广泛社会阶层的浅俗需求,因而受到广泛欢迎。元稹在谈到白氏诗的影响时说,二十多年来,白居易诗歌,“在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写者,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咏唱者”,“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⒅。白居易自己也无不自豪地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⒆吟咏传唱之人,上至王公、下至妾妇、牛童、马走;场所可以是宴宾之庭,也可是市井、僻野,其流传之广、范围之大、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盛唐李杜之诗。 尤其是其《新乐府》诗,音律上注意或平、或仄、灵活换韵,读来音乐感极强,声调铿锵,增加了诗的感染力。正因为白氏充分利用诗歌艺术的音乐性进行创作,并采用传统歌谣体,加之他本人在音乐上高超造诣、题材的细微、语言的浅俗、体制上的“顺”而“肆”,使中唐诗在继盛唐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面目。这种新面目的形成是由诗人们的创作趣味、美学追求,与当时市民阶层的浅俗审美水平完全合拍所产生的双重效应,正是这种双重效应,自觉不自觉的将中唐诗歌推向了世俗化的高峰。 三 综上所述,白居易诗歌取材的细微性、格调总趋势的俗化、语言的浅切平易及写法的“肆”、体制的配乐可歌性可概括为“常”、“俗”二字。“常”既指白氏诗歌题材的平常,也指其诗意境较狭、体制灵便、格调浅切。“俗”并不仅仅指白氏诗语言艺术的通俗易懂,主要是指在审美趣味上的世俗化,同时引起诗歌从题材到格调、语言、结构等一系列变化。几千年来,正统文学中诗的传统抒情样式已在人们心理形成定式,要打破这种格局、定式,实现诗歌“常”、“俗”之变,绝非易事。而白居易恰在这方面做了突破、创新,可谓开一代先河。正如刘熙载所云:“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20。白居易就是用看似极“常”之审美对象、再现方法,极“俗”之审美趣尚,达到“奇”特的审美效果,并表现自己的审美“志”趣的,即:“用常得奇”,以俗见志。 为此,白居易在其叙事诗,尤其《新乐府》中,采取了这样的方式:“首句标其目”,使人一目了然;“卒章显其志”,用以画龙点睛;内容 “事核而实”,且一首咏一事,持一旨,不杂不复;语言“质而径”、“直而切”,浅切流畅,便于理解、传播;体制篇幅“顺而肆”,便于“播于乐章歌曲”;叙事用虚词、散句打破传统诗歌对称、回环的韵律,变高度浓缩跳跃的情思为连贯明白的叙述,使诗在体制格律上得到解放。用白居易的话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21 由于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创作主张及方法,就使原本零乱,随意的创作变得旨臆明确,结构完整而又次序分明。读其叙事诸作,不难发现“常”、“俗”方式所取得的美学效应。“常”、“俗”的确为白居易诗歌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唐诗歌开拓出了发展的新途径。有一点也许连白居易自己也未意识到,就是由于他的变新与开创,使诗歌从典雅神圣的庙堂下放到世俗人间贵族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成为平民文学的一部分。 当然,以俗为美作为中唐的一种审美时尚,并非发端于白居易。这种世俗化的诗歌美学追求,早在杜甫和顾况时已露端倪,只不过他二人并未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这一审美追求的自觉化以张籍、王建为开端,至白居易手中发展而成一时风尚。这是和当时文学的其它样式世俗化的倾向同步合流的。唐中期以后,讲经文、变文、话本、传奇小说等空前兴盛并日趋通俗化、自觉化,而与诗有关的姊妹艺术音乐、绘画、雕塑也无一例外地卷入这股时代文艺思潮中。这些思潮的形成,除文体革新带来的文学功能演变的自身规律外,更是庶文化转型的生动体现。随着庶族阶层政治力量日渐强大,世俗化之“鼓扇轻浮”○22之风亦随进士之盛而起。这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庶族寒士带来的世俗之风,使原有士族文化受到冲击亦随之俗化起来。于是俗文学空前兴盛,它不仅活跃于民间市井,而且通过“行卷”之风带入朱门深禁。因此,元和年间俗文学形式盛行,实际正体现了士庶文化转型通过文人心理积淀而成的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与审美志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审美志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唐社会人们在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上的总体现。 也正是由于尚俗审美趣味对雅文学的冲击、影响、渗透,进而造成诗歌创作中记俗事、并着意于琐细情事本身的铺叙。元和诗坛,都显示出由写实原则到叙事笔调的演化。不用说元、白《新乐府》、《秦中吟》等标明叙事的作品,连《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悲善才》等感伤诗的具体内容亦重事件本身情节的推展、铺叙、着眼点亦往往在于“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23,所叙多为日常生活中俗事琐事。象王建《新嫁娘词》、张籍《江南曲》、刘禹锡《竹枝词》等都是这一世俗化趋向的典型体现。元稹所谓“新进小生”对白氏诗中轻俗一面的“妄相仿效”,实际就是“常”“俗”时风向诗坛渗透的表现,也正是俗文化浪潮日益发展、高涨的表征,是时代审美趣味的转变和时代社会文化氛围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居易“用常得奇”,以俗见志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崇尚,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志趣,而是体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样式由“雅”向“俗”转关的趋势。从此,文学沿两条路走:一条承袭中唐诗歌抒写内心绪的链条,向新体抒情诗——“词”发展,形成了花间词和北宋婉约词;另一条则由中唐开端的市民文学沿叙事文学的道路,经话本、诸宫调、元杂剧到明清小说,戏剧发展成熟、蔚为大观,并逐渐取代了抒情文学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主流。 注释 ○1○2《策林》六十八。 ○3见《谈艺录》。 ○4、○5见《白居易集》卷三。 ○6江进之《雪涛小书》。 ○7《唐音癸签》卷七引。 ○8张戒《岁寒堂诗话》。 ○9《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 ○10《醉后狂言酬萧、殷二协律》。 ○11、○12《新丰折臂翁》。 ○13《新乐府序》。 ○14《寄唐生》。 ○15《酬孝前见赠》十首之二。 ○16《墨客挥犀》。 ○17《续诗品》。 ○18《白氏长庆集序》。 ○19《与元九书》。 ○20《艺概》(二)。 ○21《新乐府序》。 ○22孙启《白里志序》。 ○23《唐音癸签》卷七。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