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31 发布 |
- 37.5 KB |
- 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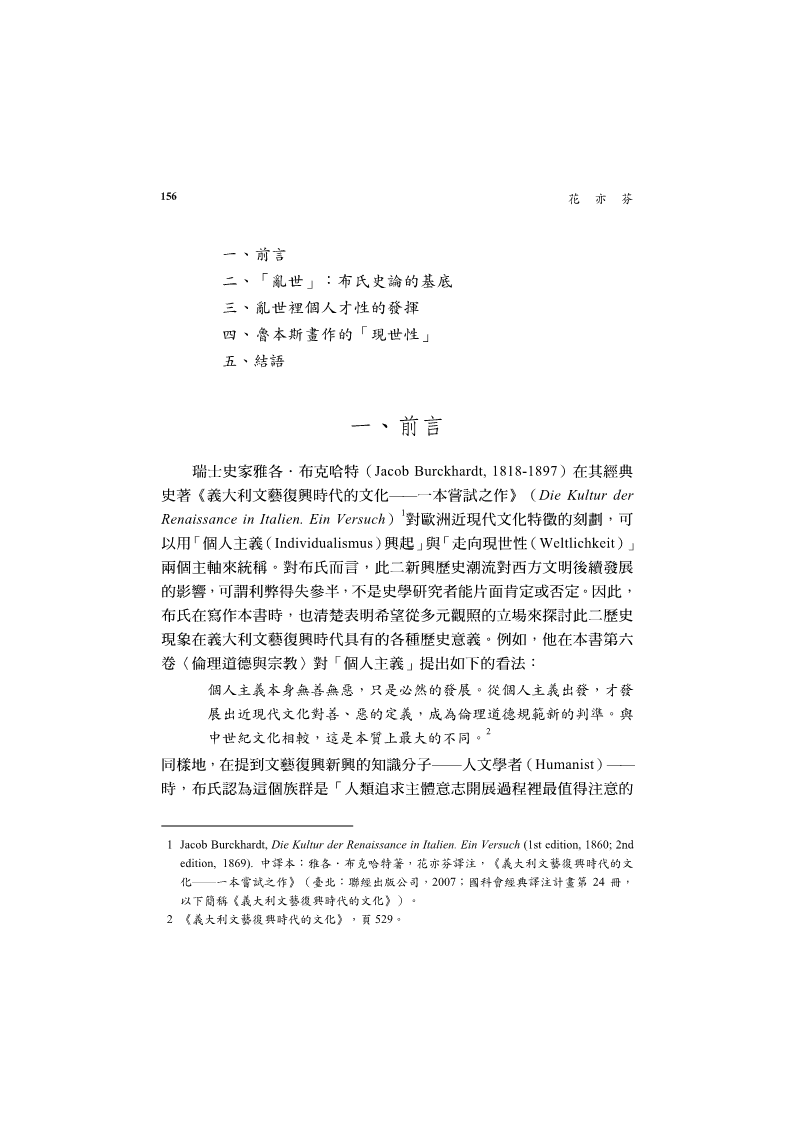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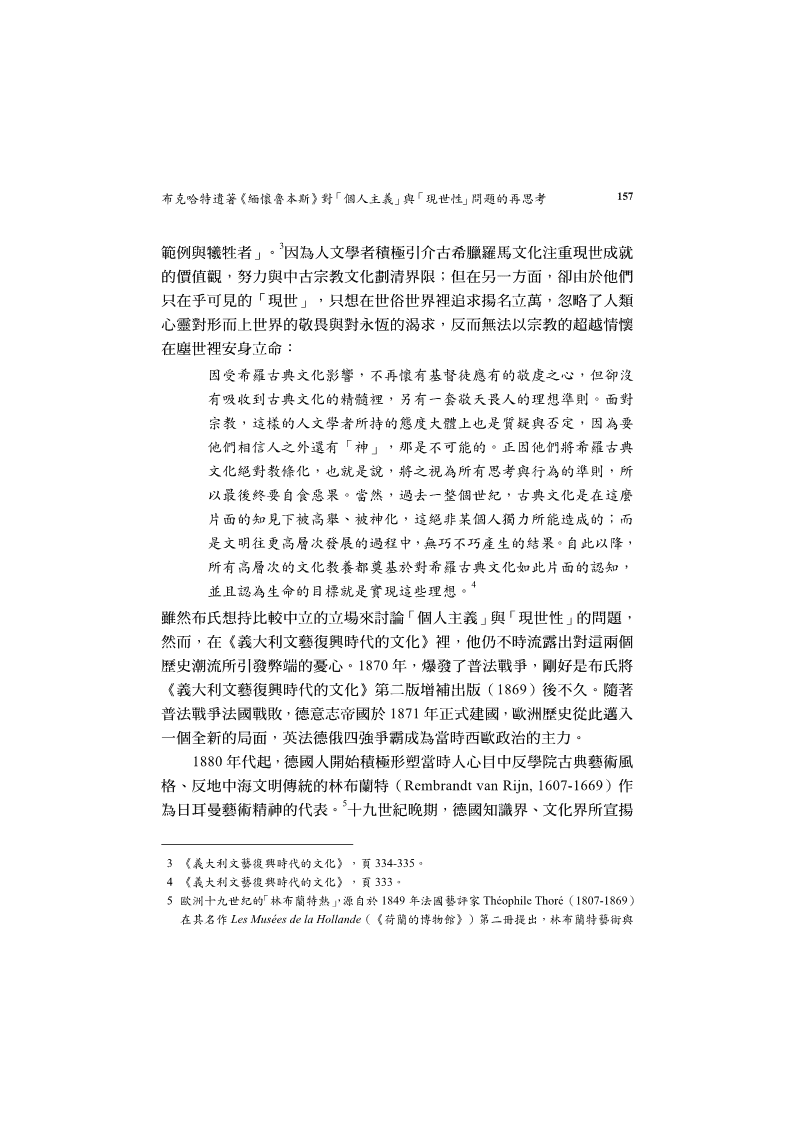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台大历史学报》第45期 页155-219
臺大歷史學報第45期BIBLID1012-8514(2010)45p.155-2192010年6月,頁155-2192010.4.9收稿,2010.6.25通過刊登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花亦芬提要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1818-1897)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KulturderRenaissanceinItalien.EinVersuch)以「個人主義興起」與「走向現世性」兩個主軸來刻劃歐洲近現代文化的特徵。對布氏而言,此二新興歷史潮流對西方文明後續發展的影響,可謂利弊得失參半,不是史學研究者能片面加以肯定或否定。然而,布氏在晚年卻親眼目睹,不少人對這兩個歷史潮流的理解,受到當時流行的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1844-1900)「超人」哲學影響,在片面解讀下,轉而對他原本從多元角度論述這兩個現象所闡發出來的豐富歷史內涵開始產生誤解。鑑於布氏晚年面對的困擾,本文將探討,布氏在生命最後階段如何藉由最後一本著作——《緬懷魯本斯》(ErinnerungenausRubens)——來處理自己史學論述被誤解的問題。針對「個人主義」,本文提出,布氏以「全才」取代十九世紀德意志社會熱衷崇拜的天才∕英雄∕強者。在這個部分,布氏認為,魯本斯(PeterPaulRubens,1577-1640)的「全才」特質為後世留下的楷模,勝過「天才」以強烈個人主義性格所留下來的正負面影響。在另一方面,本文指出,《緬懷魯本斯》對「現世性」問題的探討,跳脫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將「現世性」當成文藝復興以降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來看待的論述取徑。布氏在《緬懷魯本斯》裡想進一步探討:歐洲近現代人如何理解去基督教化後現世真實的意涵?而現世真正的幸福又該如何創造?在《緬懷魯本斯》一書裡,布氏將魯本斯這位「全人型的個人」刻劃為亂世裡仍懂得堅持文化創造主體性與追求人倫幸福的典範,為走向「現世性」近現代文明的歐洲立下足資仿效的楷模。透過對魯本斯藝術成就的推崇,布氏希望矯正十九世紀寫實主義以「表象真實」為尚的「現世」認知觀,從而喚醒具有深刻歷史反省的「現世」人文關懷;並在此基礎上,促使當代德意志文化揚棄用進步史觀形塑強者文化的風潮,而能正視建構健康明朗現世精神文化的重要意義。關鍵詞: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魯本斯(PeterPaulRubens)個人主義現世性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E-mail:yfhua@ntu.edu.tw。\n156花亦芬一、前言二、「亂世」:布氏史論的基底三、亂世裡個人才性的發揮四、魯本斯畫作的「現世性」五、結語一、前言瑞士史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1818-1897)在其經典史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Kulturder1RenaissanceinItalien.EinVersuch)對歐洲近現代文化特徵的刻劃,可以用「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us)興起」與「走向現世性(Weltlichkeit)」兩個主軸來統稱。對布氏而言,此二新興歷史潮流對西方文明後續發展的影響,可謂利弊得失參半,不是史學研究者能片面肯定或否定。因此,布氏在寫作本書時,也清楚表明希望從多元觀照的立場來探討此二歷史現象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具有的各種歷史意義。例如,他在本書第六卷〈倫理道德與宗教〉對「個人主義」提出如下的看法:個人主義本身無善無惡,只是必然的發展。從個人主義出發,才發展出近現代文化對善、惡的定義,成為倫理道德規範新的判準。與2中世紀文化相較,這是本質上最大的不同。同樣地,在提到文藝復興新興的知識分子——人文學者(Humanist)——時,布氏認為這個族群是「人類追求主體意志開展過程裡最值得注意的1JacobBurckhardt,DieKulturderRenaissanceinItalien.EinVersuch(1stedition,1860;2ndedition,1869).中譯本:雅各.布克哈特著,花亦芬譯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第24冊,以下簡稱《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2《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29。\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573範例與犧牲者」。因為人文學者積極引介古希臘羅馬文化注重現世成就的價值觀,努力與中古宗教文化劃清界限;但在另一方面,卻由於他們只在乎可見的「現世」,只想在世俗世界裡追求揚名立萬,忽略了人類心靈對形而上世界的敬畏與對永恆的渴求,反而無法以宗教的超越情懷在塵世裡安身立命:因受希羅古典文化影響,不再懷有基督徒應有的敬虔之心,但卻沒有吸收到古典文化的精髓裡,另有一套敬天畏人的理想準則。面對宗教,這樣的人文學者所持的態度大體上也是質疑與否定,因為要他們相信人之外還有「神」,那是不可能的。正因他們將希羅古典文化絕對教條化,也就是說,將之視為所有思考與行為的準則,所以最後終要自食惡果。當然,過去一整個世紀,古典文化是在這麼片面的知見下被高舉、被神化,這絕非某個人獨力所能造成的;而是文明往更高層次發展的過程中,無巧不巧產生的結果。自此以降,所有高層次的文化教養都奠基於對希羅古典文化如此片面的認知,4並且認為生命的目標就是實現這些理想。雖然布氏想持比較中立的立場來討論「個人主義」與「現世性」的問題,然而,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裡,他仍不時流露出對這兩個歷史潮流所引發弊端的憂心。1870年,爆發了普法戰爭,剛好是布氏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第二版增補出版(1869)後不久。隨著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德意志帝國於1871年正式建國,歐洲歷史從此邁入一個全新的局面,英法德俄四強爭霸成為當時西歐政治的主力。1880年代起,德國人開始積極形塑當時人心目中反學院古典藝術風格、反地中海文明傳統的林布蘭特(RembrandtvanRijn,1607-1669)作5為日耳曼藝術精神的代表。十九世紀晚期,德國知識界、文化界所宣揚3《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334-335。4《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333。5歐洲十九世紀的「林布蘭特熱」,源自於1849年法國藝評家ThéophileThoré(1807-1869)在其名作LesMuséesdelaHollande(《荷蘭的博物館》)第二冊提出,林布蘭特藝術與\n158花亦芬的林布蘭特形象,是一位洋溢個人主義色彩,中晚年因為破產開始離群索居,但仍以獨立創作之姿寫實地畫出新教荷蘭生活百態的藝術天才。1890年,朗貝恩(JuliusLangbehn,1851-1907)以匿名作者身分出版了一本刻意廉價促銷的小書——《以林布蘭特為師:一位德國人所寫》6(RembrandtalsErzieher.VoneinemDeutschen)。由於這本書的定價只有兩馬克,短短一年內便發行了29版,在中產階級引起極大迴響。該書的熱銷情況連「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vonBismarck,1815-1898)都無7法漠視,因此接見了朗貝恩好幾回。在這本抨擊理性主義、物質主義、大眾文化的書裡,朗貝恩宣揚「個人主義」才是日耳曼國族精神真正的特質。而出身低地德意志地區(Niederdeutschland)的林布蘭特就是最能彰顯這種特質的德意志人。當時的德國人為了掙脫政治、宗教與科技工業在思想上所帶來的束縛,相當容易接受以藝術的創新來追求德意志精神文化復興的想法。就在這樣的國族意識熱潮裡,林布蘭特被高舉為文化精神更新的引領者。除此之外,1885年,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1844-1900)出版《查特拉圖如是說》(AlsosprachZarathustra),並提出有名的「超人」(Übermensch)哲學。配合「上帝之死」的思想,尼采所謂的「超人」代表一種揚棄形而上超自然庇佑的生存型態,徹底追求個我在現世的存在價值。然而,布氏對1890年代尼采「超人」哲學所引起的熱潮卻學院派崇尚的拉斐爾(Raphael)的藝術恰好相反,林布蘭特的繪畫並不奠基於歐洲古典傳統,而是具有前瞻性、現代性,而拉斐爾藝術則受傳統牽制太深。1852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豎立林布蘭特雕像,正式將林布蘭特標舉為荷蘭國族文化象徵。參見E.deJongh,“RealDutchArtandNot-So-Real-Dutch-Art:SomeNationalisticViewsofSeventeenth-CenturyNetherlandishPainting,”Simiolus20(1990-1991,Amsterdam),pp.197-206;JohannesStückelberger,RembrandtunddieModerne.DieDialogmitRembrandtinderdeutschenKunstum1900(München:WilhelmFinkVerlag,1996),pp.21-53.6JuliusLangbehn,RembrandtalsErzieher.VoneinemDeutschen(Leipzig:VerlagvonC.L.Hirschfeld,1890).7JohannesStückelberger,RembrandtunddieModerne,p.50.\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598持劃清界限的態度。1896年初,著名的教宗史學者LudwigvonPastor(1854-1928)認為布氏的學說遭到嚴重扭曲,被誤解為是啟發尼采「超9人」思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建議布氏考慮出面為自己辯白,以正視聽。在布氏寫給vonPastor的回信上,布氏明確表示,自己的史學研究與「超人」哲學毫不相干:此刻,尼采這個名字不僅本身具有魅力,它也成為媒體熱烈討論、詮釋的焦點——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此外,由於我的哲學天分不夠好,當尼采在巴塞爾(Basel)任教時,我能夠給他的欣賞並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樣。我們的交往並不頻繁,就是維持真摯而友善的對話。有關他提到「強勢作為之人」(Gewaltmenschen)這個概念,我從來沒有跟他就此交換過意見;也完全不知道,當我仍比較常見到他時,是否那時他就已經開始在深思這個概念?從他生病以後,我跟他碰面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就我個人而言,我本人從來就不欣賞歷史上的「強勢作為之人」以及法律無法加以管束的放縱之輩(Out-laws)。在我心目中,這些人比較像是「上帝之鞭」(FlagellaDei)。對這些人實際心理狀態之研究,我寧可留給別人來做,因為有些人會用令人瞠目結舌的方式大張旗鼓來從事。我個人則喜歡研究讓人感到幸福的人、專心從事創作的人、以及讓人感到生氣盎然的人。有關這個立場,我想,10我在其他地方也曾提過。8有關布氏與尼采的交往經過,參見LionelGossman,BaselintheAgeofBurckhardt.AStudyinUnseasonableIdeas(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0),pp.413-437.9LudwigFreiherrvonPastor,Tagebücher—Briefe—Erinnerungen,ed.WilhelmWühr(Heidelberg:F.H.KerleVerlag,1950),pp.289-290.10JacobBurckhardtBriefe,10vols.,withGesamtregister,ed.MaxBurckhardt(Basel/Stuttgart:SchwabeVerlag,1949-1986,以下簡稱Briefe),vol.X,Nr.1598(lettertoLudwigvonPastor,13January1896).\n160花亦芬雖然布氏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史學論述曾經對尼采哲學產生過影響;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布氏必須如此清楚表白自己思想的立場、甚至於是劃清界限的姿態,在在讓我們看到,他對時人的誤解確實感到憂心。正如LudwigvonPastor在1896年1月20日的日記上所言,大家「理所當然11地」認為,布氏也像尼采一樣,在鼓吹「強勢作為之人」的崇拜。從這些現象來看,便不難理解,何以晚年的布氏會認為有必要,對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所揭示的「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就他個人的立場,做出清楚明確的澄清。而從布氏一生的學術思考轉折來看,他所走過的這一段心路歷程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畢竟,布氏的憂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尼采的「超人」12哲學仍與布氏對文藝復興僭主的詮釋牽扯在一起。1941年,原任教於慕尼黑大學的歷史社會學家AlfredvonMartin(1882-1979)鑑於「超人」哲學在希特勒(AdolfHitler,1889-1945)時代引發許多人盲目的強者崇拜,特地書寫《尼采與布克哈特:兩個心靈世界的對話》(Nietzscheund13Burckhardt.ZweiGeistigeWeltenimDialog)一書,詳加區別二人學說與性格特質的差異。在此書中,AlfredvonMartin特別提到,布氏為人淡泊謹守,堅持道德基本原則;這與尼采一心追求「超越」的生命情懷有很大的不同。就晚年垂暮的布氏而言,如果「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在政治強權意識推波助瀾下,成為建構國族文化的要素,甚至在一般人對尼采「超11LudwigFreiherrvonPastor,Tagebücher—Briefe—Erinnerungen,pp.289-290.12例如EzzelinodaRomano(1194-1259),參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0-12。13AlfredvonMartin,NietzscheundBurckhardt.ZweiGeistigeWeltenimDialog(Basel:ErnstReinhardtVerlag,1stedition1941;3rdrevisededition1945).看到布氏的史論因為尼采哲學的影響越來越被誤解、甚至持續被濫用,AlfredvonMartin不顧納粹嚴格的思想檢查,於1941年出版《尼采與布克哈特:兩個心靈世界的對話》。在該書中,AlfredvonMartin不僅清楚區分布氏史學與尼采哲學的本質差異,為布氏史論做出許多澄清;他也將自己對納粹政權的許多批判寫在註釋的字裡行間,成為納粹統治時期德國知識分子堅持學術良心的典範之一。\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61人」哲學一知半解的認知裡,竟然成為誤導許多人無限制膨脹自我意識、國族意識的藉口,一個畢生關心這兩個特殊歷史現象在歐洲近現代文化發展的學者,還能繼續以「無善無惡」、「無巧不巧產生」這種不帶價值判斷的態度靜觀它們發展嗎?從布氏晚年必須面對的這些意料之外的困擾出發,本文想要深入探討的課題便是:布氏最後一本著作——《緬懷魯本斯》(ErinnerungenausRubens)——是否反映了他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考?如果是,那麼布氏想要藉由「緬懷」魯本斯哪些部分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些被特別提出來「緬懷」的部分,又與布氏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闡述有何異同?此外,值得進一步檢視的還有,如果說《緬懷魯本斯》本質上是一本布氏明確交代自己心靈價值取向的書,那麼在書寫上,它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有何不同?綜合目前對《緬懷魯本斯》出版經過的研究,可以簡短地說,布氏真正落筆寫作該書是在1896年——也就是他過世前一年。同一年,布氏寫了上述回給LudwigvonPastor的信,對尼采「超人」哲學在德國掀起旋風感到不以為然。根據《緬懷魯本斯》第一版出版者HansTrog之言,14這本書是在1896年夏天完成的。在布氏辭世(1897年8月8日)之前,他已將《緬懷魯本斯》的書稿與另外三篇討論義大利藝術史的論文〈收藏家〉(“DieSammler”)、〈祭壇畫〉(“DasAltarbild”)與〈畫作裡的肖15像〉(“DasPorträtinMalerei”)整理好,希望四篇論著合併出版成書。14EmilMaurer,JacobBurckhardtundRubens(Basel:VerlagBirkhäuser,1951;BaslerStudienzurKunstgeschichte,Bd.VII),pp.130-131;EdithStruchholzundMartinWarnke,“EditorischesNachwort”zuErinnerungenausRubens—JacobBurckhardtWerke.KritischeGesamtausgabe11(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6),pp.231-242,atpp.231-232.JacobBurckhardtWerke.KritischeGesamtausgabed為《評註版布克哈特全集》,以下簡稱JBW;ErinnerungenausRubens本文採用JBW之版本,以下簡稱JBW11(Erinnerungen)。15布氏於1893年(時年七十五歲)自巴塞爾大學退休。自是年4月起,他開始埋首寫作三篇討論義大利藝術史的論文:〈收藏家〉(1893年5月至9月)、〈祭壇畫〉(1893年11月至1894年3月)、〈畫作裡的肖像〉(1895年7月至12月)。《緬懷魯本斯》應是\n162花亦芬布氏原先的想法是,希望這本合集在他過世後由其外甥CarlLendorff負責出版。布氏在1896年9月13日所立的遺囑中,還特別撥出700瑞士16法朗要補助本書出版所需的1,500瑞士法朗費用。然而,到了1897年7月3日——也就是在布氏過世一個月前——他突然寫信給Lendorff,表示很擔心出版這本書仍會為他帶來太多虧損,因此希望取消出版計畫。布氏在這封生平所寫的最後數封信裡表示,他覺得可行的方案是,在他身後用他遺留下來的700瑞士法朗僅僅出版《緬懷魯本斯》這本小書就好,其他三篇論文就捐給公立圖書館,讓大家仍有機會可以閱讀參考。值得注意的是,布氏叮嚀Lendorff,出版《緬懷魯本斯》時,可以在書17名下方增列「布克哈特遺著」(AusdemNachlassvonJ.B.)這幾個字。很顯然,布氏在過世前一年,是用留給後世「遺贈」(Vermächtnis)的心情,而非寫作一般學術著作的態度來完成這本書。《緬懷魯本斯》不僅是布氏最後的遺著,也是布氏一生當中唯一針對特定藝術家所寫的專書。然而,這並不是一本一般學術意義下的藝術家傳記;或者更明確地說,這不是一本結合藝術家生平與作品(lifeand18work)的論著。布氏在本書一開頭簡短介紹魯本斯(PeterPaulRubens,1577-1640)的生平經歷、人格特質、創作時必須面對的各種外在環境條件後,便直接從構圖、空間表現、人體造型、與尼德蘭傳統藝術的關係、各種表現題材(聖經故事、聖徒畫像、古典神話故事、古羅馬歷史、寓意人物畫……)等不同面向,分門別類地闡述他個人心目中魯本斯藝術的重要成就。整體而言,布氏並沒有企圖將本書寫成一本集大成式的魯本斯藝術研究名著;相反地,如布氏藉由本書書名巧妙地告訴讀者,這在寫完這三篇論文後,才動筆寫的最後遺著。參見EdithStruchholzundMartinWarnke,“EditorischesNachwort”zuJBW11(Erinnerungen),p.232.16Staatsarchiv-Basel-Stadt,PA207,49.17BriefeX,Nr.1659.181875年布氏曾表示,想脫離大學課堂傳統的藝術史講授法,即跳脫以藝術家為主軸(Künstlergeschichte)所建構起來的藝術史講授法,改採風格與形式為主要詮釋脈絡。參見他於1875年4月20日寫給RobertGrüninger的信,收入BriefeVI,Nr.675,p.34.\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63本書的內容主要出自於他個人對魯本斯的一些緬懷(Erinnerungen)。回顧布氏一生的學術生涯,在藝術史方面,他最早出版的初試啼聲之作是1842年寫的尼德蘭藝術導覽《比利時各城所見的藝術收藏》(Die19KunstwerkederbelgischenStädte)。在本書中,布氏表示,受到十八、九世紀學院派崇尚拉斐爾(RaffaelloSanziodaUrbino,1483-1520)藝術的美感價值影響,魯本斯的畫作被批評為「表現手法不純粹」(unreine20Darstellungsweise)、「想像太粗野」(“gemeine”Phantasie)。布氏認為,21對魯本斯做出這樣的評價並不適切(unbilligbeurteilt)。到了生命盡頭,回過頭來要從一生廣泛涉獵的歐洲歷史文化裡,尋找一個可以藉以表露自己最後心志的對象,布氏還是一本初衷地選擇了魯本斯。但是,畢生不喜歡隨從主流的他,到了生命最後階段,仍很有意識地選擇與MaxRooses——當時歐洲最受矚目、強調透過整理編纂魯本斯史料以建立具22有科學根據的研究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保持距離。如同他當年寫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時,選擇走上一條與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的「歷史主義」大不相同的道路一樣。布氏之所以這19JacobBurckhardt,DieKunstwerkederbelgischenStädte(Düsseldorf:Buddeus,1842),inJacobBurckhardtGesamtausgabe,Bd.1(JacobBurckhardtFrüheSchriften),eds.HansTrog&EmilDürr(BerlinundLeipzig:DeutscheVerlags-Anstalt,1930),pp.113-198.20JacobBurckhardtGesamtausgabe,Bd.1(JacobBurckhardtFrüheSchriften),p.153.21JacobBurckhardtGesamtausgabe,Bd.1(JacobBurckhardtFrüheSchriften),p.153.221886-1892年間,在MaxRooses主持下,出版了《魯本斯作品全集》(L’ŒuvredePeterPaulRubens:Histoireetdescriptiondesestableauxetdessins,5vols.[Antwerp:J.Maes,1886-1892]);1887-1909年間,MaxRooses又與CharlesRuelens合編《魯本斯書信彙編》(CorrespondancedeRubensetdocumentsépistolairesconcernantsavieetsesœuvres,6vols.[Antwerp:VeuvedeBacker,1887-1909]),兩者都透過相當大型的史料編纂工作,強調進行具有科學根據的魯本斯研究。有關Rooses研究魯本斯的學術史意義,HansVlieghe曾表示:“Rooses’spositivistapproachwastypicalof19th-centuryresearchintotheartisticpastandwaslargely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sources;buthisstylisticjudgementwasnotfaultless,andhisviewsonchronologyandattributionaresometimesopentoquestion.”參見HansVlieghe,“Rubens,PeterPaul.”GroveArtOnline.OxfordArtOnline.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art/T074324(accessed13Jun.2010).\n164花亦芬麼做,除了對白紙黑字的史料文獻在理解藝術家的創作心靈上,是否具有比較好的證據優勢表示質疑;更重要的是,透過本書的書寫,他想要表達自己對魯本斯「特定」生命面向、創作面向的再思考;並藉此對自己整個學術生涯最關注的課題做出最後的闡明。二、「亂世」:布氏史論的基底布氏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除了探討一個歐洲文化盛世的多元風貌,同時也清楚指出,義大利文藝復興文化並非黃金時代的產物,而是在政治動盪黑暗、傳統價值崩解、社會民生極度不安的年代,因有知識分子與文化菁英對「文化主體性」的堅持,才有幸打造出來的文化高峰。究極而言,「亂世」是布氏起草刻劃文藝復興文化種種歷史圖像時,心裡構思的基本底圖。自此,不論是布氏面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或是他寫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後所開展出來的研究大方向,如何面對「亂世」裡的歷史問題,都是他中晚年從事學術工作時,始終縈繞於心的關懷。從上述的角度來看布氏遺著《緬懷魯本斯》,也可以說,布氏是藉由探討十七世紀上半葉享譽全歐的畫家魯本斯「個人」與政治、宗教、藝術之間的關係,「緬懷」他在創作上所走過的豐富歷程,來思考亂世裡文化開展的問題。布氏之所以會選擇魯本斯作為自己畢生著述裡唯一的「文化菁英個案研究」,這與魯本斯生逢「破壞宗教圖像風暴」23(Bildersturm;iconoclasm)的遺緒,中晚年又目睹「三十年戰爭」(ThirtyYears’War,1618-1648)帶來的重大災難密切相關。1566年8月,也就是在魯本斯出生前十一年,尼德蘭地區許多教堂與修道院的宗教圖像接23參見CarlosM.N.Eire,WarAgainsttheIdols.TheReformationofWorshipfromErasmustoCalv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花亦芬,〈宗教圖像爭議與路德教派文化政策——以紐倫堡接受宗教改革過程為中心的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70期(2009年5月,臺北),頁179-229。\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65連遭到激進宗教改革者的嚴重摧毀。當時西北歐宗教藝術重鎮安特衛普(Antwerp)更在1566年8月21日與22日兩天遭到空前浩劫,全城四十二座教堂絕大部分的宗教造像與精美禮拜器皿全被掃到大街上砸毀打爛。這股狂亂的風潮後來在西北歐各地到處延燒,史稱「破壞宗教圖像風暴」。而隨著歐洲基督教新舊各教派在政治上、經濟上或信仰文化上互相攻伐對抗(Confessionalization),歐洲不僅陷入空前分裂,更迫使不少人流亡異鄉。魯本斯的中晚年雖然正值創作高峰,但卻碰上「三十24年戰爭」,許多荼毒生靈的慘事以宗教為藉口,肆無忌憚地在各地發生。在這樣混亂、多災難的時代背景烘托下,「亂世」成為布氏書寫《緬懷魯本斯》隱伏在字裡行間的基調。從魯本斯早年的生平來看,他的父親約翰.魯本斯(JanRubens)因為接受新教信仰,在當時信奉天主教的安特衛普無法生存,所以帶著妻兒逃到德意志地區的科隆(Köln),擔任AnnaofSaxony(1544-1577)——荷蘭建國領導人威廉一世(WilliamIofOrange,1533-1584)第二任妻子——的秘書。魯本斯就在科隆附近的小城濟根(Siegen)出生。出生不久後,魯本斯全家搬回科隆,他的童年就在那裡度過。1589年,魯本斯的母親因為丈夫過世,決定帶孩子返回故鄉安特衛普定居,全家並改信天主教。綜觀魯本斯的童年,可以說,他自小就對信仰分歧所造成的流離不安,有相當切身的體認。1600年,魯本斯為了追求個人藝術生命精進,希望培養足以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文化對話的能力,所以前往義大利曼圖阿(Mantua)擔任宮廷畫家,自此展開八年的離鄉歲月。1608年,為了探視病危的母親,魯本斯兼程趕回安特衛普。雖然無法如願見到母親最後一面,但是安特衛普當時的氣氛,卻讓魯本斯決定落葉歸根,安居故鄉。促成魯本斯作出這個重大決定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安特衛普在哈布士堡尼德蘭攝政總督(GorvernorGeneraloftheHabsburgNetherlands)亞伯特大公爵(ArchdukeAlbertofAustria,1559-1621)及24RichardS.Dunn,TheAgeofReligiousWars,1559-1715,2ndedition(NewYorkandLondon:W.W.Norton&Company,1979),pp.82-92.\n166花亦芬夫人依撒貝拉(InfantaIsabellaClaraEugeneofSpain,1566-1633)主政25下,藝術文化發展前景可期;第二,1609年哈布士堡尼德蘭即將與想要脫離西班牙統治的荷蘭簽訂〈十二年停戰協定〉(“theTwelveYears’Truce”),尼德蘭南北政治、軍事的緊張衝突可望獲得紓解。1609年,亞伯特大公爵夫婦任命魯本斯為宮廷畫家,而且允許他不必常駐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可以在自己家鄉安特衛普定居。此外,魯本斯也可以隨自己心意接受布魯塞爾宮廷以外的委製訂單。亞伯特大公爵夫婦這種寬宏對待魯本斯的態度,不僅讓他擁有自由創作的空間,同時也讓安特衛普學習藝術的後進有了可以引導他們的良師。魯本斯返鄉時的安特衛普儘管面臨時代劇變,但大體上,居民仍依循傳統的軌跡繼續過往的生活步調。雖然經濟上大不如前,但是,受過良好人文薰陶的富裕市民階層,仍有心支持像魯本斯這樣優秀的藝術家在故鄉安居。有關安特衛普在宗教改革後遭遇到的困境,布氏在1845-1846年之交所寫的〈繪畫史講稿〉(“VorlesungenüberGeschichteder26Malerei”)——這也是他在取得博士學位(1843)後,對魯本斯藝術最早發表的見解——已經提到以下的觀察:自從1585年安特衛普被西班牙人征服後,局勢大為改變。想繼續保有新教信仰的人現在只能逃到尼德蘭北方省份,尤其是逃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主因是可以入海的雪爾德河(Schelde)河道已經被荷蘭人封鎖了。安特衛普原有居民十七萬人,到了1610年,只剩下八萬人。安特衛普籠罩在一片寂靜之中,修道院紛紛興建起來,但街道仍被荒草掩蓋。嚴格的天主教被引進這個城市;然而,安特衛普人對生活情趣的追求,喜歡聚會飲宴,熱衷節慶遊行,依25JBW11(Erinnerungen),p.15.26這一系列的〈繪畫史講稿〉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從君士坦丁大帝時代講到十七、八世紀的義大利繪畫(1844-1845年之交的冬季),第二部分從魯本斯與林布蘭特講到布氏當時的現代藝術(1845-1846年之交的冬季)。這一系列〈繪畫史講稿〉(“VorlesungenüberGeschichtederMalerei”)收錄於JBW18(NeuereKunstseit1550)(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6),pp.1-123.\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67然像在十五世紀杜勒(Dürer)的時代那樣。就在這種結合反宗教改革(Gegenreform)與粗獷市井生活的土壤上,產生了新的藝術。這個新的藝術浪潮之所以可以刺激大量藝術品產生,一方面是教堂與修道院對宗教藝術重新有許多需求;另一方面是因為過去有大筆資金被存積下來不敢花用。在安特衛普藝術開始展現新風貌之際,比利時布魯塞爾與漢特(Ghent)兩地也有一些地方小畫派隨之興起。——位居布魯塞爾宮廷的亞伯特大公爵(他仿效的楷模是岳父菲利普二世)與其夫人依撒貝拉(她父親的總管、著名的女獵人……等等),對藝術發展不太插手干涉。富商與企業組織(Corporationen)比統治君侯還要有影響力。主要的關鍵在於此時產生了偉大不朽的魯本斯。如果沒有他,比利時畫派可能還要長期陷在FransFloris(1517-1570)的折衷派困境27中,無法順利結合義大利與法蘭德斯藝術(Flemishart)。布氏對「反宗教改革」(德文:Gegenreformation;英文:Counter-Reformation)這個概念並不陌生,因為這正是他的老師蘭克在其享譽歐28洲的成名作《教宗史》一書刻意引介的專業史學概念。布氏對「反宗教29改革」與「巴洛可」(Baroque)藝術之間的關係也不陌生,在布氏所寫的《義大利藝術鑑賞導覽》(DerCicerone:EineAnleitungzumGenussderKunstwerkeItaliens,1855)討論十七世紀繪畫部分,他開宗明義就寫道:「反宗教改革帶起了當時教會藝術追求寬敞、富麗輝煌的巴洛可風格。在繪畫上,這樣的精神也反映在以激情、強烈的方式來表現宗教神聖的27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75.28LeopoldvonRanke,DierömischenPäpste,ihreKircheundihrStaatim16.und17.Jahrhundert,3Bde.(Berlin:Duncker&Humblot,1834-1836),Books5-7.29有關藝術史研究裡「巴洛可(Baroque)」概念的形成與開展,參見MartinWarnke,“DieEntstehungdesBarockbegriffsinderKunstgeschichte,”inEuropäischeBarock-Rezeption:VorträgeundReferategehalteninderHerzog-August-BibliothekWolfenbüttelvom22.-25.August1988(Wiesbaden:HarrassowitzVerlag,1991),pp.1207-1223.\n168花亦芬30人與物」。然而,在晚年所寫的《緬懷魯本斯》裡,布氏卻沒有將魯本斯置於「巴洛可」藝術的概念框架下,或是教會史裡的「反宗教改革」來討論。反之,他特意刻劃的歷史環境是一個人與人、國與國、以及不同基督信仰教派之間長時期互相鬥爭、掌權者只想鞏固自己利益的「亂世」。布氏有意跳脫當時學術界盛行的理論架構來詮釋魯本斯藝術,首先可從《緬懷魯本斯》不採用「巴洛可」這個風格概念來討論魯本斯作品清楚看出。雖然魯本斯的畫風充滿戲劇性的動感,但是布氏卻用「均衡對等」(Äquivalenz)這個看似在形容拉斐爾藝術風格的概念來說明魯本31斯繪畫真正的特質。布氏在此所談的「均衡對等」涵蓋了構圖與表現境界。他認為,魯本斯的繪畫表面上雖然動感張力十足,但是靜心細觀之後,卻會發現,他的作品真正獨到之處,是在整個畫面構成裡,隱藏在強烈動感下的平衡與寧靜。在布氏的詮釋裡,不論從構圖或意境來看,畫作能夠散發出這種氣質,是因為身處亂世的魯本斯自己擁有沉靜平和的心靈,並不會盲從「巴洛可」藝術一味想在畫面上製造騷動不安的時32代品味。在討論魯本斯與「反宗教改革」歷史文化的關係時,布氏的著眼點也不是放在當時一般人難以置喙的政教大框架上。相反地,布氏強調,在宗教走上尖銳對立、政治走上專制王權的幽暗時刻,安特衛普有幸擁有熱愛藝術文化的行政首長與受過良好人文薰陶的市民階層。因為他們的支持,魯本斯才能在亂世裡安心創作。而安特衛普也有幸擁有魯本斯。在布氏心目中,魯本斯獨特的藝術史意義,不在於他是一位精擅義大利藝術風格的尼德蘭巨匠,而在於他是一位即便面對大時代動亂,依然懂得堅持創作主體性的藝術家。30JacobBurckhardt,JBW3(DerCicerone.EineAnleitungzumGenussderKunstwerkeItaliens.Malerei)(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1),p.226.31EdithStruchholzandMartinWarnke,“EditorischesNachwort”zuJBW11(Erinnerungen),pp.236-237.32JBW11(Erinnerungen),pp.64-65,235-237.\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69由富商階層為社會主力的安特衛普,過去是「阿爾卑斯山以北真正33的藝術中心」,然而,受到荷蘭獨立戰爭(1568-1648)影響,經濟受創甚深。隨著荷蘭建國運動日益推進,自1580年代起,安特衛普在經濟上逐漸失去昔日風華。在宗教上,安特衛普雖然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在西北歐的重要據點;但是,比起西班牙雷厲風行的反宗教改革運動,亞伯特大公爵夫婦統治下的安特衛普氣氛寬和許多。布氏在《緬懷魯本斯》裡認為,相較於歐洲許多地方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激烈對立,安特衛普洋溢的安適氣氛,幾乎可以說,返鄉後的魯本斯真是有幸定居在一個西歐中立的小城(niedergelassenaneinerthatsächlichsovielalsneutralen34StättedesOccidentes)。在政治上,安特衛普不是統治宮廷所在。而亞伯特大公爵夫婦對於魯本斯的賞識與支持,更讓他在故鄉安特衛普能與當時歐洲的政教威權保持適當距離。這是布氏在《緬懷魯本斯》一書中,屢次重申的要點,例如:對魯本斯而言,很幸運地,在他生活周遭沒有威權。執政的最高首長——亞伯特大公爵夫婦——是信仰極為虔敬之人;而且安特衛普也非教廷所在地,甚至不曾是尼德蘭最有份量的神學家所居之處,35因為這種重要人物住在魯汶(Louvin)。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三十年戰爭時期也是歐洲專制王權(royalabsolutism)興起的時代。在法國路易十三(LouisXIII)時期掌政長達十八年(1624-1642)的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Richelieu,1585-1642)36治下的宮廷御用畫家,必須時時依照君王或宮廷喜好的品味來創作,以致於他們的畫風雖然反映了當時流行的藝術風格,作品卻缺乏真實動33FranzKugler,HandbuchderGeschichtederMalereiseitConstantindemGrossen.ZweiteAuflage,umgearbeitetundvermehrtvonJacobBurckhardt,2Bde.(Berlin:VerlagvonDunckerundHumblot,1847),vol.2,p.396.34JBW11(Erinnerungen),p.33.35JBW11(Erinnerungen),p.29.36JBW11(Erinnerungen),pp.21&27.\n170花亦芬37人的情感。在其他反宗教改革氣氛嚴明的地區,例如教廷與西班牙,當地畫家在創作時處處受到教義與教條箝制,藝術家並無法自由發揮自38己的才華。相較之下,魯本斯不擔任專制君主的御用畫家,也與政教威權保持適當距離,這就是在歐洲走向政治集權、宗教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時刻,魯本斯的藝術創作卻依然能夠獨樹一格,越晚年作品越精彩的主因。有關魯本斯的創作不受教會威權左右,布氏在書寫《緬懷魯本斯》之前,就已經對這個問題進行過不少思考。他曾以魯本斯繪製的兩幅《最後的審判》(《最後的審判〔大〕》TheBigLastJudgment,1617,圖一;《最後的審判〔小〕》TheSmallLastJudgment,c.1621/22,圖二),來與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Buonarroti,1475-1564)在梵諦岡西斯汀禮拜堂繪製的《最後的審判》壁畫(TheLastJudgment,1537-1541,圖三)39進行比較。布氏之所以特別將這三幅畫放在一起,是有深意的。1563年12月3日與4日,全特大公會議(CouncilofTrent)舉行了第二十五場(也是最後一場)議程。這個議程的主題是討論宗教改革者嚴重撻伐的一些議題——聖徒崇拜、聖徒遺物崇拜以及宗教圖像。在有關宗教圖像的問題上,會議的結論是將宗教圖像的監管權交給各地區主40教負責。也就是說,主教應注意,宗教圖像的創作應該莊重敬虔,不可造成觀者認知上的混淆,引發不敬或褻瀆的聯想。教堂裡如果要擺置任何宗教圖像,都必須經過主教同意。這場會議討論的結果之所以特別強調宗教圖像要莊重合矩度,其實與文藝復興藝術家有時會藉宗教藝術創作之名,事實上卻繪製令人想入非非的裸體人像有關。而在這方面,41最具爭議性的,就是米開朗基羅的《最後的審判》(圖三)。1564年,37JBW11(Erinnerungen),pp.70-71.38JBW11(Erinnerungen),p.36.39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p.406-409.40英譯參見RobertKleinandHenriZernereds,ItalianArt1500-1600.SourcesandDocument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6),pp.120-122.41參見AndréChastel,“DerSkandaldesJüngstenGerichts(1545),”inhisChronikder\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71GiuliodaFabriano已經著文〈繪畫創作之謬誤對話集〉(“DialogodegliErroride’Pittori”),公開討論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裡攙雜太多裸42體人像,有違道德觀瞻的問題。接下來一連串的批評聲浪更迫使教宗保祿四世(PaulIV,1476-1559)派人將這幅壁畫上的裸體人像都畫上衣服,遮蓋住讓衛道之士感到「妨礙風化」的部分。米氏《最後的審判》43所引發的爭議,以及反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上所受到的箝制,正是布氏用來突顯魯本斯宗教人物畫不以教會威權來自我設限的獨到之處。因為即便教會設下許多箝制,魯本斯卻仍努力在米開朗44基羅的基礎上,以人體的肢體語言作為表達豐富宗教意象的溝通媒介。而在另一方面,魯本斯又能以自己獨到的細膩情感與信仰認知,開創在本質上與米開朗基羅大不相同的精神格局。以魯本斯所繪《最後的審判〔大〕》(圖一)為例,布氏認為,魯本斯這幅畫是以上帝對凡人的慈愛為出發點,不像米開朗基羅的《最後的審判》(圖三)仍脫離不了威權審判的意味。《最後的審判〔大〕》是魯本斯在1617年為南德Neuburg聖母教堂主祭壇所作。當時這座教堂45才剛從新教教堂轉變成天主教禮拜堂,隸屬於耶穌會名下。布氏認為魯本斯這幅畫裡耶穌基督的表情與肢體動作比較戲劇化(theatralisch),但洋溢著基督賞賜豐盛恩典的氣息,如同耶穌在對世人宣告:「來吧!italienischenRenaissanceMalerei1280-1580(Würzburg:ArenaVerlag,1984),pp.188-288.42參見DavidFreedberg,“JohannesMolanusonprovocativePaintings.DeHistoriaSanctarumImaginumetPicturarum,BookII,Chapter42,”JournaloftheWarburgandCourtauldInstitutes34(1971,London),pp.229-245,herep.229.43參見BernadineAnn.Barnes,Michelangelo’sLastJudgment:TheRenaissanceRespons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44參見花亦芬,〈「殘軀」——藝術創作的源頭活水:TorsoBelvedere對米開朗基羅的啟發與影響〉,《人文學報》26期(2002年12月,桃園),頁143-211。45這座聖母教堂(Liebfrauenkirche)在1607年興建之初,原是新教的教堂。但是,1614年因當地統治者WolfgangWilhelm公爵改信天主教,所以將這座教堂改贈給耶穌會。參見KonradRenger&ClaudiaDenkeds.,FlämischeMalereidesBarockinderAltenPinakothek(MünchenundKöln:Pinakothek-Dumont,2002),p.322.\n172花亦芬你們這蒙賜福的」(“venitebenedicti”〈馬太福音〉25:34)。相較之下,布氏認為,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所刻劃的耶穌,比較像是高高在上的審判者,對不遵守上帝教誨的人要降下懲罰,一如福音書所言:「你46們這被詛咒的人,離開我」(“abitemaledicti”〈馬太福音〉25:1)。根據目前最新的研究,《最後的審判〔小〕》(圖二)應是魯本斯在1621至1622年之交,將一幅原本構思為《跌落地獄圖》(Höllensturz)的畫作在頂端另加上弧形畫板,然後在其上加畫耶穌基督、聖母馬利亞47與聖方濟等人,而成為我們目前所見的樣貌。這樣的看法與布氏當時的想法可以互相參證。布氏認為,這幅畫原先應是魯本斯出於純粹創作興趣所畫,可能是他從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被打入地獄的人物造型發想,希望另外創作一幅在藝術構成上可與之互別苗頭的新作,出發點單純是為了尋求藝術表現的創新。因此布氏認為,在作品實際的解讀上,《最後的審判〔小〕》其實與宗教儀式或教義闡發(ritual-sachlich)48無關。同樣的情況也可見於魯本斯為比利時各修會(如耶穌會、方濟會……等等)所繪製的宗教作品上。舉例而言,傳統的尼德蘭主祭壇畫都是以三折聯畫(triptych)的型態來製作。例如,魯本斯初返鄉時所畫的《舉起十字架》(TheRaisingoftheCross,1610-1611,圖四,現藏於安特衛普主教座堂)與《從十字架上卸下耶穌受難身軀》(TheDescentfromtheCross,1611-1614,圖五),就是在初返鄉階段刻意遵循尼德蘭祭壇畫傳統所繪製的作品。三折聯畫因為有較多描繪的空間,可以詳盡刻劃宗教故事內容,具有完整敘事的優點。然而,深受義大利藝術影響的魯本斯,卻更想探索視覺圖像本身具有的感發力。當魯本斯的創作生涯越趨穩健成熟,他便開始以個人藝術才性的追求來超越傳統尼德蘭宗46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406.47KonradRenger&ClaudiaDenkeds.,FlämischeMalereidesBarockinderAltenPinakothek,pp.324-327.48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p.406-407.\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73教藝術的限制。例如,1620年他為安特衛普方濟會所屬的Récollets教堂繪製的《十字架上的基督》(ChristontheCross;“Lecoupedelance”,圖4950六)便捨棄三折聯畫的形制,改採義大利祭壇畫獨鍾的單一畫幅。單一畫幅的敘事空間雖然沒有三折聯畫多,卻能將視覺觀視引到單一焦點上,創作者因此可以專注於表現畫幅上宗教人物的肢體語言與彼此之間的互動,追求創新的視覺效果,而不必花費太多心力去注意微小的敘事51細節。在布氏對魯本斯藝術的闡述裡,他藉由反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地區藝術家必須小心翼翼遵守的種種規範,來凸顯魯本斯藝術獨有的自由與自主。作為當時西北歐地區最孚國際聲望的藝術家,魯本斯不以教會「代言人」的身分來換取稱霸一時的尊榮,也不委身為特定修會闡釋教義以換取現世的利益。相反地,他的作品能真切地表現出許多前人或同儕畫家不曾表現過的信仰感知與宗教情感,因而贏得泛歐普遍的肯定與認同。布氏正是在這個層次上,論述魯本斯的宗教藝術何以能超越反宗教改革藝術的格局,成為傳世不朽的傑作。三、亂世裡個人才性的發揮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書裡,布氏一則正面肯定「個人主義」讓個人的才性得到解放,不受世俗規範與教會陳規限制的個人可以自在地探索世界,盡情發揮個人潛力;而藝術文化的發展也開始具有不斷推陳出新的動能:49JBW11(Erinnerungen),p.16.50AlexanderNagel,MichelangeloandtheReformofAr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p.113-140.51有關魯本斯回到安特衛普後,早期單幅式祭壇畫的創作,參見MartinWarnke,Rubens.LebenundWerk(Köln:DuMontLiteraturundKunstVerlag,2006),pp.47-48.\n174花亦芬十三世紀末起,義大利開始出現大批具有個人色彩的人物。過去對個人主義發展的箝制至此完全被打破,成千的人盡情開拓自家風52貌。而個人意識的覺醒,也讓文化的精神向度開始朝向縱深觀視的方向發展:我們不要只看「輝煌者羅倫佐.梅迪西」(Lorenzode’MediciilMagnifico)一生享有的好運、才華與性格,也應從個人主義者——如雅瑞歐斯特(LudovicoAriosto,1474-1533)——所寫的嘲諷文章來認識當時的人怎樣評斷自己。雅瑞歐斯特以極平和的語氣表達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與詩人的自豪,也以嘲諷的眼光剖析自己如53何耽溺於享受,他有最敏銳的嘲諷與最深摯的良善。在另一方面,布氏卻也不諱言,「個人主義」為歐洲近代文明製造出許多問題。布氏對「個人主義」的探討,認為其源頭來自於政治(國家)與宗教(教會)在深層結構上起了根本變化。當新時代的人無法再依循傳統的行為規範與心理認知來確保個我生存,大家就開始拋棄過去遵守的社會法則與道德倫理,各憑本能與需求來追求自我意志的滿足。在這樣的情況下,文藝復興時代的人開始揚棄中古社會文化視為最高價值的宗教聖潔,逐漸轉往「有意識地去道德化」(BewuβtseinderDemorali-54sation)這個方向發展。換句話說,對文藝復興時代的人而言,成為「聖徒」不再是生命理想追求的極致;成為大家看得見、自己也掌握得到的「歷史上的大人物」(diehistorischeGröβe),反而成為俗世價值奮力追求的目標。布氏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第六卷〈倫理道德與宗教〉中寫道:自從大家對上古文化愈益熟稔之後,歷史上偉人的生活風采成為大家遵循的新行為準則,這也取代了過去大家謹守的基督徒生活理52《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71。53《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77。54《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03-505。\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75想,去追求神所喜悅的聖潔。由於輕易地誤以為人生在世孰能無過,所以大過小犯沒什麼好放在心上的。反正歷史上重要的人物哪個不是引人爭議的行為一堆,但他們仍然成就了自己的英名。也許,這55樣的心態就在不知不覺中發芽茁壯。然而,在布氏眼中,這種只在乎滿足自己欲求、卻不管他人死活的「個人主義」,如果無法從其他方面加以節制,歐洲近現代文化的體質是難以免除「惡」的危害。儘管布氏希望以多元省察的立場來探討「個人主義」,但他仍忍不住寫下一段帶有清楚道德批判的話:當時義大利人性格的基本缺點看來也是使他們偉大的先決條件:也就是發展成熟的個人主義(derentwickelteIndividualismus)。這樣的個人主義首先肇始於內心抵制反抗君主專政、或非法取得政權的國家權威。〔……〕看到別人因自私自利而占盡便宜(beimAnblickdessiegreichenEgoismus),個人主義者也要挺身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就會鋌而走險用報復的手段與陰狠的暴力,來讓自己的內心取得平衡。〔……〕如果從廣義或狹義來看所謂的「自私自利」(Selbstsucht)是一切罪惡之源,那我們大概可以說,當時自我意識強烈的義大利人的確比56其他族群的人更接近惡(dasBöse)。很顯然,在探討「個人主義」的問題上,布氏既希望能夠維持多元省視的立場;但又憂心歐洲文明找不到其他出路,來矯正失去宗教形而上關懷的「個人主義」所帶來的斲傷。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第六卷〈倫理道德與宗教〉的序言可以看出,布氏的擔憂並非關在象牙塔裡的學者單純發出的思辯之言,而是根據他的史識,對未來文明發展不禁懷有的憂慮:一個看來病入膏肓的民族,也許可以很快重拾健康;同樣地,一個55《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04。56《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28。\n176花亦芬看來強健無比的民族,也許體內正潛伏著致命的病毒,時候一到,57馬上發病喪命。同時面對個人主義為歐洲文明帶來錯綜複雜的正、負面效應,筆者認為,布氏對如何解決「個人主義」帶來負面影響之思考,最好的理解切入點應是他對文藝復興「全才」的闡釋:自我期許促使一個人盡可能發展自己的人格特質,如果這能與自己天生多才多藝的優異稟賦以及深入涉獵當時所有文化素養的內涵相結合,便可以產生「全才型」的人物(der“allseitige”Mensch,l’uomo58universale)。「全才」對各種知識技能充滿自主學習的熱情,因此,不會讓自己變成59為人所役的御用文人或自以為是的匠師。布氏對於「全才」的詮釋其實充滿了他個人對教育與文化理想的投射,因此完全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來論述:十五世紀是全才型人物輩出的傑出世紀。所有傳記都會提到傳主能在閒暇時所從事的愛好上有超越業餘水準的傑出表現。佛羅倫斯的商人與政治家往往精通古希臘文與拉丁文,而且他們也會邀請最負盛名的人文學者來講解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與倫理學,自己的兒子也必須跟著一起聽。而他們的女兒也都接受極好的教養,在這個部分,可說是成功地開創了私人高等教育的先河。人文學者本身也被要求盡可能精通各領域。他們精通古典語文的情形並不像現代學者只把這些古老的語言當成藉以客觀研究古典文化的工具,而是能在60現實生活各層面靈活運用之。在布氏心目中,「全才」以其對萬事萬物的熱愛,跨越了知識分類的侷限以及技藝與才性的區別,成為重視人文素養的菁英共同追求的理想。57《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03。58《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77。59《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77-179。60《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78-179。\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77如果我們用LucaFarulli討論布氏與尼采在談論有關「跨界」61(Grenzüberschreitung)問題的差異來看,可以說,布氏所談論的「全才」是即便身處亂世,仍然在放眼可見的歐洲海岸線範圍內努力追求知識、創造深具人文價值文化的人。布氏的「全才」不像尼采所讚揚的哥倫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是在歐洲海岸線以外的浩瀚汪洋上,以天地為家,不顧一切地追求自我潛能的不斷超越。正因為布氏對「全才」的思考是放在人文價值觀的建立上,因此,他在乎的是:「個人」如何將「全才」的理想內化為優雅從容的心靈境界,既可以自然而然流露於言談舉止間,又能反映在自己內心對應周遭世界的進退出處上。在這方面,卡斯堤吉歐內(BaldassareCastiglione,1478-1529)所寫的名著《朝臣》(Ilcortegiano,1528)帶給布氏不少啟發:一如卡斯堤吉歐內所言,朝臣應接受良好的訓練,不只是為了在宮廷服務所需,更是出於朝臣自發的意願。朝臣其實是最理想的社交人才,是當時人文教養理念裡不可或缺的極致精粹。朝臣決定他所服侍朝廷的格調,而不是朝廷決定朝臣該作些什麼。一個對所有事情都深思熟慮的朝臣,說實在的,沒有那個朝廷配得上聘用他來服務,因為他具有的才幹與外在的形象其實與完美的君王無異;而他對各種事物(不論世俗或心靈層次)的應對進退,又顯得如此安詳、練達而自然,展現出相當獨立的自在。驅使朝臣追求完美的心靈力量,筆者雖然無由探知,但並非為了服侍君侯,而是為了追求個人62的完成。布氏心目中理想的朝臣,之所以能成為全才型「絕對的個人」(das63absoluteIndividuum),重點不在於他可以在執政者身邊成為分享權力61LucaFarulli,“NietzscheunddieRenaissance:DieReflexionüber»Grenze«und»Grenzüberschreitung«,”inAugustBucked.,RenaissanceundRenaissancismusvonJacobBurckhardtbisThomasMann(Tübingen:MaxNiemeyerVerlag,1990),pp.54-70,herepp.58-59.62《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458。63WolfgangHardtwig,“JacobBurckhardtundMaxWeber:ZurGeneseundPathologieder\n178花亦芬的人;而在於他有足夠的才華與識見,懂得明辨何時可以盡情展露才學,何時又該有所堅持、不隨波逐流。因為布氏認為,只有懂得堅持個人主體性、重視人文價值高過世俗利益的朝臣,才有可能成為推動社會文化朝向健康方向發展的良才:將有才識的平民延攬入宮廷到君王身邊服務,並非不可能。重點只在於,朝臣應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全才,只要大家想得到的才能,他們都該具備。如果他以恭謹不踰矩的法度面對所有事,那不是因為血緣關係所致,而是因為他謙和的個人主體性已臻完美之境,這是一種近現代社會認定的高貴。衡量這種社會主流價值認定的高貴,主要是看文化素養與富裕程度,也就是說,所謂富裕是將畢生心力奉獻於人文涵養(Bildung)上,而且為與文化相關的事物64慷慨大方地付出。從上述的討論來看《緬懷魯本斯》一書,就可以清楚看出,布氏為何會選擇魯本斯作為他最後遺著闡釋的對象。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裡,布氏為了打破個人主義者只知一味追求自我意志實現,最後卻往往落入爭逐計較的負面形象,所以特地選擇有深刻宗教修持的瓦雷瑞亞諾修士(FraUrbanoValeriano,1443-1524)作為該書稱許的學者65典範。然而,瓦雷瑞亞諾修士畢竟不是「朝臣」,與布氏想要強調既modernenWelt,”in:HansR.Guggisberged.,UmgangmitJacobBurckhardt.ZwölfStudien(Basel:SchwabeVerlag,1994),pp.159-190,atp.169.64《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436-437。65《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337-338:「到頭來,到底有哪一位學者是真正幸福快樂的?他們又是如何享有幸福快樂?是對上述這些苦難都視而不見、麻木無所感嗎?〔……〕孔塔理尼(GasparoContarini,1483-1542)說,他心中幸福學者的典範是貝魯諾籍(Belluno)的修士瓦雷瑞亞諾(FraUrbanoValeriano,1443-1524),他長年在威尼斯教授希臘文,也造訪過希臘與東方,到了晚年還喜歡到世界各國遊歷,從沒有騎乘過任何動物當交通工具,從不為自己私藏任何錢財,拒絕接受任何榮銜或高官厚祿。除了有一次從樓梯上摔下來以外,他真是一生無病無災,安享84歲高壽辭世。他的一生與其他人文學者相較,有何不同?人文學者擁有更多自由意志、更多個人主觀想法,好像隨時都想緊緊抓住到手的機會。反之,瓦雷瑞亞諾這位托缽修士從小就在修道院\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79能出世、又能入世的「全才」仍有一段距離。在《緬懷魯本斯》一書裡,布氏對魯本斯的描述,不論作為「朝臣」或「個人」,其實更貼近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對「全才」所揭櫫的理想。除了作為享譽歐洲的大畫家外,魯本斯與十六、七世紀絕大多數藝術家最不同的生命經驗在於,1623至1633年間,他曾多次擔任依撒貝66拉大公爵夫人的外交使節,致力於促進尼德蘭南北和平。在繁忙的繪畫工作之餘,耗費許多時間與心力涉足三十年戰爭時代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就客觀條件而言,是因為魯本斯受過良好的古典人文教育,深獲兩年前(1621)甫遭夫喪的依撒貝拉高度信賴與倚重;就魯本斯個人主觀因素而言,布氏認為,作為一位熱愛故鄉安特衛普的人,魯本斯步上國際外交舞台,的確是想為哈布士堡尼德蘭的和平盡一份心力。在這方面,他「大可在上帝與世人面前坦言,自己的目標的確就是如此」(sich67vorGottundderWeltbekennenkonnte)。長大,在飲食睡臥方面,從來不曾享受過想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所以一般人眼中的束縛,對他而言,根本算不上束縛。這種隨遇而安的性格讓他遭遇各種憂患都能保持怡然自得之心,而這樣的修養與風範也讓所有聽過他演講的人深受啟發與感動。」66對於魯本斯在這十年之間在歐洲各國的往返周旋,布氏在《緬懷魯本斯》一書裡沒有著墨太多。他只是概括性地提到:1627年,魯本斯以藝術之名為藉口,前往荷蘭;1628年夏天至1629年春天,他在馬德里(Madrid)停留了八個月;接著又去英國倫敦拜訪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I,1600-1649),直到1630年4月才返回安特衛普。1632-1633年,魯本斯進行他最後的外交活動。他先是與第三任荷蘭共和國世襲統領FrederickHenryofOrange(1584-1647)在荷蘭會面;接著又會晤了丹麥特使。但是,他越來越清楚,作為一位畫家,自己涉足哈布士堡外交事務如此之深,已經引起比利時政壇多人的不滿。隨著依撒貝拉大公爵夫人在1633年底過世,魯本斯也選擇結束十年的外交生涯。1626年,魯本斯的元配IsabellaBrant(1591-1626)過世;1630年底,他娶了小自己37歲的HelenaFourment(1614-1673)為妻。重新回到安特衛普過著單純藝術創作的生活,表示魯本斯不再希望藉由與歐洲統治權貴周旋,來達成自己對歐洲和平的理想;而是回到畫布面前,將安特衛普視為他向世界、向後代發聲的小宇宙。參見JBW11(Erinnerungen),pp.17-18.有關魯本斯外交生涯之研究,參見FionaDonovan,RubensandEngland(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4).67JBW11(Erinnerungen),p.17.\n180花亦芬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如果布氏將「全才」看成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文化所催生出來的新式菁英「類型」(Typus),我們應該要注意,布氏是從普遍有效的層次來解釋「全才」的特質,希望藉此與不世出的「天才」做出區隔。這個區分明顯見於,當布氏要舉例說明文藝復興的「全才」時,他是舉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人文學者兼建築師阿爾貝堤(LeonBattistaAlberti,1404-1472)為例,而非充滿天才神秘風采的藝術家達文68西(LeonardodaVinci,1452-1519)。十九世紀歐洲是一個熱烈討論「天69才」的時代,布氏為何不多花一些筆墨討論達文西、或與達文西相似的藝術「天才」?反而要將討論文藝復興菁英風采的論述重點擺在「全才」上?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裡,布氏並沒有說明原因,只是淡淡地寫道:「達文西的傲世奇才我們永遠只能在歷史的遙望裡略70窺一二。」然而,這並不表示布氏對十八世紀以降德意志知識圈大感興趣的「天才」議題沒有自己的看法。相反地,從這本書另外一段討論達文西的段落我們可以讀到,布氏對於「天才」不是只看到他們令人豔羨的不羈才情;從文化發展的角度,布氏也看到天才相當「個人主義」的性格特徵,是有其容易製造問題之處:達文西這位藝術大師為何一直選擇待在米蘭宮廷,除了說是他自己心甘情願外,真的很難理解。作為這個時代最多才多藝可以四處遊走的天才,達文西卻選擇長期待在米蘭,這只能說,在羅德維科.史佛薩身上達文西看到一種異於常人的特質,所以這位謎樣的藝術天才願意長期留在他身邊。日後,當達文西選擇為殘暴的凱撒.伯爾嘉(CesareBorgia)與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I)效勞時,也71有可能是被這些人與眾不同的情性所吸引。68《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79-181。69參見JochenSchmidt,DieGeschichtedesGenie-GedankensinderdeutschenLiteratur,PhilosophieundPolitik1750-1945,2vols.(Heidelberg:UniversitätsverlagWinterGmbH,2004).70《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181。71《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9-60。\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81在著述上,布氏對「天才」問題比較具體的闡述,必須等到他後來所寫的《歷史研究導論授課手稿》有關〈歷史上的大人物〉(“Die72historischeGröβe”)那一章。布氏在此談到那些不顧傳統倫理道德、以個人驚世駭俗魅力叱吒時代風雲的人物時,認為這些狂飆人物的生命是73介於「天才」與「瘋狂」之間。在他的觀察裡,十九世紀歐洲之所以熱衷討論這種一心只想追求自我意志滿足、卻無視於善惡後果的「天才」或「英雄」,有其時代環境因素:透過各種語言文字的交流、透過越來越頻繁的交通往來、透過歐洲人走向世界各地、透過我們對各種事物越來越深廣的研究探索,我們的文化在本質上越來越以具有高度全面接受性(Allempfänglichkeit)為標的。在追求普遍有效性的同時,我們也變得對特別與眾不同、74特別驚世駭俗的人有高度興趣。儘管是時代潮流所致,也儘管布氏個人也相當欣賞這些天才不羈的才情與非凡的創新,但他卻不認為這種「天才崇拜」或「英雄崇拜」可以為75歐洲文明帶來健康的發展。因為在布氏心目中,為了追求個人意志的徹底貫徹,太過英雄主義的人最後都避免不了要與罪惡(Verbrechen)76打交道。1877年11月6日,布氏以十九世紀廣受推崇的藝術天才——林布77蘭特——為題,作了一場演講。在這場演講裡,布氏一方面肯定林布蘭72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p.274-301.73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298.74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276.75LionelGossman,BaselintheAgeofBurckhardt,p.434.76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297.77JacobBurckhardt,“Rembrandt,”inJBW13(Vorträge1870-1892)(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3),pp.194-213.\n182花亦芬特對藝術的真誠,不論他個人生命起伏跌宕為何,始終努力創作;布氏也提到,林布蘭特的畫風與他個人的人格特質息息相關。但在另一方面,布氏也不諱言,天才性格強烈的人在文化發展上是會製造出一些問題的。布氏認為,在藝術文化創造上,這種個人性格極為鮮明的人,雖有他人難以企及的獨創性;但是如果整個國族文化的發展是以這種類型的78「個人」為楷模,難免會造成傳統中斷,為後世留下許多問題。以林布蘭特為例,布氏就指出,他的畫風雖然相當寫實,但與魯本斯相較,7980林布蘭特筆下的人物,「手」畫得不夠好,人物造型也不夠優美。此外,布氏認為,林布蘭特是一個完全活在自己世界裡的「個人」。反之,魯本斯在創作上、生活上、技藝傳承上,都能與周遭世界建立相當愉悅和諧的關係:〔魯本斯〕傳承了義大利最後一個風格健朗的畫派——威尼斯畫派。他也是有史以來最為強健不息、幸福快樂的人之一。在藝術創作上,他自在且均衡地通曉各種表現方式,因此不僅能夠快樂地開創屬於自己的畫派,成為培育出Jordaens與vanDyck等高徒的名81師;從比利時後世子子孫孫豐富的畫作裡,也可看出他的影響。78布氏也持同樣的觀點來評論米開朗基羅的創作,認為他掀起的巨大風潮,讓後輩藝術家陷入「難以抗拒」(Betörung)的困境,最後大家只能以米氏獨步全歐的巨碩人物畫風為依歸,無法再有其他選擇。參見WernerKaegi,JacobBurckhardt.EineBiographie,Bd.VI,2(Basel/Stuttgart:Schwabe&Co.Verlag,1977),pp.594-595.79有關「手」的描繪,布氏在《緬懷魯本斯》裡,花費許多筆墨讚揚魯本斯人物畫對手的刻劃極為細膩動人。參見JBW11(Erinnerungen),p.45.80類似的批評也出現在《義大利藝術鑑賞導覽》有關Donatello的論述裡。在此書中,布氏認為Donatello一心追求自然寫實的雕刻風格,「完全不受限制」,他不顧美感需求,一意求新、求寫實、求擬古的作法,「會對整個義大利的雕刻造成巨大、在某個層面上危險的影響」。參見JBW2(DerCicerone:EineAnleitungzumGenussderKunstwerkeItaliens.ArchitekturundSkulptur)(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1),pp.477&481.81JacobBurckhardt,“Rembrandt,”inJBW13(Vorträge1870-1892),p.195.\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83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布氏晚期的著述與其說是立場超然的學術研究,不如說是發自個人深刻史識的文化關懷。魯本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82下,逐漸成為布氏積極闡釋的對象。透過魯本斯這個「全才」典範的提出,布氏一則希望矯正大家對《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有關「個人主義」的誤解;一則也希望藉此平衡當時德意志社會文化對「天才」崇拜或「英雄」崇拜一面倒的熱衷。布氏除了1877年透過關於林布蘭特的演講,表達他對林布蘭特作為「天才」、以及魯本斯作為「全才」的看法外,他也曾在《歷史研究導論授課手稿》裡提到,「偉大的近代心靈」應該具有三項特質:第一,原創性(Originalität);第二,豐富多面性(Reichlichkeit)。布氏認為,「豐富多面性」的根源來自於「自身具有超人般的偉大稟賦(diegroβeübermenschlicheKraftansich),並且對於願意透過學習而獲得的進步,83有能力與興趣多方加以應用」。這個見解與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對「全才」特質的解釋十分相近。在藝術大師應具有的「豐富多面性」上,布氏認為拉斐爾創作各階段都符合這個標準;但魯本斯84更以此特質回應了家鄉同胞在文化發展上的期盼。第三,幸福。布氏提到,大家對歷史上的大人物是否享有比凡俗之輩更完滿的幸福,是相85當感興趣的,尤其是否是身心同感快樂的幸福。布氏對上述三個特質的重視讓我們看到,他並不是從「人是時代環境的產物」這樣的觀點來詮釋魯本斯與他所身處時代的關係;但也不是將人抽離出他的歷史時空背景,打造「英雄創造時代」的強者形象。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到《緬懷魯本斯》,「亂世」一直是布82LionelGossman,BaselintheAgeofBurckhardt,pp.390-391.83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281.84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281.85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281.\n184花亦芬氏歷史著述最為用心探討的課題。而對「文化創造」懷抱理想的菁英如何在亂世裡活出具有人文典範的生命格局,更是布氏史學思想的價值核心。從這個歷史關懷來看,布氏的「全才」是大大迥異於尼采哲學裡凌駕於時空環境之上的「超人」。根據上述的闡釋,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思考一個布氏史學的特殊論點:魯本斯雖然憑藉個人的藝術成就,可以跳脫傳統框架自由創作;然而,在反宗教改革的浪潮裡,安特衛普果真能如布氏所言,安靜作為「中立」的文化古城嗎?布氏在1845-1846年〈繪畫史講稿〉中,對反宗教86改革時期安特衛普(dasAntwerpderGegenreformation)的景況曾作過以下描述:因為西班牙在軍事上保全住比利時作為反宗教改革的勢力範圍,比利時因而創造出一種新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藝術。這種新藝術以相當輝煌的方式表現在教堂藝術的復興上,比德意志反宗教改革藝術87的成就還要燦爛。從上述的文字可以看出,布氏晚年在《緬懷魯本斯》所提到的「中立」,與其說是外緣的客觀歷史環境,不如說是公民自覺的心態。因為布氏筆下的安特衛普之所以成為「西歐中立的小城」,並非因為它在實際政治上、或宗教上是獨立自主的城市,也不是一般人民有能力決定自己是否想要這個外在的政教框架;而是公民階層願意積極創造並維護自己故鄉文化的決心。這種公民自覺的心態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說明:第一,經濟上有能力的市民與市民團體願意支持本地傑出的藝術家,發展具有家鄉特色的藝術,而不受限於政治與宗教主流權勢的操控。誠如布氏在《緬懷魯本斯》提到,回到家鄉定居後的魯本斯,有幸得到富商階層與企業組織的支持,使得他不必為了迎合「一時興起、為時不久的恩庇之情(Protectionsstim-mungendesAugenblickes)以及富豪私人的藝術品味(Privatschmackder86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75.87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75.\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8588Reichen)」來屈從謀生。在這方面,很顯然,布氏是依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的論點,認為充滿藝術人文氣息的創造性環境是培育優質文化不可或缺的土壤。在布氏心目中,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斯(Florence)之所以能成為人文學與藝術發展的源頭活水,市民階層(Bürgertum)的支持與投入是關鍵原因。因為市民階層能夠深刻體認到人文藝術自主發展的重要,因此社會可以產生穩固的文化創造主體意識。有了文化自主意識,統治君侯以及教會領導者才可能願意或多或少89放下自己的統御企圖,讓人文藝術擁有獨立發展的空間。從佛羅倫斯以迄安特衛普,布氏史學論述的重點其實一直環繞在建構「文化主體性」90這個問題上。第二,公民自覺的心態也表現在魯本斯願意與安特衛普的鄉親建立友善和諧的關係,幫助自己家鄉重執西北歐藝術之牛耳。布氏指出,魯本斯回鄉後最早創作出的大尺寸傑作,都與安特衛普當地的重要市民組織有關:第一幅是為St.Walburga教堂繪製的主祭壇畫《舉起十字架》(圖四)。幫忙決定將這幅祭壇畫交給魯本斯繪製的關鍵人物是CornelisvanderGeest(1555-1638),他在布商同業公會擁有重要影響力。第二幅是火繩槍民兵隊(Arquebusiers’Guild)為安特衛普主教座堂耳堂(transept)祭壇訂製的《從十字架上卸下耶穌受難身軀》(圖五);第三幅是為安特衛普市政府的商務大廳(Statenkamer)所畫的《三王朝聖圖》(TheAdorationoftheMagi,1609,圖七)。在當時,商務大廳即將作為1609年西班牙與荷蘭簽署〈十二年停戰協定〉的締約場所,安特衛普市政府委託剛返鄉的魯本斯繪製這幅畫,正是為了美化這個馬上要成91為眾所矚目的政治舞台。從上述三個例子可以看出,魯本斯相當願意與委製者以及委製團體建立良好的互信與互動,並不會以恃才傲物的88JBW11(Erinnerungen),p.15.89參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264-270。90參見花亦芬,〈寫給故鄉的書──《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緒論〉,收入《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68〕-〔77〕。91JBW11(Erinnerungen),p.15.\n186花亦芬「天才」之姿,讓委製單位感到棘手或為難。布氏心目中真正具有人文理想關懷的「個人」,是像魯本斯這樣與周遭世界擁有和諧、建設性關係的「全才」;而不是尼采式超越現實世界各種限制的「超人」。這樣的立論基本立場一如布氏在《緬懷魯本斯》書中,特別引用魯本斯在安特衛普自家宅邸中庭門檻上所銘刻的古羅馬92詩句:「寓於健康身體裡的健康心靈」(“menssanaincoporesano”)所揭示的觀點:值得讚許的,是能夠以健康的身心為後世留下健康文化遺產的「個人」;而非憤世嫉俗、只想在自己成就裡孤芳自賞的私我。1870年代,與布氏以及尼采同在瑞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ätBasel)任教的神學教授FranzOverbeck(1837-1905)便注意到,當布氏看到尼采越來越激烈表現出自己反基督信仰與知識文化的立場,他就開始與尼93采保持距離。Overbeck是尼采的好友,他認為這兩人主要的差異在於,布氏以出自內心深處對基督信仰核心價值的深刻虔敬,對基督教在外在世界被製造出來的種種現象,反而可以採取不帶偏見的寬和態度來面對;而尼采卻完全否定基督信仰的價值:92JBW11(Erinnerungen),p.21.93FranzOverbeck,WerkeundNachlass,Bd.4(KirchenlexiconTexte,--AusgewählteArtikelA-I.[Stuttgart:VerlagJ.B.Metzler,1995]),pp.118-120,297-298.1889年1月6日,布氏接到尼采從北義大利杜林(Turin,義大利文Torino)寄來的一封信——這也是目前《尼采書信全集》所收錄尼采寫的最後一封信(參見FriedrichNietzsche,SämtlicheBriefe,KritischeStudienausgabein8Bänden,hrg.vonGiorgioColliundMazzinoMontinari.[München: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2ndedition,2003],vol.8,pp.577-578),信中錯亂的文意讓布氏驚覺到,尼采的精神狀況十分令人憂心,因此連忙告知尼采的好友FranzOverbeck。Overbeck兼程趕至杜林,將尼采帶回瑞士就醫。自此,尼采不曾再從精神崩潰的黑暗中解脫出來。但是,尼采的妹妹ElisabethFörster-Nietzsche(1846-1935)卻從此時開始,強勢主導有關尼采檔案文獻資料的收集工作,希望讓德國的尼采崇拜繼續延燒下去。看到尼采哲學在這樣的狀況下繼續被吹捧,不只布氏,連FranzOverbeck也開始對所有與尼采相關的事保持謹慎小心的距離。1930年,當希特勒的國社黨與反猶主義興起,ElisabethFörster-Nietzsche成為熱烈支持希特勒的擁護者。1933年,透過ElisabethFörster-Nietzsche與納粹的良好關係,位於威瑪(Weimar)的尼采文獻館獲得官方正式的經費資助。\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87如果我們想到布克哈特他整個的童年教養與長大成人過程完全是在基督教環境裡完成,我們真的會對他能以如此自在不拘、沒有偏見的態度來面對基督教大大感到驚訝。在這方面,拿他與尼采作比較是特別有意思的。〔……〕尼采完全拒絕用這種泰然自若的態度來面對基督教,特別是,他越來越採取斷然拒絕透過歷史角度來討論基督教問題的立場,而用充滿敵意的方式片面解釋基督教,這是布94克哈特不會做的事。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布氏清楚看到,缺乏形而上宗教關懷與不懂得自我節制的近代心靈,在歐洲文明上所引發的災難,只能用「付出慘痛的代價」來形容。在歐洲近代史上,這樣的災難明顯表現於三十年戰爭期間,歐洲各地幾乎難以倖免於遭逢家破人亡、生靈塗炭的悲劇。面對十九世紀末歐洲軍國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張狂,布氏內心深切感受到的隱憂,也就可想而知。面對這樣的歷史情境,布氏除了在史學研究上表達他個人的見解外;如何從正面的角度樹立一個在亂世裡真切活過的文化典範、幸福典範,應該也是他認為值得透過文字著述來努力的方向。透過《緬懷魯本斯》這本遺著的寫作,更讓我們清楚看到,布氏並不希望《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以專制僭主為基底所刻劃出的「個人主義」原型(prototype),在尼采抽離了歷史時空背景的哲學思考裡,成為眾人所誤解的「超人」哲學可能的原始靈感來源。四、魯本斯畫作的「現世性」在布氏的歷史思維裡,「宗教」一直是他最深層底蘊的研究關懷。誠如他在1870年寫給好友FriedrichvonPreen的信上所言,「宗教」的95形而上追求是平衡人類權力慾與金錢慾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在《歷史94FranzOverbeck,WerkeundNachlass,Bd.4,p.119.951870年7月3日布氏寫給好友FriedrichvonPreen的信上說道:“Ichsage:Religion,dennohneeinüberweltlichesWollen,dasdenganzenMacht-undGeldtaumelaufwiegt,gehtes\n188花亦芬研究導論授課手稿》裡,布氏也寫道:「宗教是人類天性裡,對永恆以96及完全不會被摧毀的形而上需求之表達。」從布氏所寫的第一本文化史專書《君士坦丁大帝的時代》(DieZeitConstantinsdesGroβens,1853),探討歐洲文化如何從異教文明走向基督教化的過程,以迄他的經典之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反過來思索何以近代歐洲文明又想脫離基督信仰,轉向現世性與世俗化發展,這個連貫思考的脈絡讓我們在在看到,歐洲文化與「宗教」之間緊密的關連是理解布氏史學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裡,布氏對「現世性」問題的探討,主要可從兩方面來理解:(一)去基督教化後,近現代「現世」生活的景況;(二)去基督教化後,近現代人如何建構對「現世」的認知?如何追求「現世」的存在價值?整體而言,布氏並非完全持否定的態度來看歐洲文明走向「現世性」這個趨勢。對他來說,問題的關鍵在於,近現代歐洲人如何去開創具有存在意義的價值觀,並建立現世真正的幸福。針對上述第一點,布氏指出,中古歐洲的政教之爭讓教廷急於想將自己轉變為世俗化機制,以為上帝國的來臨可以藉由世俗版圖的擴張與影響力的建立來達成;因此反而將靈魂牧養工作視為次要。然而,當教會走向世俗化發展之際,其實也就是教會沉淪腐敗的開始。正是神職人員的腐化失德引發了後來僭主的為所欲為、以及知識分子的無德無行,一如布氏所言:當時教會的沉淪已到基督教史上教會蒙受最多批判的時刻了:教會以各種手段將暴力合理化、也將繼續維護他們絕對威權的學說講成絕對真理。為了維持他們不可侵犯的尊嚴,他們作盡各種傷風敗俗之事。而且為了合理化他們的處境,不惜對老百姓的心靈感受與良nicht.”見BriefeV,Nr.546,p.97.96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168.\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89知予以致命一擊;並迫使許多受過良好教育、但與教會劃清界線的97菁英最後只好選擇脫離基督信仰或因此絕望沮喪。在布氏的史學論述裡,歐洲近代文化朝向「現世性」方向發展並不意味著,人在放棄宗教信仰後,終於可以完全依循理性原則來創造更臻美善的社會文化。反之,近代歐洲人因為放棄了對上帝的信仰,不少人在面對現實世界的叢林法則時,只好不顧一切追逐獲得世俗權勢的倚靠,或98是轉而求助各種巫術,以讓自己的生存獲得外在力量的蔭庇。除此之外,當然也有人選擇在現世生活裡,沒有太高的道德標準,也沒有造福99人群的渴望,只想以隨波逐流的方式走完一生。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裡,布氏對近代歐洲文明趨向「現世性」問題的探討,主要的課題之一,正是在鉤沉近代歐洲人走向現世化的心理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必須面對的焦慮、恐懼,以及由此產生的後續文明發展問題。針對上述第二點,布氏也從另外一方面清楚表明,對「現世性」問題的探討,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心態:文藝復興與中古最明顯的差異——現世性(Weltlichkeit)——首先肇因於在自然科學與人類心靈世界的探討上,大量出現了新的觀視方式、思維方法以及探索的企圖心。〔……〕對具有近現代性格的人而言,不受任何阻擋去研究人與世間萬物,並將此視為畢生職志,這是崇高、不可放棄的使命。至於這些研究要花多長時間、會以什97《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30。98《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89-633。99參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631:「當教會的教誨變得愈來愈荒腔走板、而且專制獨裁時,宗教不可避免再度被轉化為個人主觀意識所能感受到的情狀,而且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對宗教的看法。這樣的現象也顯示出,歐洲人的精神活動並沒有枯竭衰萎。當然,上述的情況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呈現出來:阿爾卑斯山北方的密契主義(mystisch)者與苦修者很快為他們新的感知世界與思維方式建立了新的規範;但義大利人卻各走各的路,並讓成千上萬的人因為對宗教變得淡漠而迷失在人生險惡的波濤洶湧裡。」\n190花亦芬麼方式重新歸向上帝、以及這些研究與個人化的宗教信仰如何產生關連,都是無法以制式的規定來解決的。整體而言,中古時代不鼓勵透過經驗求得知識(Empirie),而自由研究的作法也已經讓教條100化的作風在上述重大問題的解決上無法再產生關鍵影響了。布氏很清楚,「現世性」既然已經成為歐洲近現代文化難以逆轉的重要質性,與其持保守、不願正視的態度,不如積極思考有建設性的對話應在甚麼層次上進行。在這方面,布氏在《緬懷魯本斯》一書裡的論述,充分展現他對這個問題後續的思考。換句話說,《緬懷魯本斯》對「現世性」問題的處理,不是將它繼續當成文藝復興以降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來看待;而是要進一步追問:「歐洲近現代人如何理解現世真實的意涵?現世真正的幸福如何創造?」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到《緬懷魯本斯》,我們可以看到,布氏不斷表達他對擺脫教會束縛的歐洲近現代文明實際生存狀況的深切關懷:歐洲近現代人從哪些層面認知、理解他們所處現世的「真實」?而透過這樣的認知方式與所得到的理解內涵,近現代人可以追求得到現世幸福嗎?如果不能,那麼,現世的幸福又該如何獲致?從上述的問題來看布氏在《緬懷魯本斯》裡對魯本斯的刻劃,我們就可以理解,何以布氏特別強調,魯本斯雖然身處亂世,卻依然將自己培養成創造力旺盛的藝術巨匠;而且因為時代的混亂不安,他反而更有意識地在作品裡表露出濃厚的現世人文關懷。布氏對這些面向的解釋,在在都讓讀者看到,晚年的他如何多方思考「個人」在「現世」生活裡如何創造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然而,在高度肯定魯本斯藝術之際,布氏卻也直率指出,十九世紀對如何透過視覺圖像來表達個人對現世存在經驗的感知,與魯本斯大為不同。他在《緬懷魯本斯》裡寫道:對於這位安特衛普藝術大師作為一位歷史畫家(Historienmaler),我們的時代一定會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標準來審視他的成就。首100《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73。\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91先,他會被要求將〔安特衛普在地理區域上所屬的〕布拉邦省(Brabant)以及其他尼德蘭地區過去所有的歷史以寫實的筆法來描繪,也就是畫中人物所穿的服飾應該還原歷史實況,而歷史戰役、人民反抗起事、示威遊行等等,也都應該依照真實的歷史情境來繪製。——諸凡此類檢視標準其實不是為了藝術創作本身值得往這些方向來追求,而是因為這樣是符合愛國情感,甚至於是進步的意識型態。這樣的檢視標準不是出於願意以同情的瞭解真正去感受,魯本斯所生存的那個世界是如何看待他們自己當下所處的環境;而是現代人認為當時人應該就是這樣感受。當然,這些崇尚寫實風格的人也會從他們正巧閱讀到的書籍或文獻裡找到史論的根據。他們會認為,魯本斯不應該在畫中表現他個人真摯熱切的情感,而應表現101別人的。在此,布氏指出,如果從十九世紀的藝術創作觀來看當代德意志文化對「歷史真實」的講究,「真實的歷史情境」其實是戴上「愛國情感」與「進步史觀」的眼鏡來認識的。換句話說,人們對於「現世」的理解,並非是去宗教化後,有能力以自由無拘的心靈重新認知現實界的真實,如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論及以全新的觀視重新認識世界102那般中立客觀;相反地,人們常常不自覺地淪為政治意識形態操弄下的應聲筒或犧牲品。101JBW11(Erinnerungen),pp.105-106.這一段論述可與《1550年以降的近代藝術》一段文意十分相近的論述相互參照:「從我們這個時代所在意的品味來看魯本斯,他會被要求應該如此這般來創作:首先,他應以寫實的手法畫出布拉邦省,或者更確切地說,比利時整個過去的歷史。過去的服裝、戰役以及人民的反抗行動、示威遊行都應包括在內。之所以會被要求這樣畫,不是為了對繪畫藝術而言,這是值得努力的;而是為了愛國主義以及時勢所趨。魯本斯會被要求,他應該作為自由主義的先驅。他不應該去表現自己以及具有良好素養的委製者內心真正感受到的熱情;而應該去表達並歌頌其他人偶然在剛出版的報章雜誌上所看到的一些意見。」參見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p.432-433.102《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573。\n192花亦芬布氏之所以會把他個人對十九世紀藝術的批判,透過表彰魯本斯藝術的成就來做對照組式的闡釋,是有原因的。這與十九世紀德意志繪畫在國族主義影響下,亟力追求「寫實主義」(realism)的風潮有關。「寫實主義」的興起基本上與十九世紀德意志市民階層希望脫離傳統封建貴族與教會權威對新興社會文化的箝制,以及新興的中產階級藝術市場希望擺脫傳統藝術講究的寓意象徵與文化符碼有關。對饒富資產的市民階層而言,他們想要擺脫過去宮廷、貴族、教會喜愛的藝術類型,轉而支持在公開藝術市場可以自由買賣的新藝術。不需要瞭解深厚傳統藝術語103言的「歷史寫實主義」(historicalrealism)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新的藝術風尚。因為這個新式藝術潮流希望透過寫實擬真的視覺圖像,將創作者與贊助者對當下歷史的認知、批判與所期待的時局走向,透過對過往歷史的詮釋表達出來。在這種強調寫實精神的創作思維主導下,不僅對所謂「真實」的掌握被高高舉起,畫作表現的內容大抵也與希望加速社會改革的「進步史觀」有關。然而,在布氏心目中,只根據一時一地的所見所聞,或將單方面「眼見為信」的資料視為確立「真實」的絕對證據,這種自信不免欠缺足夠的思慮。1871年——也就是德意志帝國建國那一年——7月2日布氏在寫給BernhardKugler的信上清楚明說,他們身處的時代表面上雖然進入媒體開放的時代,但有太多政治社會的對立,使得比較超然的公共意見論述無法成形;也有太多檯面下的利益交換,不是一時之間可以看得清楚:我首先要打從心底特別恭喜你推辭掉寫作《當代德國史》的邀約。跟其他事比起來,只知研究眼前所發生的當代歷史事件其實是最不103有關「歷史寫實主義」,參見PeterParet,ArtasHistory:EpisodesintheCultureandPoliticsofNineteenth-CenturyGerman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JohnR.Hinde,“JacobBurckhardtandNineteenth-CenturyRealistArt,”JournalofEuropeanStudies27(1997,London),pp.433-455;JohnHinde亦將上文的論述內容改寫,收入氏著,JacobBurckhardtandtheCrisisofModernity(Montreal&Kingston: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2000),Ch.8,“BurckhardtandContemporaryArt,”pp.232-269.\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93費真正腦力、但也最傷害一個人的學術生命。我們的時代與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c.460BCE-c.395BCE)不同,他可以完全無視於外在情勢與各種對立,而能深入到一切事件的核心。然而,今天的當代史講述者卻要承擔風險,等著稍過一陣子有些被揭露出來的大秘密把他所寫的書變成「不必再看了」。此外,他還得跟那些擅長臆造故事的人競爭,這些人以寫副刊小品文章的筆調所能吸引到104的群眾目光比他多一百倍。對布氏而言,對事物的表象作即時性的反應,不論文字或圖像,不僅尚未經過時間淘洗,而且本身也無法確實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有清楚的省視。布氏對時事評論式的報導與研究之所以如此排斥,應與他早年曾積105極參與過《藝術報》(Kunstblatt)的當代藝術論戰,以及在1844-1845年間擔任《巴塞爾日報》(BaslerZeitung)與《科隆日報》(Kölnische106Zeitung)的編輯與通訊撰稿人切身體認到的一些負面經驗有關。對於這種片段式、反射式、有時甚至不免趨炎附勢、譁眾取寵的「時事寫實」,布氏認為,這些文字表面上雖然貼近最即時的歷史現場,令人讀來有「時事見證」的快感;但是,實際上並不具備深刻的人文反思,更無法幫助104BriefeV,Nr.569,pp.131-132.1051842年底,布氏在其師FranzKugler鼓勵下,曾針對當年在柏林舉辦的當代藝術展寫過一篇長篇評論報導,該文自1843年初起在《藝術報》連載。不料因為布氏對德意志當代藝術的批評,觸及對德意志國族意識的批判,結果引發慕尼黑學者ErnstFörster對他發動幾近謾罵式的論戰。這個經驗對布氏學術生涯造成的影響,是研究布氏學術思想不可忽視的課題。筆者將另行撰文探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106WernerKaegi,JacobBurckhardt.EineBiographie.Bd.II,pp.401-458.Hardtwig提到,十九世紀重要的德意志史學家,從蘭克至TheodorMommsen與HeinrichvonTreitschke都曾或多或少擔任過報章媒體的固定撰稿人,其中只有蘭克與布克哈特與媒體的關係時間持續最短。無論如何,這個現象也反映出當時的歷史學者認為可以透過自己的專業研究所得,來影響當下政治社會的發展。參見WolfgangHardtwig,“Erinnerung,Wissenschaft,Mythos.NationaleGeschichtsbilderundpolitischeSymboleinderReichsgründungsäraundimKaiserreich,”inhisGeschichtskulturundWissenschaft(München: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0),pp.224-263,herep.233.\n194花亦芬讀者在此基礎上建立宏觀深刻的視野。此外,十九世紀歐洲常想要透過大眾媒體來促進社會「進步」;但卻忽略了所謂大眾媒體的背後,常有國家機器的介入與操控。在布氏心中,這種訴求普羅大眾認同的「進步」,到頭來,更難逃將整個社會心靈帶向「普遍平庸化」(eineallgemeine107Verflachung)的危機,讓一般人更容易受到掌權者的煽動利用。在另一方面,布氏也清楚表明,十九世紀藝術家必須面對新興的媒體力量,他們的創作也必須與公開展覽以及商業文化結合(這些都不是魯本斯必108須面對的創作環境)。而資本主義以大吃小的策略對歐洲藝壇生態帶來的巨大影響,在集中大量金錢資本的大城市威脅下,小畫廊、小城市109如果本身沒有足夠的競爭力,很難存活下來。說穿了,表面上訴求以崇尚「真實」、揭露「真實」為基調的十九世紀文明,實際上卻難逃國族意識、政治正確、進步史觀、以及資本主義所構築的「現世」之網。這樣的「現世」生存景況其實與布氏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所鉤沉那些失去基督信仰的近代義大利人如何轉而求助巫術,或索性過著趨炎附勢、隨波逐流的生活,其實並無二致。布氏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因為想要維持比較中立多元的論述觀視,所以對經歷了去基督教化的歐洲究竟該何去何從,並沒有110直接表明個人的立場,只在該書最末一段透過佛羅倫斯的新柏拉圖主義思想間接道出他個人的期盼:這個有形可見的世界是上帝用祂的愛創造出來的,是根據已預存於上帝那兒的理想形式所塑造出來的形象,而上帝也永遠會是這個世界的撼動者與使之繼續前進的推手。個體的靈魂可以先透過認識上帝而將祂安置於個人有限的軀體內;同時我們又會透過對上帝的107JacobBurckhard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NeuesSchema—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p.301.亦參見JBW13(Vorträge1870-1892),p.448.108JBW11(Erinnerungen),p.28.109JBW11(Erinnerungen),p.36.110花亦芬,〈寫給故鄉的書——《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緒論〉,頁〔90〕。\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95愛,把自己擴展到神的無盡境界裡。如此一來,上帝國的恩慈就會111降臨在塵世裡。布氏在上引《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的結語裡,仍以比較間接委婉的態度,用抽象的神學思想表達出,他對「個人」在近現代歐洲文明裡,如何透過個人化的信仰,重新追尋有上帝恩慈的「塵世」生活之理想。該書出版後,布氏在論述思考上卻也開始觀照到,如何透過良好的歷史教育與藝術史教育,就「現世」論「現世」,希望藉由培養學生從更有歷史省思、歷史識見的角度來建構自己對「現世」意義的認知,誠如1874年他在寫給尼采的信上所言:我教歷史從來不曾為了所謂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學術專業而教得慷慨激昂。基本上,我把歷史學看成入門學科:我應該幫助學生把歷史的基本架構建立起來,好讓他們以後無論繼續學什麼(只要不是漫無目的),這個架構仍然不可或缺。我盡力引導他們去掌握自己對過往歷史的看法與關係——不論是何種型態;至少不要讓他們對過去的歷史感到索然無味。我希望他們能憑自己的能力學習採摘求知的果實。我從來就不會狹隘地想,要培養學者和專業的學生;而是希望每個來聽我課的人都能有堅定的信念、也有這樣的心願: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地建構自己對過往歷史的看法,因為過去的歷史對每個人的意義不盡相同。在這方面,研究歷史是一件讓人幸112福的事。如同布氏不認為沒有經過深刻反思的現實表象可以作為認知現世真實的實際內涵,他也不認為,最容易被觀察到的政治權力更迭是認識人類歷史發展的主要架構。對他而言,學習與過往歷史對話是帶領人邁向幸福的一條途徑。而甚麼樣的人可以透過研讀歷史獲得幸福呢?依照布氏的看法,那就是願意透過不斷探問歷史、不斷用真實的生命感知與歷史對話,而可以在自己生命中逐漸培養出見識的人。在布氏對史學教育111《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頁636。112BriefeV,Nr.627,pp.222-223.\n196花亦芬的想法中,研讀歷史不是為了要影響別人、改變世界;而是要提升自己的見識、探尋自己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研讀歷史如果能使世界更趨美好、現世生活更趨幸福,不是因為這個世界被特定的史學理論、特定的歷史詮釋所改變;而是因為人透過良好的歷史教育、歷史省思,將自己培養成願意從事深刻人文思考的個人。這個「現世」如果能產生正向的改變,是源於許許多多的個人願意自主地進行自我改變,113並由此慢慢匯聚成一股推動社會往更文明方向發展的文化自省力量。對提升具有人文關懷的「現世」認知所做的努力,也表現在布氏對藝術史教育上。1877-1878年之交的冬季學期,布氏為「十七、八世紀的114藝術」(KunstdesXVII.undXVIII.Jahrhunderts)演講課撰寫的講稿,在往後近二十年的歲月裡,逐漸累積為他個人對近代藝術系列研究的手稿彙編。這些手稿被《評註版布克哈特全集》(JacobBurckhardtWerke.KritischeGesamtausgabe,簡稱JBW)編輯委員會整理為專書《1550年115以降的近代藝術》(NeuereKunstseit1550)。在這本書裡,布氏讚揚魯本斯是第一位完美結合義大利文藝復興與中古日耳曼藝術的人。針對這一點,布氏特別說明,魯本斯以「自然寫實風格」(Naturalismus)來描繪人體,並不是為寫實而寫實;而是透過對人體具體的描繪,傳達人在現世生活實際的存在經驗,希望藉此讓觀者產生感同身受的聯想:米開朗基羅刻劃的人體,其中任何一塊肌肉的表情,都必須能滿足其他各種情境的要求;魯本斯描繪的人體則不然。他所刻劃的人體與這個人體當下所處的時空環境完全不可切割。這正是魯本斯創作113WolfgangHardtwig,“WissenschaftalsMachtoderAskese:JacobBurckhardt,”inhisGeschichtskulturundWissenschaft,pp.161-188,atpp.170-174.114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p.1271-1275.115收入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p.125-876.透過這本書可以清楚看到,晚年的布氏在藝術史專業研究上,如何跳脫1840年代增修《繪畫史研究手冊》時,有形無形裡受到FranzKugler的影響,轉而建立具有個人觀察視野的研究方法,來判斷藝術品真偽、斷定其年代,並解讀其意涵。參見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p.1275-1276.\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97的追求所在。這個追求「正是」他藝術理想之所寄,也是他創作活116力的源頭。在《1550年以降的近代藝術》裡,布氏也舉魯本斯為安特衛普主教座堂所繪的《從十字架上卸下耶穌受難身軀》(圖五)為例說明。布氏指出,在這幅巨大尺寸的祭壇畫裡,每個人都以壯碩的形象出現:從右上方用自己的嘴使勁咬住裹著耶穌屍身那塊布的老人,到跪在耶穌腳下、幫忙攙扶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所有人都隸屬於這個特定的存在時刻,117而且全心投入耶穌被卸下十字架這個事件的過程裡。簡言之,人的存在意義是因為他們確確實實在塵世生命裡活出自己的價值,而這個價值也透過他們實際表現出來的行動為人所認知。布氏認為,魯本斯的畫作即便描繪了許多神話人物或寓意人物,他真正的創作思維卻是在探討「現世」生活的種種;而非跳過對現世的關懷,只在乎對「超自然」的想望。正是在這一點上,布氏區分了表面上看起來頗為類似的米開朗基羅與魯本斯藝術本質上的差異。早在1845-1846年之交的冬天,布氏在〈繪畫史講稿〉談到有關魯本斯的部分,就曾藉米開朗基羅與魯本斯所畫人物118的差別,來說明魯本斯創作的特色:米開朗基羅:不論在造型或構圖魯本斯:只以擬人化人物來表上,都將人體刻劃成較為超脫凡達塵世的各種力量,以及塵世俗、理想化的形象。利用壯碩的生活最極致、華美的輝煌。他人物造型,賦予畫中人物生氣與的刻劃更細膩入微,對各種事活力,藉此將畫中人物轉化為表物的描繪都賦予獨特的魅力。達特定意涵的符號(Symbole)。例如,上帝派遣的小精靈、先知。116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390.117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402.118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76.以下用左右兩欄分別列述米開朗基羅與魯本斯宗教人物畫的差異,是根據布氏在原文的作法。\n198花亦芬布氏在上引的比較裡指出,在創作思維上,雖然米開朗基羅與魯本斯都119喜歡以「人物畫」(figura)作為表現個人才情與思想最主要的繪畫類型,但是兩人畫作的精神意涵,在本質上是大不相同的:米開朗基羅喜歡用充滿理想化美感的人物來表現他對超凡脫俗的形而上世界之思考;而魯本斯卻喜歡採用尼德蘭藝術自然寫實的人物造型來表達對現世生活真切的感知。透過對比米開朗基羅與魯本斯人物畫的差異,布氏指出,魯本斯更有意識地表達他對現世的人文關懷。布氏這樣的看法一直延續到二十年後他在《1550年以降的近代藝術》所下的判斷:「魯本斯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第一位完全超越米開朗基羅以及羅馬畫派的人,此120外,他也推翻了他們的表現手法。」在《緬懷魯本斯》一書裡,布氏特別藉由《戰爭的後果》(TheConsequencesofWar,1637-1638,圖八)這幅寓意人物畫(德文:Allegorie;121英文:allegory),來闡釋魯本斯藝術如何從人文關懷的角度表現對「現世性」的思考。在高度肯定《戰爭的後果》之際,布氏其實深知,在十九世紀晚期的人眼中,這幅畫所採用的表達形式——「寓意人物畫」——已經是「完全過時」的創作形式(einejetztsovölligvergangene122《Mode》);然而,布氏不但肯定《戰爭的後果》是魯本斯「真正留119參見花亦芬,〈「殘軀」——藝術創作的源頭活水:TorsoBelvedere對米開朗基羅的啟發與影響〉,《人文學報》26期,頁143-211。120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391.121何謂「寓意人物畫」?布氏解釋,「寓意人物畫」是藉由擬人化人物的寓意象徵來表達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例如,各種力量、特質、動力、狀態、地方、人群。這些代表各種寓意象徵的擬人化人物,有些是藝術家自己創造出來的;有些則是從著名的古典神話援引出來。布氏強調,魯本斯喜愛採用擬人化人物來表達抽象概念或意涵深遠的思維,這與魯本斯對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的探索有關。也就是說,布氏認為,如果要理解魯本斯藝術,首先要能掌握魯本斯對希臘羅馬古典藝術以及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豐富思考。而魯本斯「寓意人物畫」正提供深富啟發性的切入點,讓後世可以透視這些錯綜多元的關係。參見JBW11(Erinnerungen),p.102.122JBW11(Erinnerungen),p.102.\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199123給後世的藝術遺贈」(eigentlicheKunstvermächtinisse)之一;他更讚揚這幅傑作是「刻劃三十年戰爭永垂不朽的代表性名畫,出於對時代最深刻的感受,獨力所完成的使命之作」(dasewigeundunvergeβlicheTitelbildzumdreiβigjährigenKriege,vonderHanddesalleinimhöchsten124SinnedazuBerufenen)。為何布氏要如此高度讚揚這一幅畫?布氏認為,如果想瞭解魯本斯如何看待他自己在三十年戰爭期間真正經歷過的「現世」,觀者就須細膩體會,魯本斯如何透過寓意人物來表達他對自己時代「真摯而深刻的想法與感受」(ernsteundtiefeWahrheitenund125Gefühle)。換言之,魯本斯不是從歷史表象來書寫他所生存的時代,而是從人文價值在那個時代如何被蹂躪踐踏的角度來探討那個混亂時代的病源。布氏指出,要瞭解《戰爭的後果》這幅畫原始的創作思維,最好的導讀是出自魯本斯本人之手。魯本斯於1638年3月12日將畫作完成後,要運給佛羅倫斯訂製者斐迪南.梅迪西大公(Ferdinandde’Medici,GrandDukeofTuscany)時,專程寫信給中間人——佛羅倫斯宮廷御用畫家JustusSustermans(1597-1681)。在這封信裡,魯本斯詳細解釋這幅政治寓意畫各種象徵意涵所代表的人文反思:主角人物是戰神馬爾斯(Mars),他剛從敞開的雅努斯(Janus)神廟出來(根據古羅馬的規矩,承平時期,雅努斯神廟是關閉的),手上拿著盾牌與沾滿血跡的劍繼續向前衝,威脅眾人要帶來巨大災難。他幾乎無視於身旁的情人維納斯(Venus)。在愛神(Amors)與丘比特(Cupids)陪伴下,維納斯極力想以輕柔的撫觸去擁抱馬爾斯;然而,他卻被手上拿著火炬的憤怒女神(theFuryAlekto)從另一邊123JBW11(Erinnerungen),p.20.124JBW11(Erinnerungen),p.105.在《1550年以降的近代藝術》上,布氏就盛讚《戰爭的後果》這幅畫是「高貴的魯本斯針對三十年戰爭刻意留下來的遺世之作」(EsistdesedelnRubensVermächtnisinSachendes30jährigenKriegs)。參見JBW18(NeuereKunstseit1550),p.429.125JBW11(Erinnerungen),p.104.\n200花亦芬拖走。在馬爾斯附近有代表瘟疫與飢荒的寓意象徵人物,他們是伴隨戰爭而來的必然產物。地面上,有一位手裡拿著一把破弦琴(lute)的婦女,她象徵「和諧」,但卻不見容於帶來種種不和諧的「戰爭」。還有一個媽媽手上抱著小孩,這也代表戰爭讓豐收、生產創造、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受到嚴重威脅,戰爭摧毀了一切。此外,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建築師正以仰躺的姿勢不支倒下,他手上還拿著畫建築設計圖的工具。在承平時代,建築原本是為建設城市實際所需及美化城市所用;但是,現在一切都被戰爭的暴力摧毀成斷垣殘壁。如果我記的沒錯,我相信,你可以在地上看到馬爾斯的腳下踩著一本書和一張畫紙,這是隱喻,戰爭將一切藝術與文化踐踏在腳下。地上還有一束鏢箭,原來綁住它們的束帶已經鬆脫了。這是隱喻,當束帶將鏢箭捆紮成束時,世上還有「和諧」(Concord)。在這些散落的鏢箭旁,還有醫神之杖(caduceus)和象徵和平的橄欖枝,這些也都被棄置一旁。穿著黑衣的婦女憂傷滿懷,她的面紗被扯下,身上穿戴的珠寶與其他首飾全被抓落,這位婦女象徵不幸的歐洲,長年以降一直慘遭劫掠、狂怒、戰火的侵擾,戰爭對每個人造成的殘害實在沒有必要在此盡數。歐洲的象徵物是那個小天使手上拿的圓球,圓球上立著一個十字126架,表示這是基督教的世界。布氏一再強調,魯本斯的寓意人物畫在歐洲藝術史上獨具意義之處在於,他筆下的寓意人物不是制式地表現抽象概念;而是有著活潑的肢體語言。藉由這些肢體語言,各個寓意人物不僅生動表達出與現世凡人一樣的情感與意念;他們彼此間的互動,也透露出微妙的心緒。例如,在《戰爭的後果》(圖八)這幅畫裡,愛神維納斯與戰神馬爾斯彼此之間126本信收入MaxRoosesandCharlesRuelenseds.,CorrespondancedeRubensetdocumentsépistolairesconcernantsavieetsesœuvres,6vols,vol.6(Antwerp:VeuvedeBacker,1887-1909),pp.207ff;英譯請見RuthSaundersMagurned.,TheLettersofPeterPaulRuben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5;repr.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1),pp.408-409.\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01的互動(圖九)就十分耐人尋味。在希臘羅馬神話裡,馬爾斯是最經常代表「戰爭」的標記,他通常是與女戰神米內娃(Minerva)一起搭配出現。然而,在《戰爭的後果》這幅有關戰爭的畫作裡,魯本斯卻選用手無寸鐵、對戰爭的強暴毫無招架之力的愛神維納斯來與馬爾斯配搭。在羅馬神話裡,馬爾斯與維納斯也是一對愛侶,當他們一起出現時,馬爾斯最常扮演的角色是維納斯的保護者。然而,在《戰爭的後果》這幅畫裡,馬爾斯卻成為一位強勢壓制者,面對赤身裸體、毫不設防的維納斯,他127毫不顧念過往柔情,任憑維納斯無助哀求,自己絲毫不心軟。除此之外,《戰爭的後果》這幅畫值得注意之處還有,有一對凡俗母子夾雜在神話人物之間。他們的身心飽受戰爭的摧殘,原本應在人間享受人倫親情,在戰爭無情的肆虐下,親子之樂卻活生生被驚恐與憂懼取而128代之。針對魯本斯畫作將寓意人物與現世生活的史實結合在一起這個部份,EmilMaurer曾指出,《緬懷魯本斯》並非一本著眼於「魯本斯與他129的時代」(RubensundseineZeit)的書,因為布氏想要刻劃的,是一位超越時代環境限制的普世型藝術大師。Maurer認為,布氏想強調魯本斯不僅在人格特質上不為外物所役;在繪畫語言上,他也透過寓意象徵130圖像的運用,突破地域限制,成為國際級藝術巨匠。然而,這種只一味強調「超越時空環境」的詮釋,其實忽略了布氏在《緬懷魯本斯》再三鋪陳「亂世」這種無以逃脫的「現世」,對魯本斯創作產生的深遠影響:「亂世」不僅促使晚年的魯本斯一再地以「戰爭」的恐怖與災禍為題材;「亂世」也曾讓魯本斯走上國際外交舞台,最後卻又選擇安靜回到畫布面前。對布氏而言,魯本斯之所以大量採用寓意人物來表達當時人對「現世」的感受,這與他思考如何從普遍有效的層次來書寫人在亂127JBW11(Erinnerungen),p.104.128JBW11(Erinnerungen),p.104.129EmilMaurer,JacobBurckhardtundRubens,p.237.130EmilMaurer,JacobBurckhardtundRubens,pp.237-238,242-243.\n202花亦芬世裡的切身感受有關。從史實來看,借用宗教之名所發動的三十年戰爭,實際上卻是許多強權與強人廝殺混戰的亂世。多少人剛開始舉著正義的旗幟,到頭來,究竟誰能以善告終?而長年混戰的結果,說穿了,就是蒼生飽受蹂躪。如果要從寫實主義的角度要求畫家具體畫出特定時空下的歷史場景,以為一時一地的「現世真實性」留下記錄,魯本斯反而要面對幾年後物換星移,原先大家所寄望的正義之師最後卻以不顧蒼生福祉的盜賊原形現身。我們應在這個層次上理解,何以魯本斯在《戰爭的後果》這幅畫裡,不願具體選擇某人某事或某場戰役作為特定描述的對象;也應在這個層次上理解,何以布氏如此欣賞魯本斯這樣的表現手法,並在《緬懷魯本斯》一書的末尾,盛讚魯本斯是歐洲文化史上真正可與荷馬(Homer)131相提並論的「敘事大師」(diebeidengrößtenErzähler)。對布氏而言,單純反映肉眼所見的現實世界表象,或被一時之間的愛國情緒、國族意識刺激,而留下來的「寫實」記錄,其實缺乏深度的人文觀視。藝術家對「現世」的揭露與詮釋,以及透過創作所欲喚起的「真實存在感受」,應該要從普世共通的人性面著手。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出於對「現世性」問題的反覆思考,布氏建立了一種不是將目光放在強權政治如何左右人類文明發展,而是深切關懷社會文化心靈健康的人文論述傳統。布氏以這樣的關懷來研究近現代歐洲文明的「現世性」問題,的確與當時史學專業化所要求的態度與認知大不相同。而在這樣的思維下,也就可以理解,何以布氏會認為,如果歐洲文明的發展勢必要走向以人在「現世」追求幸福為主要價值觀的道路,魯本斯會是值得仿效的典範。究極而言,布氏是想藉由身處亂世的魯本斯來說明,他儘管必須面對當時種種脫軌失序的現象,但仍堅守自己的創作主體性,並將自己發展成充滿創造力的人;而在現實生活上,魯本斯謹守公、私領域德行,並懂得充分享受人倫幸福。從布氏對這位「全人型個人」的闡131JBW11(Erinnerungen),p.143.這個讚許亦見於JBW13(Vorträge1870-1892),p.453.\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03釋,我們可以理解,何以布氏在《緬懷魯本斯》一書裡,對魯本斯在亂世裡仍能經營出幸福美滿「現世」生活的讚揚,完全不下於對他不朽的132藝術成就之肯定。五、結語雖然布氏早在1842年就表明,希望畢生能為社會大眾的歷史教育獻身,如他寫給好友GottfriedKinkel信上所言:我默默許下心願:此生將以清晰易讀的文筆來從事歷史著述,並且寧可為歷史感興趣的人來寫;而非寫一些枯燥、只求史實完備的著133作。在布氏漫長的大學教職生涯裡,他也一再強調,自己對歷史教育的認知,並非以培養專業研究者為目標;甚至於,他在臨終前一個月為遺著《緬懷魯本斯》所做的最後出版安排,也是將這本書視為一本為普羅大眾所寫的小書,如他叮嚀外甥CarlLendorff所言:「這本小冊子在巴塞爾大134概多多少少還可作為餽贈的禮物來銷售。」然而,布氏史學思想的複雜性,其實遠遠超過他素樸心願單純想做到的「歷史普及著作」或「歷史普及教育」。布氏史學著作內蘊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不僅可從西方史學界至今仍持續不斷探討、修正對布氏史學思想的理解看出;布氏在巴塞爾大學任教時的同事、同時也是尼采的好友FranzOverbeck也曾說過:如果有人只看到布氏的才情太過複雜,因此認定這是他的缺點,這樣的評價並不公允。因為在此同時我們也應該肯定,正因他的思想132JBW11(Erinnerungen),p.19.133BriefeI,Nr.59.(Berlin,21March,1842).134BriefeX,Nr.1659(3July,1897).\n204花亦芬135涵蓋高度複雜性,所以別具豐富內涵。面對十九世紀歐洲軍國主義與國族主義帶來的危機,布氏不像歷史主義支持者那樣,想藉由進步史觀來打造國族強權意識。相反地,在歷史研究裡,布氏開啟了歷史反省的研究向度,指出歐洲在近代文明「進步」的外觀下,體質並非完全健康。「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固然讓近現代歐洲文化走出一條新的路徑;然而,只有當歐洲人願意誠實面對它們一併衍生出來的問題,健康而文明的社會文化才是可以期盼的。這樣的歷史關懷,不是出於一位史家對自己時代單純的觀察,更是源於布氏親眼目睹了當時人受到「天才崇拜」、「英雄崇拜」、與「國族意識」的激情催化,對《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所闡釋的重要觀念產生了意料之外的誤解與錯誤推論。正因為布氏深刻意識到他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的詮釋如果被濫用所可能導致的危險,因此,如何解讀他刻意留給後世的「遺贈」——《緬懷魯本斯》,就不能只是從表面的文字敘述來理解。對布氏而言,透過最後一本著作的書寫,很顯然,他不僅想清楚表明自己真正的思想與立場;他也希望後世讀者能透過這本書,瞭解他內心真正的價值取向,從而澄清他的史學論點可能引發的誤解。從這個層次來閱讀《緬懷魯本斯》,便不難瞭解,為何這不會是一本單純的藝術史論著,卻像是一位關懷現世極深,以致於一生不斷地與當時學術主流思潮、社會政治主流思潮奮力對抗的史學家最後的心靈宣言。這個心靈宣言所表明的思想意向,不只如WilhelmWaetzoldt所言:「對布氏而言,魯本斯136具有的特質正代表布氏私密的自我期許」;更重要的還在於,藉由緬137懷魯本斯,布氏具體說出他個人對抗亂世、對抗時局無力感的方法,並135FranzOverbeck,WerkeundNachlass,Bd.4,p.120.136WilhelmWaetzoldt,DeutscheKunsthistoriker,2vols.,3rdedition(Berlin:Wissenschaft-sverlagVolkerSpiess,1986),vol.2,p.205:“RubenshatfürBurckhardtZügedesgeheimenWunschbildesseinerselbstgetragen.”137WolfgangHardtwig,“WissenschaftalsMachtoderAskese:JacobBurckhardt,”inhis\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05以此論述成果作為他留給後世的「遺贈」。誠如他寫給LudwigvonPastor那封著名的信上所言:「我個人則喜歡研究讓人感到幸福的人、專心從138事創作的人、以及讓人感到生氣盎然的人。」*本文的完成感謝97年度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計畫(NSC97-2628-H-010-002)研究補助的支持。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謹致誠摯謝忱。(責任編輯:雷晉豪校對:張佑如吳宛臻)GeschichtskulturundWissenschaft,pp.165-167.138BriefeX,Nr.1598,p.263(13January,1896).\n206花亦芬圖一PeterPaulRubens.《最後的審判[大]》(TheBigLastJudgment),1617.Oiloncanvas,606×460cm.AltePinakothek,München.引自:ChristopherWhite,PeterPaulRubens:LebenundKunst(Stuttgart&Zürich:BelserVerlag,1988),Fig.121.\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07圖二PeterPaulRubens.《最後的審判[小]》(TheSmallLastJudgment),c.1621/22.Oilonwood,184.4×120.4cm.AltePinakothek,München.引自:MartinWarnke,Rubens:LebenundWerk(Köln:DuMontLiteraturundKunstVerlag,2006),Abb.32\n208花亦芬圖三MichelangeloBuonarroti.《最後的審判》(TheLastJudgment),1537-1541.Fresco,1370×1220cm.CappellaSistina.Vatican.引自:AnthonyHugh,Michelangelo(London:PhaidonPress,1997),Fig.160.\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09圖四PeterPaulRubens.《舉起十字架》(TheRaisingoftheCrosswithsidepanelsTheVirginandSt.JohnwithWomenandChildrenandRomanSoldiers),1610-1611.Oilonpanel,centralpanel:462×300cm;sidewingseach:462×150cm.Cathedral,Antwerp.(©攝影:花亦芬)\n210花亦芬圖五PeterPaulRubens.《從十字架上卸下耶穌受難身軀》(TheDescentfromtheCross,withsidepanelsTheVisitationandPresentationintheTemple),1611-1614.Oilonpanel;centralpanel:4220×310cm;sidewingseach:420×150cm.Cathedral,Antwerp.(©攝影:花亦芬)\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11圖六PeterPaulRubens.《十字架上的基督》(ChristontheCross;“Lecoupdelance”),1620.Oilonpanel.427×312cm.KoninklijkMuseumvoorSchoneKunsten,Antwerp.引自:CharlesScribnerIII,Rubens(NewYork:HarryN.Abrams,Inc.,Publishers,1989),Fig.45.\n212花亦芬圖七PeterPaulRubens.《三王朝聖圖》(TheAdorationoftheMagi),1609.Oiloncanvas,346×488cm.MuseodelPrado,Madrid.引自:MartinWarnke,Rubens:LebenundWerk,FarbtafelXIV.\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13圖八PeterPaulRubens.《戰爭的後果》(TheConsequencesofWar),1637-1638.Oiloncanvas,206×342cm..GalleriaPitti,Florence.引自:ChristopherWhite,PeterPaulRubens:LebenundKunst,Fig.256.\n214花亦芬圖九PeterPaulRubens.《戰爭的後果》局部圖\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15引用書目一、文獻史料Burckhardt,Jacob.DieKulturderRenaissanceinItalien.EinVersuch.1stedition,1860;2ndedition,1869.中譯本:雅各.布克哈特著,花亦芬譯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第24冊。(本文簡稱《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Burckhardt,Jacob.JacobBurckhardtWerke.KritischeGesamtausgabein29Bände.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0-.本文簡稱JBW,引用冊次如下:JBW2(DerCicerone:EineAnleitungzumGenussderKunstwerkeItaliens.ArchitekturundSkulptur).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1.JBW3(DerCicerone.EineAnleitungzumGenussderKunstwerkeItaliens.Malerei).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1.JBW10(AesthetikderbildendenKunst.ÜberdasStudiumderGeschichte.MitdemText《WeltgeschichtlichenBetrachtungen》inderFassungvon1905).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0.JBW11(ErinnerungenausRubens).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6.JBW13(Vorträge1870-1892).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3.JBW18(NeuereKunstseit1550).Basel/München:SchwabeVerlag&VerlagC.H.Beck,2006.Burckhardt,Jacob.DieKunstwerkederbelgischenStädte.Düsseldorf:Buddeus,1842.InJacobBurckhardtGesamtausgabe,Bd.1(JacobBurckhardtFrüheSchriften),eds.HansTrog&EmilDürr.BerlinundLeipzig:DeutscheVerlags-Anstalt,1930.Burckhardt,Jacob.JacobBurckhardtBriefe,10vols.,withGesamtregister,editedbyMaxBurckhardt.Basel/Stuttgart:SchwabeVerlag,1949-1986.Kugler,Franz.HandbuchderGeschichtederMalereiseitConstantindemGrossen.ZweiteAuflage,umgearbeitetundvermehrtvonJacobBurckhardt,2Bde.Berlin:VerlagvonDunckerundHumblot,1847.Langbehn,Julius.RembrandtalsErzieher.VoneinemDeutschen.Leipzig:VerlagvonC.L.Hirschfeld,1890.Magurn,RuthSaunders,ed.TheLettersofPeterPaulRuben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5;repr.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1.\n216花亦芬Nietzsche,Friedrich.SämtlicheBriefe.KritischeStudienausgabein8Bänden,hrg.vonGiorgioColliundMazzinoMontinari.München: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2ndedition,2003.Overbeck,Franz.WerkeundNachlass,Bd.4.KirchenlexiconTexte,—AusgewählteArtikelA-I.Stuttgart:VerlagJ.B.Metzler,1995.Pastor,Ludwigvon.Tagebücher—Briefe—Erinnerungen,editedbyWilhelmWühr.Heidelberg:F.H.KerleVerlag,1950.Ranke,Leopoldvon.DierömischenPäpste,ihreKircheundihrStaatim16.und17.Jahrhundert.3Bde.Berlin:Duncker&Humblot,1834-1836.Rooses,Max,andCharlesRuelens,eds.CorrespondancedeRubensetdocumentsépistolairesconcernantsavieetsesœuvres,6vols.Antwerp:VeuvedeBacker,1887-1909.二、近人論著Barnes,BernadineAnn.Michelangelo’sLastJudgment:TheRenaissanceRespons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Chastel,André.“DerSkandaldesJüngstenGerichts(1545).”InhisChronikderitalienischenRenaissanceMalerei1280-1580.Würzburg:ArenaVerlag,1984.Donovan,Fiona.RubensandEngland.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4.Dunn,RichardS.TheAgeofReligiousWars,1559-1715,2ndedition.NewYorkandLondon:W.W.Norton&Company,1979.Eire,CarlosM.N.WarAgainsttheIdols.TheReformationofWorshipfromErasmustoCalv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Farulli,Luca.“NietzscheunddieRenaissance:DieReflexionüber»Grenze«und»Grenzüberschreitung«.”InRenaissanceundRenaissancismusvonJacobBurckhardtbisThomasMann,editedbyAugustBuck.Tübingen:MaxNiemeyerVerlag,1990,pp.54-70.Freedberg,David.“JohannesMolanusonprovocativePaintings.DeHistoriaSanctarumImaginumetPicturarum,BookII,Chapter42.”JournaloftheWarburgandCourtauldInstitutes34,1971,London,pp.229-245.Gossman,Lionel.BaselintheAgeofBurckhardt.AStudyinUnseasonableIdeas.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0.Hardtwig,Wolfgang.“Erinnerung,Wissenschaft,Mythos.NationaleGeschichtsbilderundpolitischeSymboleinderReichsgründungsäraundimKaiserreich.”InhisGeschichtskulturundWissenschaft.München: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0,pp.224-263.Hardtwig,Wolfgang.“WissenschaftalsMachtoderAskese:JacobBurckhardt.”InhisGeschichtskulturundWissenschaft.München: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0,pp.161-188.\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17Hardtwig,Wolfgang.“JacobBurckhardtundMaxWeber:ZurGeneseundPathologiedermodernenWelt.”InUmgangmitJacobBurckhardt.ZwölfStudien,editedbyHansR.Guggisberg.Basel:SchwabeVerlag,1994,pp.159-190.Hinde,JohnR.“JacobBurckhardtandNineteenth-CenturyRealistArt.”JournalofEuropeanStudies27,1997,London,pp.433-455.Hinde,JohnR.JacobBurckhardtandtheCrisisofModernity.Montreal&Kingston: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2000.Jongh,E.de.“RealDutchArtandNot-So-Real-Dutch-Art:SomeNationalisticViewsofSeventeenth-CenturyNetherlandishPainting.”Simiolus20,1990-1991,Amsterdam,pp.197-206.Kaegi,Werner.JacobBurckhardt.EineBiographie.Bd.II.Basel:BennoSchwabe&Co.Verlag,1950.Kaegi,Werner.JacobBurckhardt.EineBiographie,Bd.VI,2.Basel/Stuttgart:Schwabe&Co.Verlag,1977.Klein,Robert,andHenriZerner,eds.ItalianArt1500-1600.SourcesandDocument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6.Martin,Alfredvon.NietzscheundBurckhardt.ZweiGeistigeWeltenimDialog.Basel:ErnstReinhardtVerlag,1stedition1941;3rdrevisededition1945.Maurer,Emil.JacobBurckhardtundRubens.Basel:VerlagBirkhäuser,1951;BaslerStudienzurKunstgeschichte,Bd.VII.Nagel,Alexander.MichelangeloandtheReformofAr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aret,Peter.ArtasHistory:EpisodesintheCultureandPoliticsofNineteenth-CenturyGerman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Renger,Konrad,&ClaudiaDenk,eds.FlämischeMalereidesBarockinderAltenPinakothek.MünchenundKöln:Pinakothek-Dumont,2002.Schmidt,Jochen.DieGeschichtedesGenie-GedankensinderdeutschenLiteratur,PhilosophieundPolitik1750-1945,2vols.Heidelberg:UniversitätsverlagWinterGmbH,2004.Struchholz,Edith,undMartinWarnke.“EditorischesNachwort”zuJBW11,Erinnerungen,pp.231-242.Stückelberger,Johannes.RembrandtunddieModerne.DieDialogmitRembrandtinderdeutschenKunstum1900.München:WilhelmFinkVerlag,1996.Vlieghe,Hans.“Rubens,PeterPaul.”GroveArtOnline.OxfordArtOnline.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art/T074324(accessed13Jun.,2010).Waetzoldt,Wilhelm.DeutscheKunsthistoriker,2vols.,3rdedition.Berlin:WissenschaftsverlagVolkerSpiess,1986.\n218花亦芬Warnke,Martin.“DieEntstehungdesBarockbegriffsinderKunstgeschichte.”InEuropäischeBarock-Rezeption:VorträgeundReferategehalteninderHerzog-August-BibliothekWolfenbüttelvom22.-25.August1988.Wiesbaden:HarrassowitzVerlag,1991,pp.1207-1223.Warnke,Martin.Rubens.LebenundWerk.Köln:DuMontLiteraturundKunstVerlag,2006.花亦芬,〈「殘軀」——藝術創作的源頭活水:TorsoBelvedere對米開朗基羅的啟發與影響〉,《人文學報》26期,2002年12月,桃園,頁143-211。花亦芬,〈寫給故鄉的書——《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緒論〉,收入《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23〕-〔111〕。花亦芬,〈宗教圖像爭議與路德教派文化政策——以紐倫堡接受宗教改革過程為中心的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70期,2009年5月,臺北,頁179-229。\n布克哈特遺著《緬懷魯本斯》對「個人主義」與「現世性」問題的再思考219JacobBurckhardt’sReflectionsonIndividualismandSecularisminhisErinnerungenausRubens*Hua,Yih-fenAbstractInDieKulturderRenaissanceinItalienJacobBurckhardtcharacterizedearlymodernEuropeashavingtwomajorfeatures:theriseofindividualismandthetrendtowardsecularism.Lateinlife,Burckhardtwitnessedtherisingmisunder-standingofhisdiscussionsabouttheRenaissanceindividualismandsecularismintheshapingofGermannationalidentityandNietzsche’sphilosophyof“Übermensch.”Inordertoclarifyhisownhistoricalthinking,Burckhardtstrovetospecifyhispersonalvaluesinhislastbook,ErinnerungenausRubens.ThepresentstudyaimstoinvestigatehowBurckhardtfoundtheproperwaystomakehisthoughtsclearbyportrayingRubensasrolemodelinpresentinghimselfasahighlycreativeartistandahealthy-mindedindividualwholedahappyfamilylifeaswellasrenownedpubliclifeduringanagefullofpoliticalandreligiousconflicts.Thetwomainargumentsofthispaperareasfollows:(1)HowdidBurckhardtrebutthenotionofgeniusworshipinhistimewiththeidealofl’uomouniversale,towhichRubensservedasanappropriateembodiment?(2)HowdidBurckhardtelaborateonthemeaningfulperceptionof“reality”inthesecularworldbydistinguishingbetweenthepositivistnotionof“reality”inthenineteenth-centuryartandRubens’humanisticapproachtodepictingthe“reality”oftheThirtyYears’War?And,howdidheargueforthevalueofRubens’perceptionofthe“reality”inhistimewithregardtothepursuitoftruehappinessinthe“secularized”modernworld.Keywords:JacobBurckhardt;PeterPaulRubens;individualism;secularism;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AssociateProfessor,DepartmentofHistory,NationalTaiwanUniversity.No.1,Sec.4,RooseveltRoad,Taipei,10617Taiwan;E-mail:yfhua@ntu.edu.tw.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