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27 发布 |
- 37.5 KB |
- 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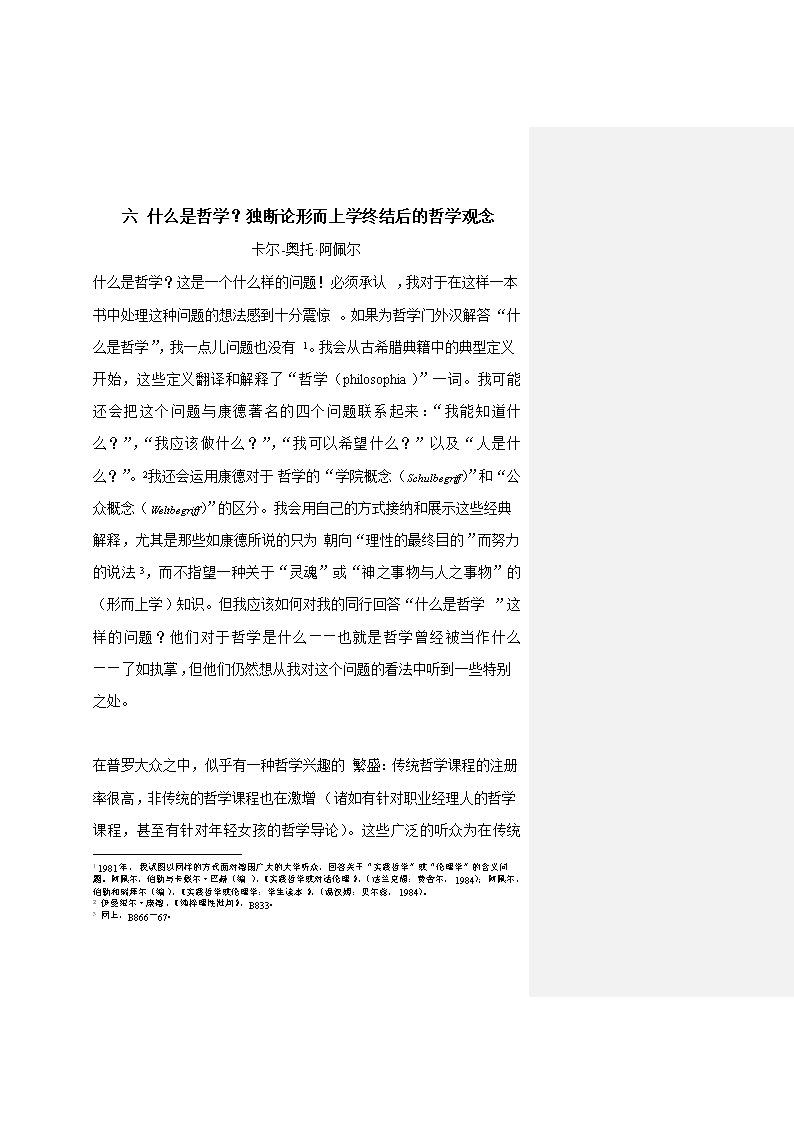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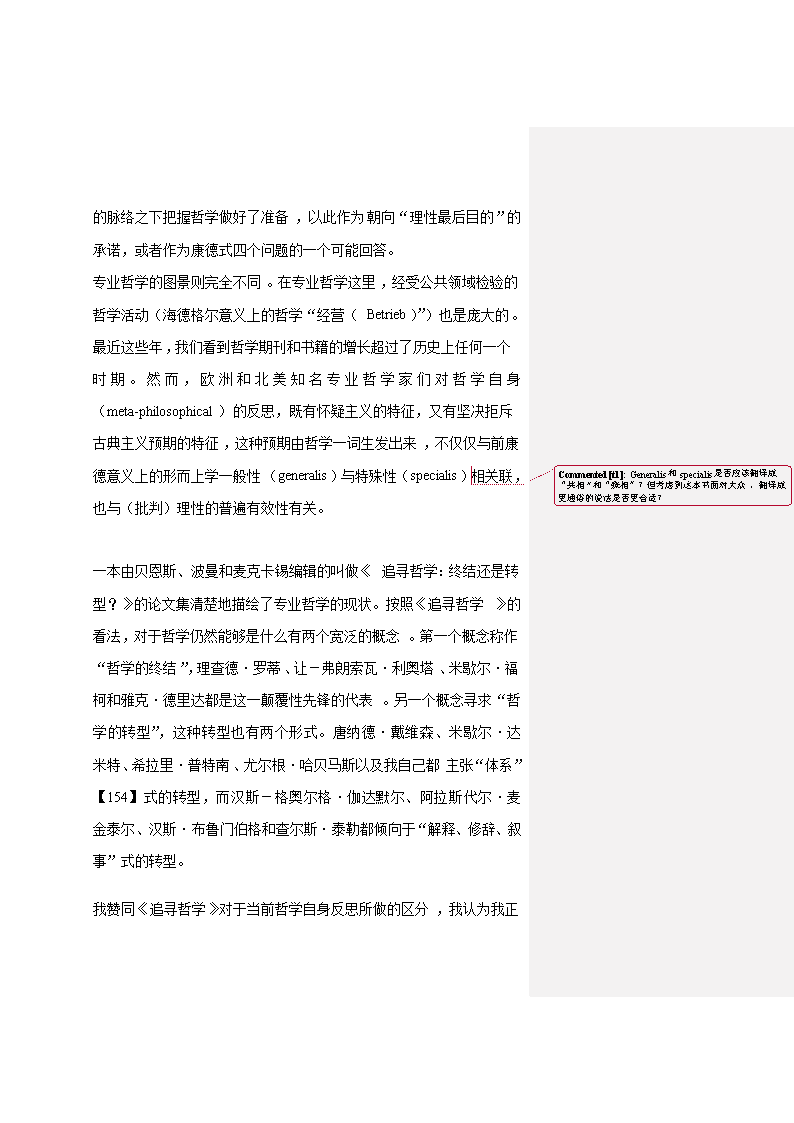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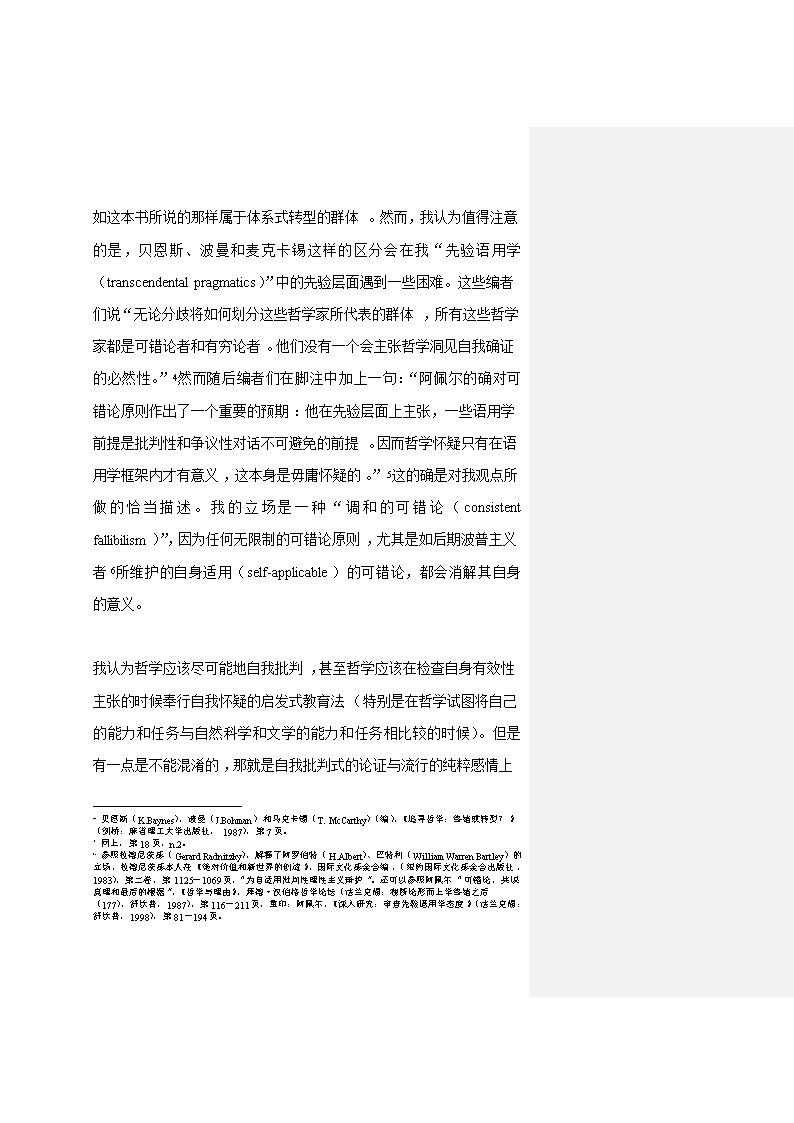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什么是哲学?独断论形而上学终结后的哲学观念
六什么是哲学?独断论形而上学终结后的哲学观念卡尔-奥托·阿佩尔什么是哲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必须承认,我对于在这样一本书中处理这种问题的想法感到十分震惊。如果为哲学门外汉解答“什么是哲学”,我一点儿问题也没有1981年,我试图以同样的方式面对德国广大的大学听众,回答关于“实践哲学”或“伦理学”的含义问题。阿佩尔,伯勒与卡戴尔·巴赫(编),《实践哲学或对话伦理》,(法兰克福:费舍尔,1984);阿佩尔,伯勒和瑞拜尔(编),《实践哲学或伦理学:学生读本》,(温汉姆:贝尔兹,1984)。。我会从古希腊典籍中的典型定义开始,这些定义翻译和解释了“哲学(philosophia)”一词。我可能还会把这个问题与康德著名的四个问题联系起来:“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以及“人是什么?”。伊曼纽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833。我还会运用康德对于哲学的“学院概念(Schulbegriff)”和“公众概念(Weltbegriff)”的区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接纳和展示这些经典解释,尤其是那些如康德所说的只为朝向“理性的最终目的”而努力的说法同上,B866-67。,而不指望一种关于“灵魂”或“神之事物与人之事物”的(形而上学)知识。但我应该如何对我的同行回答“什么是哲学”这样的问题?他们对于哲学是什么——也就是哲学曾经被当作什么——了如执掌,但他们仍然想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听到一些特别之处。在普罗大众之中,似乎有一种哲学兴趣的繁盛:传统哲学课程的注册率很高,非传统的哲学课程也在激增(诸如有针对职业经理人的哲学课程,甚至有针对年轻女孩的哲学导论)\n。这些广泛的听众为在传统的脉络之下把握哲学做好了准备,以此作为朝向“理性最后目的”的承诺,或者作为康德式四个问题的一个可能回答。专业哲学的图景则完全不同。在专业哲学这里,经受公共领域检验的哲学活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哲学“经营(Betrieb)”)也是庞大的。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哲学期刊和书籍的增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然而,欧洲和北美知名专业哲学家们对哲学自身(meta-philosophical)的反思,既有怀疑主义的特征,又有坚决拒斥古典主义预期的特征,这种预期由哲学一词生发出来,不仅仅与前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一般性(generalis)与特殊性(specialis)Generalis和specialis是否应该翻译成“共相”和“殊相”?但考虑到这本书面对大众,翻译成更通俗的说法是否更合适?相关联,也与(批判)理性的普遍有效性有关。一本由贝恩斯、波曼和麦克卡锡编辑的叫做《追寻哲学:终结还是转型?》的论文集清楚地描绘了专业哲学的现状。按照《追寻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仍然能够是什么有两个宽泛的概念。第一个概念称作“哲学的终结”,理查德·罗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都是这一颠覆性先锋的代表。另一个概念寻求“哲学的转型”,这种转型也有两个形式。唐纳德·戴维森、米歇尔·达米特、希拉里·普特南、尤尔根·哈贝马斯以及我自己都主张“体系”【154】式的转型,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汉斯·布鲁门伯格和查尔斯·泰勒都倾向于“解释、修辞、叙事”式的转型。\n我赞同《追寻哲学》对于当前哲学自身反思所做的区分,我认为我正如这本书所说的那样属于体系式转型的群体。然而,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贝恩斯、波曼和麦克卡锡这样的区分会在我“先验语用学(transcendentalpragmatics)”中的先验层面遇到一些困难。这些编者们说“无论分歧将如何划分这些哲学家所代表的群体,所有这些哲学家都是可错论者和有穷论者。他们没有一个会主张哲学洞见自我确证的必然性。”贝恩斯(K.Baynes),波曼(J.Bohman)和马克卡锡(T.McCarthy)(编),《追寻哲学:终结或转型?》(剑桥: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第7页。然而随后编者们在脚注中加上一句:“阿佩尔的确对可错论原则作出了一个重要的预期:他在先验层面上主张,一些语用学前提是批判性和争议性对话不可避免的前提。因而哲学怀疑只有在语用学框架内才有意义,这本身是毋庸怀疑的。”同上,第18页,n.2。这的确是对我观点所做的恰当描述。我的立场是一种“调和的可错论(consistentfallibilism)”,因为任何无限制的可错论原则,尤其是如后期波普主义者参照拉德尼茨基(GerardRadnitzky),解释了阿罗伯特(H.Albert)、巴特利(WilliamWarrenBartley)的立场,拉德尼茨基本人在《绝对价值和新世界的创造》,国际文化基金会编,(纽约国际文化基金会出版社,1983),第二卷,第1125-1069页,“为自适用批判性理性主义辩护”。还可以参照阿佩尔“可错论,共识:真理和最后的根据”,《哲学与理由》,拜德·汉伯格哲学论坛(法兰克福:独断论形而上学终结之后(177),舒坎普,1987),第116-211页,重印:阿佩尔,《深入研究:审查先验语用学态度》(法兰克福:舒坎普,1998),第81-194页。所维护的自身适用(self-applicable)的可错论,都会消解其自身的意义。我认为哲学应该尽可能地自我批判,甚至哲学应该在检查自身有效性主张的时候奉行自我怀疑的启发式教育法(特别是在哲学试图将自己的能力和任务与自然科学和文学的能力和任务相比较的时候)。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混淆的,那就是自我批判式的论证与\n流行的纯粹感情上顺服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s);这种感情往往都是迸发自与我们理性话语能力的有穷性和完全可错性有关的准形而上学话语,通过诉诸我们据称可以仅仅从历史经验的证据中得来的东西,理性话语似乎可以逃脱所有批判性质询而获得它自身的有效性状态。【155】我认为,针对这种混淆的最好解毒剂就是将其哲学前提,包括那些不可知论的前提,与通过言语行为所显示的暗含其中的有效主张,进行持续地反思性比较。如果我们的哲学前提与出于语用所预设的有效主张不相符,我们就会使自己陷入践言性自相矛盾之中——后语言学转向相当于康德所谓的对“理性一致性(SelbsteinstimmigkeitderVernunft)”的违反。在我们的时代,这里所建议的严格的先验反思是哲学中运用先验论证的最极端方式。在库尔曼(W.Kuhlmann)《反思最后的根据,对先验语用学的研究》(法兰克福:舒坎普,1991)这种反思不再受到“范畴图型”或此类东西(正如彼得·斯特劳森及其后继者曾改造过的)先验还原的束缚。参照尼奎特(M.Niquet),《先验论证:康德,斯特劳森和去先验的困境》(法兰克福:舒坎普,1991)因此,这种反思也不会遭受罗蒂从戴维森质疑“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所得出的“去先验化(detranscendentalization)”的裁决,“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就在于假设在认知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离。参照罗蒂,“适度迷失的世界”,《哲学杂志》第69期,第19页;“先验论证,自指涉和实用主义”,《先验论证和科学》,比艾瑞等编(多德雷赫特:瑞戴尔,1979),第77-103页。还可以参照尼奎特《先验论证》,530E。\n由于我们能够也应该检验所有类型的哲学论证,即使是那些整体论(holism)或不可知论(skepticism)的论证,以此确信我们能够避免践言性自我冲突从而超越他们。事实是论证都会预设有效性主张,这是哲学非闭合的,因而也是非常先验的先决条件。难道在我们的时代,即使是这个先决条件也要质疑?带着这个问题,以及前面的一些评论,我已经在以下的论述中搭建了尝试的舞台,去解释我所认为的当今哲学应该是什么。“哲学终结”的立场回到《追寻哲学》这本书,我想那些代表着“哲学终结”观点的人或多或少会很明确地反驳我的论题,即论证预设某种有效【156】主张是哲学的非闭合先决条件。但由于这些反驳者通过论证进行反驳,他们本身仍然按照我的先验语用学的最小条件进行哲学思考,而他们各种各样相关的反驳只是犯践言性自我冲突的诸多形态而已。这一点需要连同其后果进行更详尽的分析。对论证所具有的先验功能进行反驳,内在地与另一个反驳相关联,即对在哲学、修辞和诗歌的语言游戏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这一观点进行反驳。为了避免误解,让我解释一下。我不否认,伟大的诗歌可能具有哲学意义,甚至其哲学意义还会大于那些平庸的学院派哲学。我也不反对在哲学论证的过程中使用诸如暗喻这样修辞的和诗歌的手段。但在我看来,这种语言游戏或种类的合法性融和有一个限度;\n文学的或修辞的目标不能淡化或否认哲学论证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性主张,尤其在这种论证将会面对可能的批判之时。举个例子,我们考虑一下这种臭名昭著的模糊性:说服(persuade)、说服力(persuasion)和说服性(persuasive),正如同从拉丁语演化而来罗曼语系,这种英语中的模糊性代表了一种修辞传统。如今,言语行为理论使我们能够在通过论证使人信服(德语:überzeugen)与狭隘的修辞意义上的“说服力”(德语:überreden)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前者的成事效果(perlocutionaryeffect叙事行为(Locutionary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act),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依赖于听话者的自主判断,后者则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达到“成事效果”,即使卑鄙地抑制或消除听话者的自主判断也在所不惜。比Überzeugen与überreden之间的混淆更糟糕的是混淆两种具有不同公开策略的语言使用【157】:有策略地使用论证,为弥补和批判有效性主张服务,与之相对的是,有策略地使用语言,为自身的利益(interest)服务——即通过显示给价(offers)和(或)要价(threats)获益(例如交易中那样)。通过先验语用学反思,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种语言游戏中证实论证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而第二种语言游戏则因为需要达到关于有效性主张的某种共识这样的哲学兴趣(philosophicalinterest)而排斥先天性。在《追寻哲学》一书中,代表“哲学终结”一派的罗蒂、利奥塔、福柯和德里达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或反对论证的先验功能。他们跨越\n具有自身一致性哲学的界线,不仅运用文学类的元素实践和增殖(propagating)一种无害的哲学盛宴,还会实践和增殖我上面提到的关于语言使用的基本原理的混淆。举个例子,罗蒂就建议让哲学退到“教化式的对话”中。这样做,他就会努力避免所有与论证的普遍性有效主张相关联的复杂哲学问题。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拥护罗蒂解决先验哲学问题方案的党徒,在听完我关于对话理性的报告之后,对我说:“你本不需要有效性主张,你只要有说服力就行了。”这种说法与罗蒂独特的关于真理的共识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理论是实用性的,对于某个主张的某个听众,其实际的说服成功有着自己标准化的测量手段。通过把目标定位于具体的社会性协定,罗蒂试图将我们的“客观性”目标替换为“一致性”目标,(其后的威廉·詹姆斯)把“真理”理解成对于那些实际上可以达成协议的人“利于相信”的东西,例如,“自由主义者,那些西方社会受过教育的人”实际上参与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构成。参照罗蒂,“真理是追问的目标吗?戴维森是对的。”,《哲学季刊》第45期(180),第281-300页。罗蒂还说:“我们希望向尽可能多和广泛的听众证明我们的信念。”(第298页)。但他怎么证明他的这一希望或假定?根据罗蒂关于说服的语用学理论,其假定的意义仅仅在于欲求提高说服的社会成功率,否则,他就必须向普遍有效性寻求援助,这实际上会解释和证明通过论证达到共识的无限制尝试需要试验信念的力量。参照哈贝马斯,“罗蒂的实用主义本质”,《德国哲学杂志》44(5),第715-742页。罗蒂的观点看起来就像一个通过修辞性论证将真理与有用性等同起来的文化中心主义;这种观点【158】削弱或消解了真理主张(truth-claim)的观点,因为这种主张的有效说服力独立于情境,具有普遍有效性。实际上,罗蒂明白地否认überreden与Überzeugen之间的区分与“\n情境依赖”和(真理主张的)“普遍性”之间的区分有任何关系。对罗蒂来说,“在语言使用的策略性和非策略性之间的区分正如同以下两种情形的区分: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说服别人;我们希望能学到什么(learnsomething)。”对罗蒂来说,这两种情形是“光谱的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上,我们极尽所能用一切肮脏的诡计(欺骗,隐瞒事实(omissioveri),虚假暗示(suggestiofalsi)等)去使人信服。[我本来打算在这里用说服一词,因为(按照苏格拉底)我会把通过论证使人信服的所有尝试都与希望学到什么相关联。]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像和自己说话一样轻松、深思熟虑和充满好奇……‘对真理的纯粹追寻’即是在这一极端下发生的谈话所具有的传统名称。但我看不到这种谈话与普遍性或无条件性有什么关系。”理查德·罗蒂,“普遍性与真理”(未出版手稿,1993年6月14日)。然而,在严肃的哲学讨论中,这样一种“实用的”立场使得讨论不可能被反对者批判,因为这种讨论并不会展现一个有效性主张,事先就区别于依赖情景的成功说服。消除了批判的可能性,罗蒂的对话式实用主义实际上就标志着哲学的终结。卡尔·波普尔是对的,他认为免疫抵消批判,同样,没有独立于情境的有效性主张也无异于此,都是哲学的致命错误。但是,因为在可提供的“外部实在论”参照希拉里·普特南,《带人类面孔的实在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n的意义上没有真理的标准,也就是在对话可能的成功之前不可能辨别出真理的标准,那么罗蒂的立场就是唯一的出路了吗?罗蒂对出路的选择与其说代表着所有外部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不如说只是代表着查尔斯·皮尔斯“实用主义”特别参看皮尔斯“什么是实用主义”,论文集,第五卷,§§4”-437;cf.5-438n\5-453”“,5-458,5.460^5-497ff,5-nff。还可以参看阿佩尔《从实用主义到实用主义》(阿木赫斯特:麻省大学出版社,1981),第二部分。的实用主义学说,在我看来,这种选择是一种论辩性对话的标准化程序主义,一种不是依赖于修辞性说服,而是依赖于论辩的调整性观念(regulativeidea):在论辩性对话的理想(认知性的和交流性的)状态中,达到最终的共识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真理是我们在原则上可以诉求的,那么这种共识就是我们经由这种真理所必需明了的东西。参照阿佩尔,“可错论,共识:真理与最后根据”。我在这里不能适当地讨论最近那些反对调整性观念有意义使用的讨论,这些调整性观念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概念,而这些反对意见特别是来自威尔默(A.Wellmer)在《对话及伦理》中提到的反驳,(法兰克福:阿佩尔【178】,舒坎普,1986),第91页;另外在《决赛》(法兰克福:舒坎普,1993)中“真理,偶成性,现代性”,第162页。我在这里只能说,如果我们从调整性观念中得出寻求一种超出所有可能交流状态的义务,那么我们就是误解了最终共识的调整性观念。只有在我们试图去想象在历史条件下达到最终共识会是怎样的情况,或者去想象人类历史终结之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种调整性观念的构想才能浮现出来。但我认为这无异于将某个调整性观念实体化,而这一调整性观念已被试图将这类“观念”去柏拉图化的康德所禁止。即便是如此,没有哪个群体可以实际上达到那种可以把握关于真实的整个真理的共识。任何严肃的论证必然把这种共识认作是一种调整性观念。换句话说,我们要对这一调整性观念的前提进行驳斥,就必然暗含践言性自身冲突(performativeself-contradictio)。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倡者简-弗朗索瓦·利奥塔,他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驳斥调整性观念如何导致践言性自身冲突。追随一种尼采主义或维特根斯坦式的无政府主义,利奥塔用一种后对话式的哲学公开地攻击对话“合法性”的需要或可能性。\n但他没有对其自身的后对话式哲学(及其普遍有效主张)的必然性进行反思。取而代之的是,他主张,现代科学的后对话哲学就如同思辨性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后叙事,这种思辨性历史哲学始于18世纪,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努力下登峰造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做出了一个普遍有效性的整全性主张,只是以一种进步的现代观念中某个特殊概念的面目进行的。由于反对这些观点,利奥塔将知识的后经验主义哲学与幻想破灭的当下经验二者的缺点都暴露无遗。因为利奥塔否认存在理性的先验批判,他就会这样来说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想的那样,合法性是通过【160】讨论在共识中获得的吗?这种共识其实是在对异质性语言游戏施行暴力。而创造总是来自意见纷争。后现代主义知识不再仅仅是权威的某个工具,它完善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性,加强我们容忍不可比性的能力。后现代主义的原则不是专家共同体,而是发明者的家族相似(paralogy旁系同源,意译为家族相似)。”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第75页。《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这一典型段落提出了以下的问题。恰恰是这样一个反对寻求共识的论证本身难道不暗含一种对共识的诉求吗?至少,只要它是一个论证,只要它是通过它的普遍有效性主张展现它后对话式哲学的特征。更进一步的,“异质性的语言游戏”本来就会使抱有达成共识的希望不复可能,这种不可能性又如何能够被一个“以讨论达成的共识”打破?我们能够也必须通过讨论以下事实达成一个共识:“异质性语言游戏”\n必然抑制我们达成共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仅仅要为“家族相似”喝彩。相反,我们要尽量克服语言游戏的异质性,至少在科学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求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范式”或“整全性原则”(如在尼尔斯·波尔那里)。在最低限度上,我们需要努力在这个持续的异质性语言游戏的特性和理由上达成共识。有时候,我们能一致同意这样的事实:不同的认知兴趣引发方法论的差异(例如,解释学倾向的人类学和定律解释性(nomological-explantory)的自然科学或准定理性的行为科学之间的差异)参照阿佩尔,《理解与解释:一个先验语用学视角》(剑桥:麻省理工出版社,1984),以及“人类认知兴趣下的社会科学类型”,《社会研究》44(3),第425-470页,重印于《社会科学的哲学争论》,布朗编(布莱顿:哈维斯特出版社,1979),第3-50页,以及阿佩尔,《伦理与理性理论》(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6)。。正如康德所区分的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这里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理性。然而,辨识这些差异并不必然使我们假设在这些不同理性过程的维度【161】中没有内在的关联,因此,就像利奥塔所宣称的那样:“解放的目标与科学无关。”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第8页。我们会发现,在当今的人类状况下,全球正义和共同责任的伦理以决定性的方式依赖于关乎生态和社会经济事实的科学(的进步)知识。我发现如此假设是非常荒唐的:即一个论辩性对话的普遍实用主义会泯灭不同种类的语言行为之间的差异。\n如果最终我们必需要处理在那些具有文化依赖性的世界观点中不可比较的差异,包括处理不同的强伦理价值,我们可以遵循以下这个整全性原则:一方面,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最终全球化)的社会,我们能够也必须接受去容忍各种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也必须同样接受一些普遍性规范——其中有各种人权,以此限制有害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就是在面对人类共同问题诸如环境危机等,使不同文化不能和平共处或相互合作的特质。)参照阿佩尔,“善的多样性?从伦理观点看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积极容忍问题”,《理性法(RatioJuris)》10(2),第199-212页;及“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正义问题:对伦理对话的回应”,《追问伦理:当代哲学的论争》,理查德·科尔尼,马克·杜雷编(伦敦:劳特里奇,1999)。在这些情况下,寻求“以讨论达成的共识”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达成共识的方式既不是以“权威的工具”也不是以“恐怖”的工具来发生作用的(如利奥塔所建议的);参照罗蒂,《知识分子之墓与其他文章》,(巴黎:迦利出版社,1984),第81页,在这本书中罗蒂说到了“来自美国但尤其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一致同意)的恐怖”。相反,这种达成共识的方式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进行权力地位的纯粹斗争唯一的可能选择。论辩性对话打开一个自由的空间,不仅是为了共识,也是为了理智地争议,从而,为了每一个人都认为值得拥有的“革新(innovations)”和“发明(inventions)”。利奥塔对于后对话式哲学合法性的谴责,为反哲学策略的论证如何通过践言性自身冲突必然消解自身提供了一个最佳例证。这种自身冲突不仅仅在利奥塔挑战性的小册子《后现代状况》【162】(1979)中得到证明,在他的主要著作《分歧(Ledifférend)》(1983)中也得到证明。在那本书中,内在于“哲学终结”\n观点的践言性自身冲突以一种既明晰又恼人的方式显示着自身:它在两个针锋相对的态度之间制造了一个持续的斗争。一方面,利奥塔从行为上对特定的生活形式及其独特的语言学自我表达(及对世界的解释)方式显示出了一种感情上和评估上的兴趣;他反对所有官僚的和技术专家倾向,这种倾向通过语言上的明争暗斗迫使人们趋于一致。正因为此,不论利奥塔本人相信与否,他都完全同意普遍实用主义对话伦理明确的合法化策略。因为正如利奥塔所假设的,这种后对话哲学并没有指定任何事先固定的语言使用规则,而只是要求基本的准则,即对于语言的使用,所有可能的对话伙伴都有平等的权力和责任。另一方面,利奥塔在他自己直率的后对话中,拒绝了任何这样的准则。在他看来,对于论证不同有效性主张的所有可能批驳仅仅是一个“分歧(differend)”的不同立场,这就是说:“两个伙伴(或更多)之间的冲突事件不可能做出公平的决断,因为没有适用于彼此双方的判断准则。”我的翻译。利奥塔,《分歧》(巴黎:午夜出版社,1983),第9页。参照其后曼福瑞德·法兰克(ManfredFrank),《理解的边界:利奥塔与哈贝马斯之间的一个精神对话》(法兰克福:舒坎普,1988)。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说道:“说话就是在游戏的意义上战斗,言语行为已经坠入普遍的好战者领域。”利奥塔,《后现代状况》,10ff。在《分歧》中,紧随其后,利奥塔否认任何伦理关系是在主体间有效的。严肃地声称关于别人的道德义务是一个“丑闻”,道德义务实际上是一种“善的分歧(differendparexcellence)”。与康德相反,利奥塔声称\n:道德律的绝对性“外在于我”,这种绝对性巧妙地令其自己相信:它愿意自己退位以支持某个对等原则。按照利奥塔的思想,认识到一个“伙伴间共识的原则,或可交换性的原则,对话的原则”,这不是自由的真实法则;这种法则已经从理论上的对话非法地过渡到实践的对话,尽管自由与知识已被“深渊”隔离。因而利奥塔断定“没有伦理共同体。”利奥塔,《分歧》,第162,169,172ff176,182ff,184,186页。参照阿佩尔“交流团体的先天性与伦理的基础”,《哲学的转型》,第二卷(法兰克福:舒坎普),第358-436页。一个英文译本见阿佩尔《朝向哲学的转型》(伦敦:劳特里奇与柯甘·保罗(KeganPaul),1980),以及《伦理学与理性理论》(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6)。如果按照利奥塔后对话哲学的思想,不可能对任何事情进行合法化或批判。然而利奥塔本人充满热情地对许多事情进行合法化和批判。这种源始的践言性自身冲突,是利奥塔所有后现代主义独特论题破坏性挑战的源泉。我在这里无法进入细节,但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利奥塔的哲学给出了“哲学终结之后”哲学能成为什么的最后范例。“哲学终结”观点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是福柯和德里达。两位思想家著作的特定内容都是非常有趣的,但在我这个论题的语境中,我只能说他们此外还通过践言性自身冲突,代表着当今的自我解构哲学。德里达甚至可能会肯定这一评价,他会宣称我们只有试图克服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同时发掘其中的论辩性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后期海德格尔也追求这种思想,他提到通过VerwindenderMetaphysik\n克服西方形而上学),否则我们别无出路。但是对于践言性自身冲突的困境,我们无路可逃。在德里达的例子上,只是不宜于反驳通过标记一个“先验标签”进行呈现的可能性,从而仅仅传达这一宣称的事实。必然有其他的方法处理德里达对于“差异”(即意义差异的持续生成)的发现以及【164】标记过程的“撒播”。我相信,我们能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帮助下找到这样一种方法,这种符号学不仅能够认识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无限指涉,还认识到这种指称功能三项合一的结构,这就避免了德里达式的从符号学到符号主义的转换。参照阿佩尔,《先验符号学与发展的假说式形而上学:对周期性后康德哲学问题的皮尔斯或准皮尔斯回答》,《皮尔斯与当代思想》,克特勒编(纽约:福特翰大学出版社,1995),第366-397页,重印于阿佩尔《朝向先验符号学》(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4),第207-230页。在福柯的例子上,我发现甚至不用参照他对哲学的自我理解,就能够很容易地对他在历史探寻中的发现致以敬意。人们也许会承认,在所有划时代的体制分支中,在社会现实的语言学解释中,通过“真理体制”交织在一起的“管辖措辞(jurisdiction)”和“真话措辞(veridiction)”都在发生作用;然而,人们还是会坚持在对真理的科学意愿和对权力的政治或准政治意愿做出分析性的分离。人类科学必须事实上是对意识形态持续批判的主题和目标,但人类科学不能被取消自身有效性主张的尼采式(道德的和真理的)“系谱”取代。参照尤尔根·哈贝马斯,《话语的现代性》(法兰克福:舒坎普,1985),第十章。\n其实,在我看来,尼采是这种思想方式或方法的经典创始人,这种思想撕下每一个真理主张以及道德光明的面具,消解其自身的有效性主张。这种涉及践言性自身冲突的模式并不能克服西方形而上学,它更像是一种自然主义者的还原论,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的反形而上学,一种对现代科学还原解释的形而上学误用。在叔本华的思想中,这种反形而上学采取了一种功能性理性还原的形式。尽管德国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已经把自由意志整合在理性之中,对叔本华来说,理性除了作为自然意志——生命驱使或冲动——的必然功能以外什么也不是。在试图解释人类为什么以及如何会为了真理的兴趣和怜悯(同情)的道德情感而否定自然意志的时候,叔本华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尼采试图克服叔本华的【165】不一致性,把自然意志断言为“权力意志”。但这只是使潜在的践言性自身冲突在功能性还原主义中更加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延续了尼采式的反形而上学还原,一种对柏拉图理性实体化或逻各斯实体化或心灵虽然“心灵”也不甚准确,但鉴于“努斯”更让人不知所云,遂采用“心灵”这一较通俗的说法。(nous)实体化进行自我消解的反转。也许(德里达意义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属于现代理性论,也即是对世界的客体化,海德格尔把这种客体化归于(科学和技术的)“框架又译“底座”(Gestell)”的标签下,或者是现代思想“理智化(rationalization)”的类型中,即就像马克斯·韦伯和霍克海默或阿多诺那样,将“意义终结(means-ends)”的绝对化或“工具”理性演绎到极点。\n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理性主义必然会遭受来自理性观点的批判。这不会是理性对理性进行的自我摧毁式的批判,而是从论辩性对话的哲学理性观点上,对某种抽象理性模式的现代性绝对化进行批判。参照阿佩尔,“对理性总体性批判的挑战与关于理性类型的一个哲学理论的规划”,《理性及其他》,弗兰德里布,哈德森编(牛津:贝尔格,1992),第23-48页(重印于阿佩尔,《伦理学与理性理论》,第250-274页)。无论如何,由“哲学终结”观点发起的对理性的总体性批判不能回答关于在我们的时代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因此,让我们现在来考虑哲学转型的问题。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