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25 发布 |
- 37.5 KB |
- 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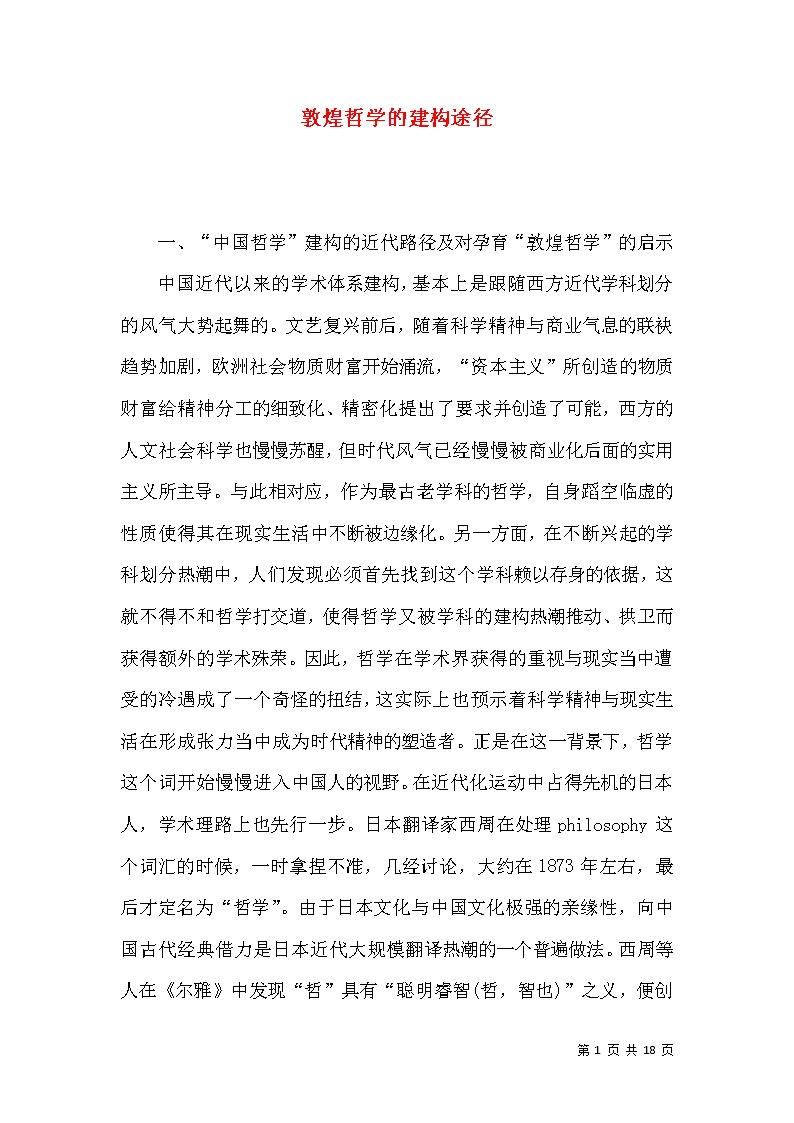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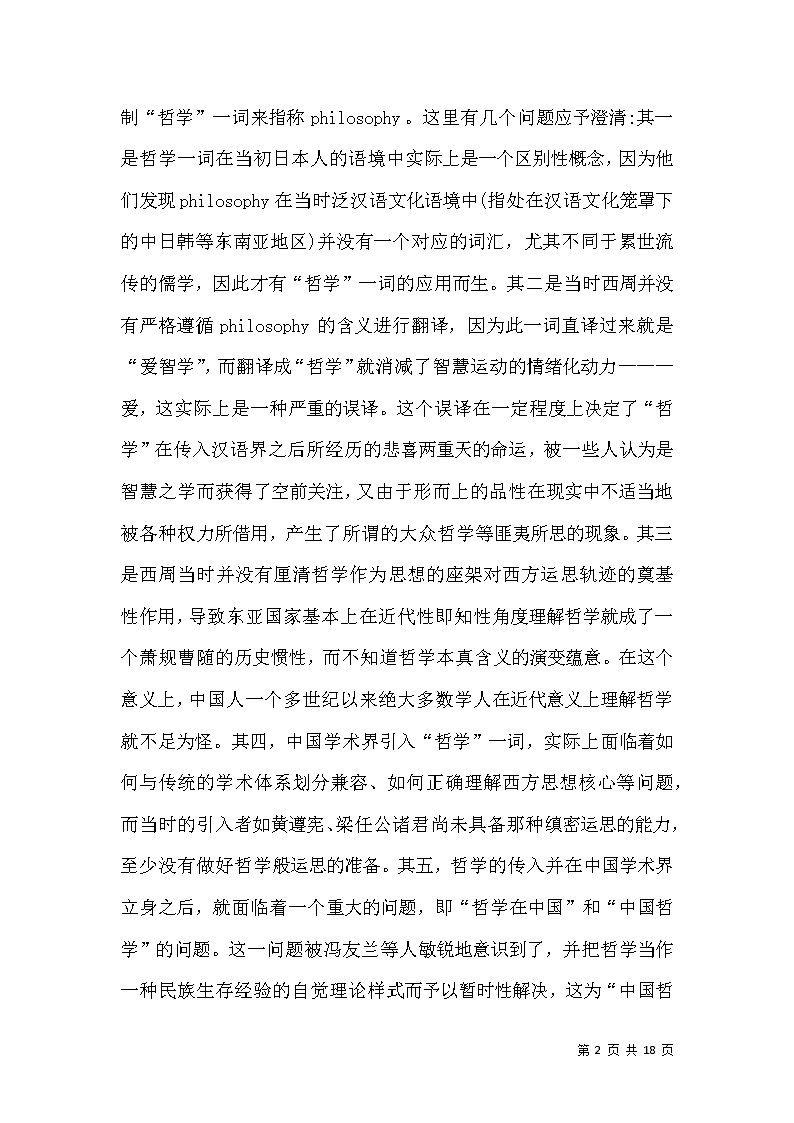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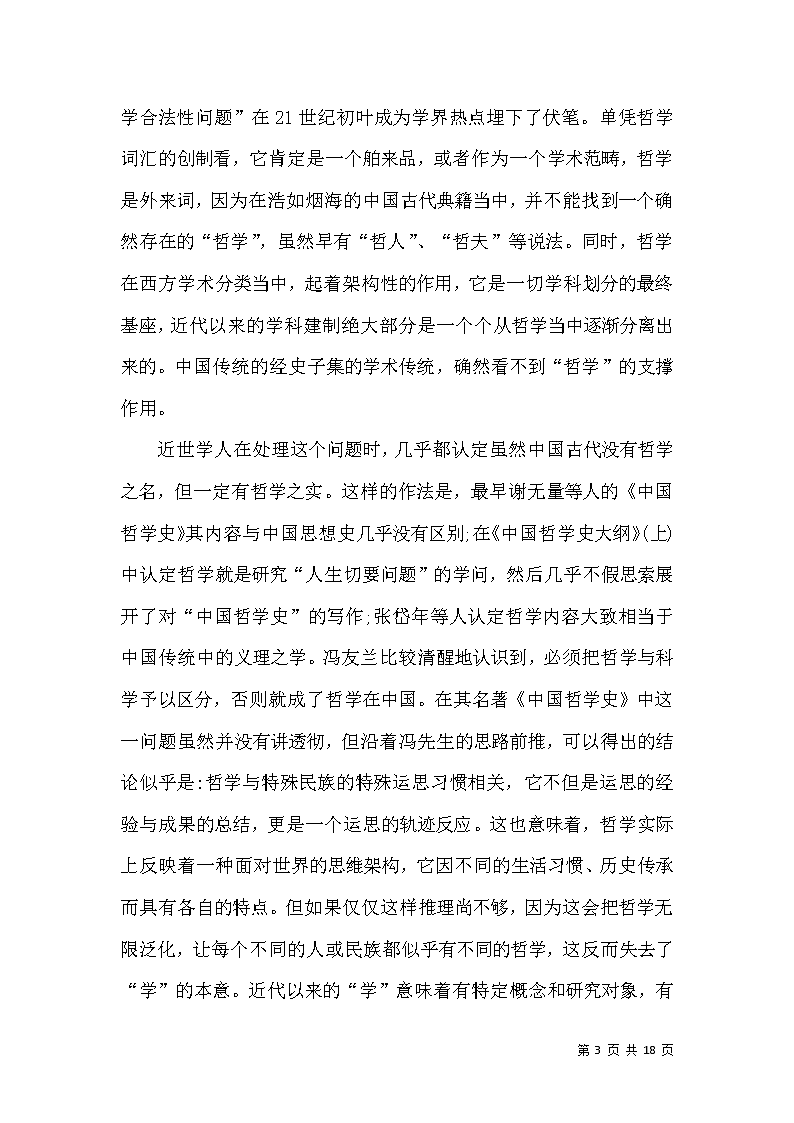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敦煌哲学的建构途径
敦煌哲学的建构途径一、“中国哲学”建构的近代路径及对孕育“敦煌哲学”的启示第18页共18页\n敦煌哲学的建构途径一、“中国哲学”建构的近代路径及对孕育“敦煌哲学”的启示第18页共18页\n敦煌哲学的建构途径一、“中国哲学”建构的近代路径及对孕育“敦煌哲学”的启示第18页共18页\n敦煌哲学的建构途径一、“中国哲学”建构的近代路径及对孕育“敦煌哲学”的启示第18页共18页\n敦煌哲学的建构途径一、“中国哲学”建构的近代路径及对孕育“敦煌哲学”的启示第18页共18页\n敦煌哲学的建构途径一、“中国哲学”建构的近代路径及对孕育“敦煌哲学”的启示第18页共18页\n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建构,基本上是跟随西方近代学科划分的风气大势起舞的。文艺复兴前后,随着科学精神与商业气息的联袂趋势加剧,欧洲社会物质财富开始涌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给精神分工的细致化、精密化提出了要求并创造了可能,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慢慢苏醒,但时代风气已经慢慢被商业化后面的实用主义所主导。与此相对应,作为最古老学科的哲学,自身蹈空临虚的性质使得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在不断兴起的学科划分热潮中,人们发现必须首先找到这个学科赖以存身的依据,这就不得不和哲学打交道,使得哲学又被学科的建构热潮推动、拱卫而获得额外的学术殊荣。因此,哲学在学术界获得的重视与现实当中遭受的冷遇成了一个奇怪的扭结,这实际上也预示着科学精神与现实生活在形成张力当中成为时代精神的塑造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哲学这个词开始慢慢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近代化运动中占得先机的日本人,学术理路上也先行一步。日本翻译家西周在处理philosophy这个词汇的时候,一时拿捏不准,几经讨论,大约在1873年左右,最后才定名为“哲学”。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极强的亲缘性,向中国古代经典借力是日本近代大规模翻译热潮的一个普遍做法。西周等人在《尔雅》中发现“哲”具有“聪明睿智(哲,智也)”之义,便创制“哲学”一词来指称philosophy。这里有几个问题应予澄清:其一是哲学一词在当初日本人的语境中实际上是一个区别性概念,因为他们发现philosophy在当时泛汉语文化语境中(指处在汉语文化笼罩下的中日韩等东南亚地区)并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尤其不同于累世流传的儒学,因此才有“哲学”一词的应用而生。其二是当时西周并没有严格遵循philosophy的含义进行翻译,因为此一词直译过来就是“爱智学”,而翻译成“哲学”就消减了智慧运动的情绪化动力———爱,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译。这个误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哲学”在传入汉语界之后所经历的悲喜两重天的命运,被一些人认为是智慧之学而获得了空前关注,又由于形而上的品性在现实中不适当地被各种权力所借用,产生了所谓的大众哲学等匪夷所思的现象。其三是西周当时并没有厘清哲学作为思想的座架对西方运思轨迹的奠基性作用,导致东亚国家基本上在近代性即知性角度理解哲学就成了一个萧规曹随的历史惯性,而不知道哲学本真含义的演变蕴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学人在近代意义上理解哲学就不足为怪。其四,中国学术界引入“哲学”一词,实际上面临着如何与传统的学术体系划分兼容、如何正确理解西方思想核心等问题,而当时的引入者如黄遵宪、梁任公诸君尚未具备那种缜密运思的能力,至少没有做好哲学般运思的准备。其五,哲学的传入并在中国学术界立身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哲学在中国”和“中国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被冯友兰等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并把哲学当作一种民族生存经验的自觉理论样式而予以暂时性解决,这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在21世纪初叶成为学界热点埋下了伏笔。单凭哲学词汇的创制看,它肯定是一个舶来品,或者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哲学是外来词,因为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当中,并不能找到一个确然存在的“哲学”,虽然早有“哲人”、“哲夫”等说法。同时,哲学在西方学术分类当中,起着架构性的作用,它是一切学科划分的最终基座,近代以来的学科建制绝大部分是一个个从哲学当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传统,确然看不到“哲学”的支撑作用。第18页共18页\n近世学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几乎都认定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但一定有哲学之实。这样的作法是,最早谢无量等人的《中国哲学史》其内容与中国思想史几乎没有区别;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认定哲学就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的学问,然后几乎不假思索展开了对“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张岱年等人认定哲学内容大致相当于中国传统中的义理之学。冯友兰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哲学与科学予以区分,否则就成了哲学在中国。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史》中这一问题虽然并没有讲透彻,但沿着冯先生的思路前推,可以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哲学与特殊民族的特殊运思习惯相关,它不但是运思的经验与成果的总结,更是一个运思的轨迹反应。这也意味着,哲学实际上反映着一种面对世界的思维架构,它因不同的生活习惯、历史传承而具有各自的特点。但如果仅仅这样推理尚不够,因为这会把哲学无限泛化,让每个不同的人或民族都似乎有不同的哲学,这反而失去了“学”的本意。近代以来的“学”意味着有特定概念和研究对象,有着通约化的语言,是可学的,可理解的。由此只有具有群体所遵循的、稳定有效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运思轨迹和经验,才可能被称之为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范式建构中居功至伟,但他们共同受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哲学观”属于新实在论是大家的共识,此看法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观点。这样,(中国)哲学就具有了“宗教与科学”的性质,但又不同于二者。作为面对世界的运思经验,哲学实际上担当着世界观的作用,但这个世界观是靠哲学自身内在的演化规则来执行、达到的,因而不同于宗教化不假思索的信仰。也正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哲学也区别于科学,因为,科学要剔除了人的主观性,达到假设的某种客观性,而哲学恰恰包含着人的情绪、信仰、运思习惯等,它是一个现实的然而又是历史的产物,单靠科学的冷静观察或客观实验无法提供一个完整有效的世界观。此问题在近代科玄论战中得以发酵,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路向,也说明哲学在中国学术语境中的多义性。与其相对应,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首倡“敦煌学”,只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其时并没有对敦煌学的内涵外延予以清晰考察,更多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后来敦煌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广,并逐渐成为国际显学。可见,一个学术概念在创立之初,其含义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敦煌哲学”创立之初当应有此学术雅量。二、从哲学的分类到“敦煌哲学”成立之可能第18页共18页\n如果沿着philosophy所展开的轨迹回眸,那个“物理—后物理”所构成的形式化运思构架附着了几乎所有哲学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核心是“本质—现象”所衍生的。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有清算这个构架的冲动,直到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崛起,前者悬置争论,后者企图通过严格的语义分析,一劳永逸清除形上学(后物理学)所制造的语词假相。如果说传统哲学纠缠于是与存在,哲学就是一门关于“是”的学问,现象学以不“是”什么自居,分析哲学则以语义诊断而存身。这两大现代哲学思潮在当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诘难,因为现象学作为方法有效并附有启发性,但其创始人胡塞尔一开始所谓的“本质直观”就有重蹈传统形上学的嫌疑,这也是海德格尔后来背离现象学运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分析哲学在一开始构建严格的“逻辑语言”,直到后来维特根斯坦等人意识到语言的“游戏性”,重新回到生活(自然)语言,意味着坚决清理哲学语言已经几乎不可能了。但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当代欧美哲学界慢慢意识到,所谓哲学,就是那个决定了西方人运思构架与轨迹的东西,并且这个东西,是古希腊人的一种创造,是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沿着“本质—现象”这一构架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等人认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运思方式都不是哲学化的,也正是类似这一论断,引爆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如果把“费罗索菲Philosophy”当成西方人的那个大思,那么沿着这个思路就会对通常的学科划分造成致命性伤害。它意味着哲学就是一个运思的构架,无法分类且无法修饰,因而由此所谓的管理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其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如果哲学是无法分类的,那也意味着,我们即将讨论的敦煌哲学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分析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语言必须回归日常生活,它是人们之间的游戏。这也意味着包括学术语义在本性上也并不是严格的,因为它的有效性依赖另一方的认同。后现代哲学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冲动中,无法避免由此而导致的价值虚无。福柯敏锐地洞见到知识与权力具有同构关系,但无法清理掉这个中心。这也意味着,约定俗成的东西仍然具有它的某种合理性。第18页共18页\n在近代兴起的学术划分热潮中,哲学也被一次次附加了许多修饰语,随着研究重点和实用性的双重需求,哲学被实用主义、存在主义、新实在论等一次次命名。如果考虑到这个热潮,意味着当初哲学这个词在中国学术界误打误撞、生根发芽,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自己的合法性。语言的有限性意味着命名本身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哲学可以严格意义上理解,也可以在更宽泛意义上看待,即哲学可以狭义化,也可以广义化。哲学在中国学术界的落地生根,还并不完全由语言的游戏性决定,它实际上牵涉到中国思想经验与一个被哲学构架决定了的整个西方学术体系如何对话的问题。只有通过共名的哲学,才可能依循现代学术语言对中国传统运思经验予以解读,否则会面临着无法对传统进行言说的尴尬。近代中国民族苦难史昭示,完全依照过去本有的汉语学术划分框架,已经无法在科技主导的时代精神中站住脚,即使中国传统运思方式持久有效,但必须经过现代化的阐释,形成一种对话的姿态才能让其内部的活力得以彰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成立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我们今天谈论敦煌哲学开出了思路。它在源头上给我们论述敦煌哲学以言语的合法性。对于那些把敦煌与哲学连接起来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至少在近代哲学传入中国的历程看,我们的判断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当敦煌学已然约定俗成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后,就面临着其自身内涵的理论阐述问题。姜亮夫先生曾说:“……所以我们现在将研究敦煌所有的东西的学科称之为‘敦煌学’。这个‘学’字是什么意思呢?‘学’就是说一种有系统,有原始发生、发展到衰落的次序的,就叫做学。敦煌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学。”[1]但学之为学在严格的学科建构中,必然有着哲学的机理,或者,在近代的学科建构中,通常只有把学科的基础挂靠到形上学(哲学)上,这个学科的成立才就具有了合法性。就敦煌学来说,这一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在现有的学科分工中,敦煌学在社会、人文科学的序列中排位就处在尴尬的境地。周一良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说,‘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所以他赞成把“敦煌学”永远留在引号当中。[2]但这个困难并没有阻挡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从刚开始的敦煌遗书研究扩展到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敦煌学理论等等,其中敦煌学理论就必须直面敦煌学内在根据的问题。“从目前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3]也有人认为:“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4]概而言之,敦煌哲学在语义的本质上具有成立的可能性,在敦煌学的发展当中更具有找出其内在隐线、为学科之成立找到合法性的迫切需求。三、敦煌哲学的根本依据:敦煌性第18页共18页\n敦煌哲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必然有其内在的根据,这就要求必须对敦煌哲学本身的特质予以揭示。在“敦煌哲学”的构架中,“敦煌”构成了修饰语,人们不仅会心生疑窦:为何是敦煌?假如把敦煌仅仅看作一个地域性概念,马上会引发人们的质疑:是否能够把敦煌置换成别的地名?譬如天水,譬如酒泉,甚而甘肃哲学岂不更加显得地域辽阔?这里首先必须回应敦煌作为饰词的基本含义。作为地名意义上的敦煌出现,在汉语文献中最早见于《史记》,当时张骞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明确提到了敦煌二字。后世论者也曾争论敦煌地名的由来,有的甚至说敦煌一词来自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5]但汉代以后敦煌作为地名,其基本含义以这样的解释为准:“敦,大也,煌,盛也”。按我们的理解,弄清一个地名的来历是必要的,这是文化学上造成蝴蝶效应的初始因子,即文化具有历史的惯性,初始形式具有决定后世发展的巨大作用,但过分纠缠于词源学的考察并无法真正揭示历史文化的秘密,有些词汇在历史的流变中发生了重大的语义变迁,以讹传讹、歪打正着的事情大为存在。如果我们仅仅把敦煌当作一个地名,就无法让其文化含义凸显,而“伟大辉煌”的本意则透露了“敦煌”的含义,歌颂军功武力的地名外溢出来,变迁为一个富有精神承载力的重大词汇,这甚至可以成为理解敦煌哲学的一个入手处。第18页共18页\n在西汉初设河西四郡的时候,敦煌作为正式的地名被固定下来,这里成了几大文明的交汇点,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是各种文化交流的大动脉。20世纪以来,由敦煌学不断派生出新的学科分支,如敦煌文化、敦煌文学、敦煌艺术等等。这些学科按其学科的建制而言都有各自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质。颜廷亮先生曾对敦煌文化有过自己的总结:“敦煌文化的独特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敦煌文化的灵魂,乃是根深蒂固的中原情结,乃是透骨入髓的乡土情感,乃是这两者水乳般的交融为一。”[6]穆纪光先生在对敦煌艺术哲学进行总结的时候,“没有对敦煌艺术涉及的所有哲学问题进行普遍论述,而是从‘存在论’的观点出发,对敦煌艺术形式背后所隐含的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和叙述。”[7]特别是对佛教经典的改造与发挥出发,阐发其蕴涵的艺术哲学的。两位先生显然已经触发到了作为文化构架的敦煌可能附着的精神内涵,颜先生首次讨论了敦煌文化精神,穆先生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给予了敦煌哲学一个有益的视角,那就是佛经精神与世俗化生活在敦煌的融合。但依照这些的观点尚不能让敦煌自身作为哲学的生发地予以现身。季羡林在多年前对敦煌的文化定位有过精妙的总结,它对于理解敦煌现象乃至发掘敦煌哲学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他断言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只有在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发生了汇流,“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8]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为何是敦煌而不是别的地方?作为一个地名的敦煌为何能够承载起一种精神的嘱托?敦煌作为四大文明的汇流处,其重要地位不可替代,百年前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不但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辉煌,更让敦煌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集散地逐渐浮现。敦煌哲学的成立当从“希腊性”意义上予以揭示。黑格尔曾说,当欧洲人提到希腊的时候,自然会有一种精神家园感。这源自希腊从一个古代的地域国家名称走向了文化的饰语。当我们历经努力,打开敦煌哲学的地形地貌的时候,也许那种久久回荡在历史当中的精神家园感也会重现光辉,带来久违的历史人文温度,久沐在敦煌文化中的古代人有着强烈的中原情结,这个情结实际上也是家园感的反映,而近世以来,凡是被敦煌文化所吸引感染的学人,无不在“敦煌”的感召下生发出巨大精神敬畏与心灵震动。由此,敦煌本身就成为一种饰词,敦煌性恰恰对照敦煌的“伟大辉煌”而生,它没有脱开敦煌地名的含义,但又超越于具体的地域名称。如果对照希腊性人的理性精神的觉醒,则敦煌性应当是基于伟大空间的共生性这一特质,所表现出的大气包容、共生共存、和而不同。也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是敦煌哲学而不能轻易妄言酒泉哲学、甘肃哲学等这样的说法。敦煌哲学存在的内在根据是什么?是人为创制一种哲学还是基于历史精神的结构发现一种哲学?那是一种精神的暗流,是历史的隐线,是潜伏在伟大辉煌的敦煌文化下的精气神,它所需要的是重见天日,需要在历史的河床中找到它奔腾的力量。因此,敦煌哲学并不是建构,而是一种发现,一种荒芜的精神地貌的重新耕作,焕发新的思想朝气。第18页共18页\n当我们把哲学从严格的证明体系引申过来,让其接受其他语词修饰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哲学可以随意接受打扮?如果这样做,势必失去哲学作为引导人之所思的严格性,或者哲学失去其作为思维构架的基础性作用,那么,即使敦煌哲学成立,也仅仅是为当前学界假借分科命名的学术圈地运动提供了一个谈资,而无法让作为严肃的学科保持久远的生命力,更无法对敦煌学的研究给出一个方法论的支持。但如果在成果斐然、引世瞩目的有关敦煌学的研究中,潜心再潜心,发现那纷繁的敦煌现象后面的精神主线,它不但横贯敦煌学的始终,而且能够为未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方向性甚至是方法论的支持,那它不是敦煌哲学又能是什么呢?反过来讲,敦煌文化在历史上辉煌了上千年,并且在20世纪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它所涉及的内容不但囊括了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和所有文化形式,而且成了古代文明的集散地,各种文化、各种文明都在此有着深深的烙印,敦煌曾是世界文明的大舞台,并能够保持长久的辉煌,而不是过眼沙尘。这就启迪后人,一种文化能够长久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内在理由。敦煌文化庞杂博大而有序不乱,百花竞放又不失下自成蹊,这必然有种隐含的精神张力来支撑其繁盛,否则敦煌文化就早已在历史的风沙中坍塌了。那么,这个精神张力是什么呢?唯有敦煌哲学。严格意义上说,敦煌哲学不是建构的问题,而是发现的问题,后人仅仅是发现了敦煌哲学并予以命名。敦煌哲学的成立必须从揭示其自身的特质入手。四、从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回到敦煌哲学第18页共18页\n欲对敦煌哲学的特质予以揭示,就必须对中国哲学的特质予以审察。敦煌哲学概念只能隶属于中国哲学,这二者的关系是子集与母集的关系。但敦煌哲学也一定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哲学,它一定是把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质加以张扬、发挥、放大了,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精神特质。以下当我们讨论中国哲学特质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据敦煌哲学的特殊性,更加强调了中国哲学某一方面的特质。如果我们放弃对“哲学是一个证明体系”的硬性规定,而把哲学当作更加始源性的运思基座,则中国哲学当是中国人运思的轨道及其痕迹。从“物理—后物理”的运思构架出发,在形式逻辑的指引下,具有时空含义的世界,具有逻辑冷硬性的真理,具有存在意义的自我等一系列概念被创制出炉,这种具有几何性的思的经验并不为中国古代人熟悉。或者我们更加有把握的说,这种运思经验没有成为中国学人的主流方式。中国哲学的特质恰恰是在中外哲学对比中现身的,但对比的前提必然具有某种相似的问题、相同的对象。就中国哲学处理的主题而言,它要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神灵的问题予以自我解读,就此来说,中西方哲学都在“自我—他者”这个主题的框架中来审视人在宇宙当中的地位。无论是后世以恩格斯为代表所谓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是自尼采、海德格尔之后西方人对“存在与存在者”的执著,实际上都是人面对天地万物、自我神明,要对自我进行一个价值定位,寻访到心灵归宿地,由此找到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此来说,范鹏先生关于敦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总结甚为恰当,他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整体的中国哲学的境界和精神当然也就必然是敦煌哲学的精神。”[9]在完成形式化的运思框架后,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哲学就主宰了西方人的运思轨迹。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一旦思想,就是哲学的,就是处在“物理—后物理”的张力扭结中,而一旦给出一个不言自明的开端,如公理、概念、假设、条件等,就会在逻辑思维的推力下,呈现出定理、推理、结论等。中国哲学面对天地万物并不是采取严格的形式逻辑,而是一直处在自然思维的要求中,它在开端处把人看作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是万物之灵长,但绝非万物之主宰。换言之,主体意识在中国哲学那里是隐忍的,而不是张扬的。中国人在处理“自我—他者”这个思维扭结的时候,并不是把自我抽离出来,而是首先把自己归于这个整体,元素寓于关系中,关系的作用远远大于单个元素的性质,阴阳五行的生克变化都没有固定的好坏,而是遵循彼此的平衡。在中国哲人眼里,人是万物之一种,人的最高境界并非是从万物当中突出出来,而是如何让自己化为万物的一部分。就此来说,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既是古代生活经验的理性总结,也实际上是一种赖以安抚自身存在的信仰。中国哲学既是有理性的,但又由于在运思的开端处,就把自身看作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所以又十分重情感。后世引申出的辩证思维、整体观念、实事求是等实际上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挥。人与万物的须臾不可分,这既是理性的认识,又是生活的信仰,使得中国哲学在整体中见部分,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讲求共赢共生,最后发展出一个基本理念:和。第18页共18页\n就此来说,中国哲学并没有开出严格几何学意义上的世界,没有原子化的自我,没有过分的“自我—他者”关系的严重紧张,而是给出了具有理性和情感相交织的天下、道理、和合等。后世论者如列维•布留尔等人在人类学的考察中有所谓“原始思维”的说法,把这种比附思维区别于现代人,或者把一切具有比附性质而不符合逻辑分类的思维都归结为原始思维,带有明显的逻辑原教旨主义。从处理矛盾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尚和而西方哲学尚斗的路径是清晰的,且很难说谁高孰低的。也许,从一个局部讲,尚斗的理念更加具有战斗力,更加直接有效,但以道观之,从万物并流而不相害的信念出发,尚和恰恰表明了万物变迁的常态,散发着浓重的温情主义。以张载为代表提出的所谓“太和”观念中,中国古人早看到了矛盾双方斗争的一面,但更多强调“仇必和而解”,这区别于18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运思框架在中国哲学的基本符号即阴阳五行、八卦动静中已经完全具备。在“阴阳”的运思框架中,世界被中国人早早划分为可见与不可见的两部分,而《周易》中强调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给出了运思的轨迹与归宿:道。人之所要做的仅仅是找出不同层面的道,并力争挣脱“技”的束缚。健康的家庭、社会与个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保持阴阳五行的动态平衡,而并非偏于一方去消灭另一方。这就使得和的观念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不是没有原则的和稀泥,不是骑墙的乡愿,而是坚持中庸之道的包容,是“多样性的统一”。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关系比单独的元素更加重要,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性的主宰,而是无声的渗透,保持和的状态。同时,中国哲学的原始眼界是阴阳,把天地万物首先划分为可见与不可见两部分,这就为泛神灵的存在留下了余地,中国哲学不仅仅是理性的产物,也包含了信仰的对象。五、敦煌哲学可能的核心观念:和第18页共18页\n欲让敦煌哲学现身,必须涉及到对敦煌哲学可能的特质之揭示。文明的交汇地为数不少,甚至可以说,任何文明的边缘地带都可能是文明的交汇地,为何敦煌能够占有特殊的位置?季羡林先生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对敦煌以及新疆哈密地区文化丰富性的总结,并一再声称敦煌是世界的。把这个问题再清晰化,也即为何敦煌能够负载起一种精神气质的嘱托?亦即敦煌哲学为何能够成立?可能的回答是:敦煌哲学将中国哲学的和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敦煌哲学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凡是对敦煌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的再认识。敦煌哲学的特质将深化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反过来,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也必将规定着敦煌哲学的内涵。除过和之外,中国哲学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价值理念,如重伦理纲常、重天道王权,由此引发对孝道、仁爱等诸范畴的阐发。但我们认为,在敦煌哲学中,和的观念是根本性的,它起到了统摄敦煌学的作用,也应是敦煌哲学之魂。我们前面从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和”入手,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初步总结。而我们看到,敦煌哲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在于其内在构架中时时处处都体现出的和的观念。首先,从和的表现看,敦煌作为几乎古代所有文明的交汇地,让所有的文明形式都留下了痕迹。无论是中国儒家文明,还是古希腊文明,还是印度佛教文明,抑或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在敦煌有着各自的痕迹,都书写了自己的特质。甚而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其他古老文明形式,也都在敦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些足迹通过敦煌石窟以及百年前发现的敦煌藏经洞为载体,每个文明形式甚而是亚文明都能够在敦煌找到曾经的足迹,这种包容大度没有“和”的精神支持是无法想象的。第18页共18页\n其次,敦煌不是仅仅把各种文明做了简单的杂糅搅拌,不是简单的文化集散地,而是创造出了属于自身的文化形式即敦煌文化,也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在敦煌石窟为代表的艺术形式中,反映的不仅仅是佛家的处世理念,而是常见儒家的圣贤、道家的神仙,凡圣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统为一体,甚而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的理念、特质也得到了反映。一部经文能够有多种文字书写,一个石碑镶嵌多种文字,这些百川汇流、有容乃大的特质在敦煌随处可见。换言之,各种文明形式都能够在敦煌找到自己的根脉,并且都是生长在鲜活的体质上的,敦煌是各种文明之汇流,更是各种文明之融合地、生长地。取百家之长而独树一帜,这表明了“和”对各种文明因素的强大的粘合、再生能力。反过来,只有和才能够把形式迥异的文化母体统摄到一个整体中。再次,应该看到各种文明交汇形成新的文化形式的难能可贵,或者非常万难。就此来说,世界上唯有敦煌,才能以一个地域来命名一种精神的形式。在敦煌文化生成的时候,四大文明形式都已经各自成熟。文明形式的成熟意味着对文明他者的拒斥,这尤其反映在宗教文化中。由于宗教信仰的绝对性,必然会导致宗教信仰的排他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常见的事情,尤其欧洲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宗教战争史。而敦煌恰恰包容了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明形式。唯有和才让文明剑拔弩张的对峙柔软下来,消弭这种张力只有中国做到了,更进一步说,只有敦煌做到了。第18页共18页\n最后,我们反过来推理,敦煌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艺术形式,必然与一个根本的观念有关,而融和各种文化的剑锋,软化各种文明的张力,唯有和。敦煌的雕塑、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从属于更大范围的敦煌文化,而敦煌文化所反映出的海纳百川、文明竞流的特征,必然有种基本的理念来支撑它,除过中国哲学中的和,无他者可以替代。和在这里不但是一种价值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而且也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思索轨迹,是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正因为有了和,敦煌成为了自身,正因为有了和,敦煌哲学立起来了,敦煌文化获得了灵魂,敦煌艺术有了大的依托,敦煌具有了精神家园的意味。和不是简单的元素堆积,不是原子变量的力量拉扯,而是动变中关系的此消彼长,是指向生的取长补短,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决斗。敦煌哲学之成立恰恰在于以一种决然而然的特质把中国哲学的和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它向世人昭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明是可以和合共处的,是可以实现共赢的,是能够在相互学习中获得共生效应的。和不但是价值观,而且能够成为一种方法论。从这里出发,敦煌哲学不但跃出隐蔽的精神领地,而且给世人理解敦煌文化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附着在“敦煌”身上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可能变得豁然开朗、别有洞天。敦煌哲学以和为基本内核,它会引导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学理念,“和而不同”表明了万物的变化的动力,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和而生气”,气聚为生,气散为死,敦煌哲学的和与中国哲学重生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完全一致。有了和,中国哲学讲求的生生不息就有了源头;有了和,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就有了新的思路,这迥异于西方所谓“哲学就是学会死亡”的基本理念。同时,它也给出了日后可能有待深入的重大研究领地,譬如:“和”的自身的依据是什么?“和”如何在敦煌哲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在敦煌文化中得到更加细致有序的体现?敦煌哲学为何能够把尚和的中国哲学基本理念发挥到极致?它对未来的文明对话或者新的文明样态有何启发?等等。这将是另外的问题。作者:成兆文单位:甘肃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第18页共18页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