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9 发布 |
- 37.5 KB |
- 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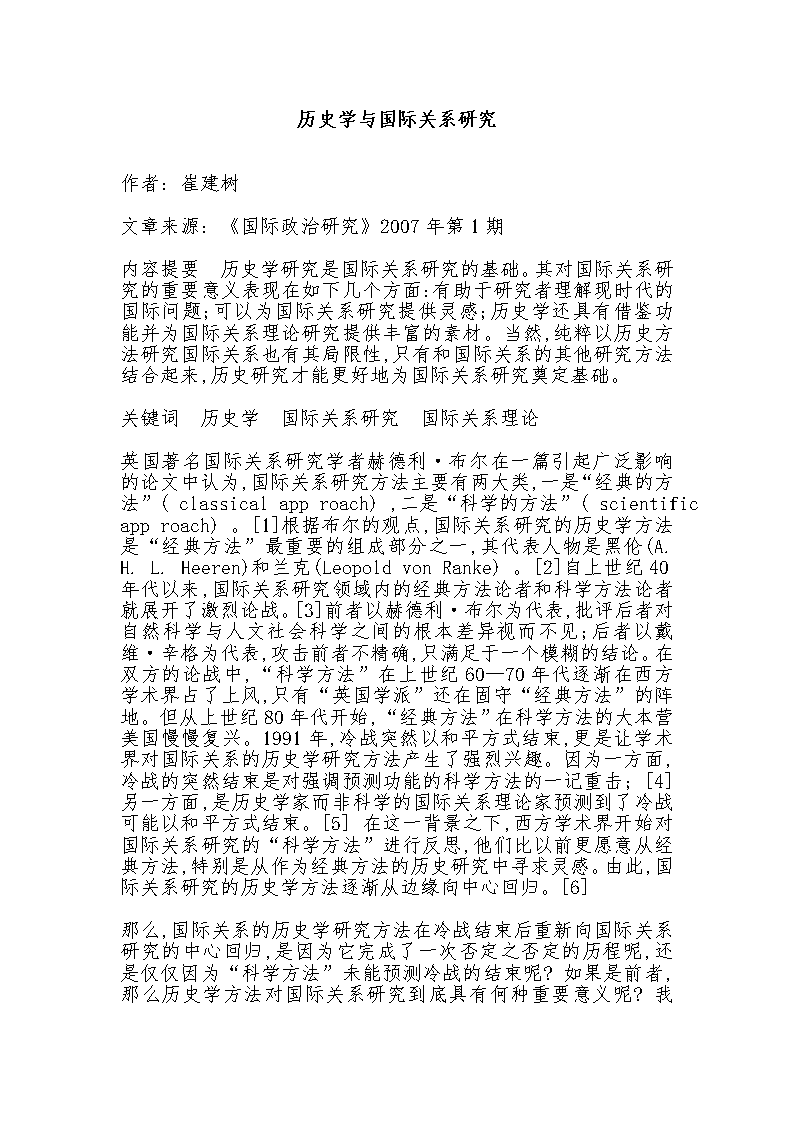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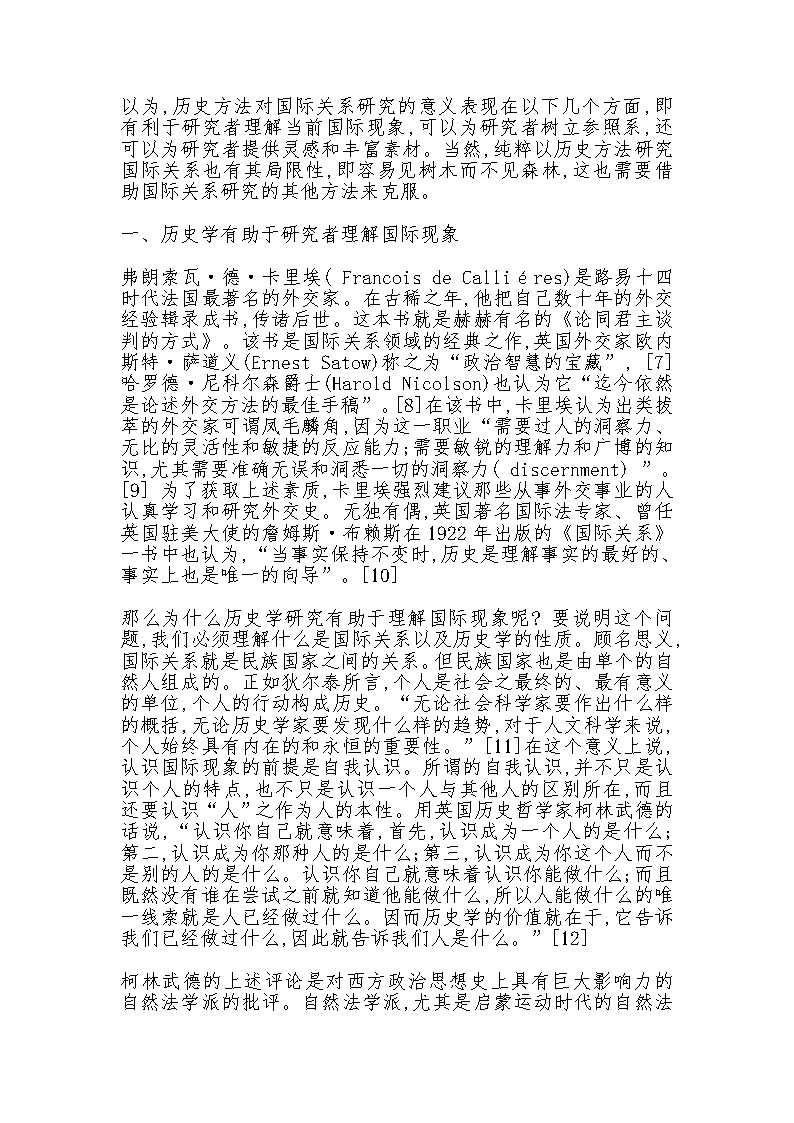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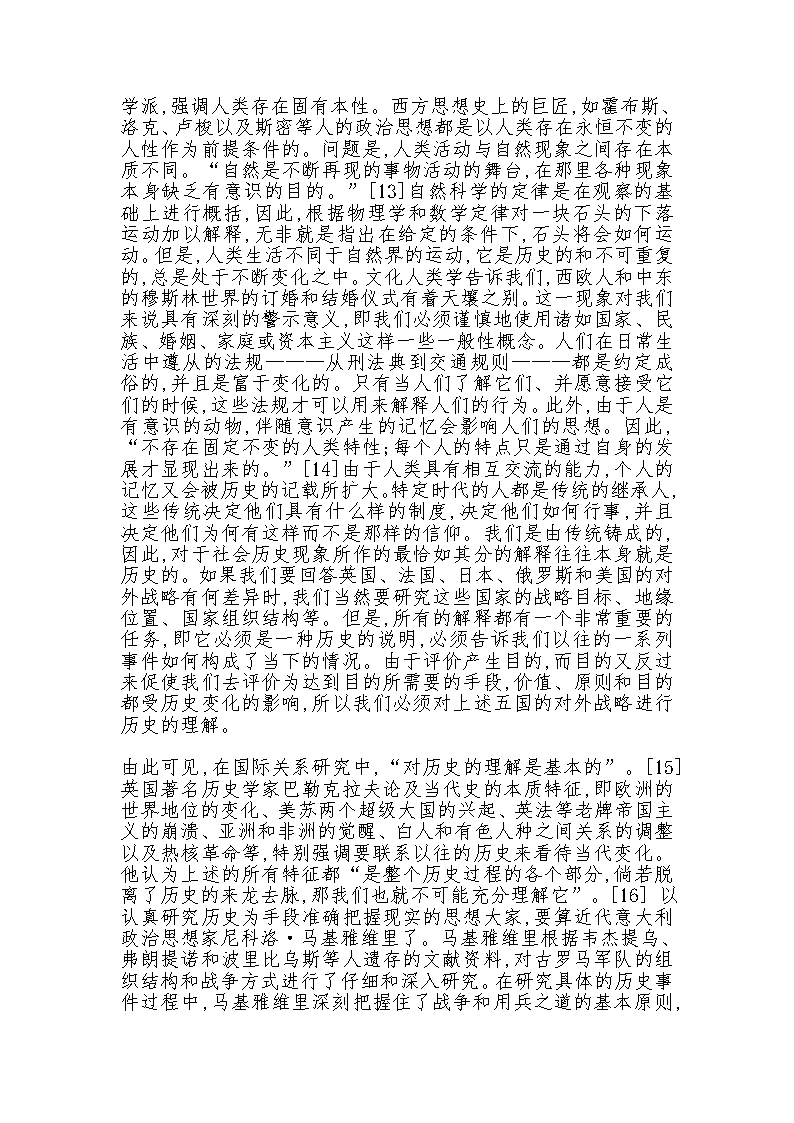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作者:崔建树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内容提要 历史学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现时代的国际问题;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历史学还具有借鉴功能并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和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基础。关键词 历史学 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赫德利·布尔在一篇引起广泛影响的论文中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经典的方法”(classicalapproach),二是“科学的方法”(scientificapproach)。[1]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方法是“经典方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代表人物是黑伦(A.H.L.Heeren)和兰克(LeopoldvonRanke)。[2]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的经典方法论者和科学方法论者就展开了激烈论战。[3]前者以赫德利·布尔为代表,批评后者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视而不见;后者以戴维·辛格为代表,攻击前者不精确,只满足于一个模糊的结论。在双方的论战中,“科学方法”在上世纪60—70年代逐渐在西方学术界占了上风,只有“英国学派”还在固守“经典方法”的阵地。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典方法”在科学方法的大本营美国慢慢复兴。1991年,冷战突然以和平方式结束,更是让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强烈兴趣。因为一方面,冷战的突然结束是对强调预测功能的科学方法的一记重击;[4]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而非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预测到了冷战可能以和平方式结束。[5]在这一背景之下,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进行反思,他们比以前更愿意从经典方法,特别是从作为经典方法的历史研究中寻求灵感。由此,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方法逐渐从边缘向中心回归。[6]那么,国际关系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向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回归,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呢,还是仅仅因为“科学方法”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历史学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到底具有何种重要意义呢?\n我以为,历史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有利于研究者理解当前国际现象,可以为研究者树立参照系,还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和丰富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即容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也需要借助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方法来克服。一、历史学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国际现象弗朗索瓦·德·卡里埃(FrancoisdeCalliéres)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数十年的外交经验辑录成书,传诸后世。这本书就是赫赫有名的《论同君主谈判的方式》。该书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之作,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ErnestSatow)称之为“政治智慧的宝藏”,[7]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HaroldNicolson)也认为它“迄今依然是论述外交方法的最佳手稿”。[8]在该书中,卡里埃认为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可谓凤毛麟角,因为这一职业“需要过人的洞察力、无比的灵活性和敏捷的反应能力;需要敏锐的理解力和广博的知识,尤其需要准确无误和洞悉一切的洞察力(discernment)”。[9]为了获取上述素质,卡里埃强烈建议那些从事外交事业的人认真学习和研究外交史。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专家、曾任英国驻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赖斯在1922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一书中也认为,“当事实保持不变时,历史是理解事实的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向导”。[10]那么为什么历史学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的性质。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民族国家也是由单个的自然人组成的。正如狄尔泰所言,个人是社会之最终的、最有意义的单位,个人的行动构成历史。“无论社会科学家要作出什么样的概括,无论历史学家要发现什么样的趋势,对于人文科学来说,个人始终具有内在的和永恒的重要性。”[11]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国际现象的前提是自我认识。所谓的自我认识,并不只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也不只是认识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还要认识“人”之作为人的本性。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话说,“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n[12]柯林武德的上述评论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自然法学派的批评。自然法学派,尤其是启蒙运动时代的自然法学派,强调人类存在固有本性。西方思想史上的巨匠,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斯密等人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人类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前提条件的。问题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本质不同。“自然是不断再现的事物活动的舞台,在那里各种现象本身缺乏有意识的目的。”[13]自然科学的定律是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因此,根据物理学和数学定律对一块石头的下落运动加以解释,无非就是指出在给定的条件下,石头将会如何运动。但是,人类生活不同于自然界的运动,它是历史的和不可重复的,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西欧人和中东的穆斯林世界的订婚和结婚仪式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现象对我们来说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即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诸如国家、民族、婚姻、家庭或资本主义这样一些一般性概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从的法规———从刑法典到交通规则———都是约定成俗的,并且是富于变化的。只有当人们了解它们、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时候,这些法规才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此外,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伴随意识产生的记忆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因此,“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每个人的特点只是通过自身的发展才显现出来的。”[14]由于人类具有相互交流的能力,个人的记忆又会被历史的记载所扩大。特定时代的人都是传统的继承人,这些传统决定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他们如何行事,并且决定他们为何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信仰。我们是由传统铸成的,因此,对于社会历史现象所作的最恰如其分的解释往往本身就是历史的。如果我们要回答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何差异时,我们当然要研究这些国家的战略目标、地缘位置、国家组织结构等。但是,所有的解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即它必须是一种历史的说明,必须告诉我们以往的一系列事件如何构成了当下的情况。由于评价产生目的,而目的又反过来促使我们去评价为达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价值、原则和目的都受历史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对上述五国的对外战略进行历史的理解。由此可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解是基本的”。[1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论及当代史的本质特征,即欧洲的世界地位的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的崩溃、亚洲和非洲的觉醒、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热核革命等,特别强调要联系以往的历史来看待当代变化。他认为上述的所有特征都“是整个历史过程的各个部分,倘若脱离了历史的来龙去脉,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16]以认真研究历史为手段准确把握现实的思想大家,要算近代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n马基雅维里了。马基雅维里根据韦杰提乌、弗朗提诺和波里比乌斯等人遗存的文献资料,对古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和战争方式进行了仔细和深入研究。在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过程中,马基雅维里深刻把握住了战争和用兵之道的基本原则,从而写就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不朽名著《论战争艺术》(TheArtsofWar)。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研读古罗马史家们的著作,马基雅维里“理解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国家是逐步成长和扩张的,它们永无休止地卷入战争,力图扩展它们的权势和领土,并且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抵挡试图征服它们的其他国家”。[17]吉尔伯特对马基雅维里的评论恰当地说明了历史研究对理解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意义。二、历史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科,就任何科学而言,都需要研究该学科的历史。这并非出于专爱摆弄古董的癖好,而是因为学科史的研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和借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开拓者约瑟夫·熊彼特把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三卷本《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指出,历史研究至少可以使我们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收获,即“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原因在于:第一,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方法的继承与创新。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就不能充分把握与理解当前问题或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科学研究不单纯是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再以直线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纵横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换句话说,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该门学科的发展状况。所以,只对当前问题进行理论研究而不追溯其历史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第二,科学史的研究会赋予研究者源源不断的灵感。“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事实上,从学科史中获取灵感并做出成就的研究者不在少数。根据恩斯特·马赫所著的《力学发展史》所载,爱因斯坦就是从一本力学史的书上获得“相对论”灵感的。最后,“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是它能把人类思维的方法告诉我们很多。”[18]历史学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的前提是史实必须准确无误。如果史实不准确,那么由历史事实擦出的灵感火花就是苍白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对于历史“事实”\n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是历史虚无派,他们认为不存在历史事实,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主观产物,历史学家确立历史事实,而且通过解释的过程掌握历史事实。另一方则坚信历史的客观性,其代表人物有英国历史学家R·G·埃尔顿。他在《历史的实践》一文中提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比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为真实。比如,为研究生物化学而处理细胞,或者为研究重力问题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一块石头,这些都是人为的。“如果没有一种代表实验者愿望的故意的行动,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虽然所研究的事物有可能来源于自然界,但在被研究之前,它已经为达到研究目的而被改变了。”历史研究却与此不同。埃尔顿认为,尽管历史学家可以选择自己中意的课题,但他所面临的仍然是真正的事实———一种与研究无关的死的事实。“正因为历史上的事物是从前的,是不可挽回、不可改变和不可重复的,所以它的客观真实性是有保证的:它不会因任何意图而改变。”[19]“科学历史”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也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兰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对材料的钻研和对批判性解释学方法的应用,借助叙述重现过去,从而获得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科学的历史事实。对于上述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二十年危机》的作者爱德华·卡尔认为,二者均失之偏颇。他把历史学家与历史史实的关系比作人与环境的关系。人除了在儿时和晚年以外,并不完全受环境所左右,毫无条件地屈从于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人也从来不曾独立于环境之外,成为环境的绝对的主人。与此同理,“历史学家既不是他的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是那些事实的暴虐专制的主人。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如果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都知道他所从事的只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而已。”[20]依卡尔之见,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无止境的问答交谈,亦即历史学家总是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审视过去。从这个意义上看,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妥,历史不会因其年代久远而失去当代意义。所以,即便是遥远的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依然能为人们解读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提供灵感。1947年,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即提到,研读历史可以为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问题提供灵感。他说:“我很怀疑,一个至少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雅典覆灭都没有进行过重新思考的人在考虑当今一些基本的国际问题时,能否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深刻的信念。”[21]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提一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西利(JohnRobertSeeley,\n1834—1895)。在1883年,即当时欧洲正处于扩张的顶峰时,西利爵士就预见到了欧洲的衰落。他指出,美国和俄国由于其辽阔的疆域,一旦它们的潜力因“蒸汽机和电力”以及铁路网而得到充分的发挥,将使“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相形见绌,并迫使其沦为二流国家”。就是登上霸权顶峰的英国,如果不能把殖民帝国转变为“更大的不列颠”,也注定会沦为“不安全、不重要、第二流”行列的国家。[22]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见证了历史学家西利的真知灼见,也充分证实了历史能赋予历史学家见微知著的灵感!三、历史具有借鉴功能并可为 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究竟历史有无借鉴意义?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久争不决。中国古代史学家格外坚持历史的鉴今意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强调:“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23]不过,在学术界也有不少学术大师和思想家否认历史具有借鉴功能,仅把历史看成是一门艺术(arts)而非科学(science)。英国外交史大师A·J·P·泰勒称:“人们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支持自己的偏见”。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把历史看成是“杂货袋”,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出证实自己观点的“经验”。[24]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也否认历史的借鉴功能,他说:“经验和历史昭示我们,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的法则行事。⋯⋯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25]笔者认为,历史研究的借鉴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仔细阅读路德维希·德里奥的颇具启发性的著作《不稳定的平衡》、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和威廉·兰格的《欧洲的联盟与同盟》,[26]我们就不能不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浮想联翩。对于这种现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n杰维斯从认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的信息的解读。如果认为历史仅仅起到加强原有认识的作用,那么,具有不同认识的人就不会从历史事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历史上发生的国际事件为政治家的决策提供了一系列参照标准,使他能从中发现规律和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决策者解读他所面对的复杂国际形势。[27]杰维斯的解释绝非虚言。1919年的巴黎和会召开前,法国外交部就曾把路易十四时代的首相黎塞留下达给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谈判的法国代表的训令搜集整理出来,发给与会的法国代表团的每一位代表,供其参考。历史案例研究的借鉴功能特别表现在危机决策方面。当危机爆发时,决策者如果能了解历史上同类危机爆发时决策者如何判断自己的战略利益以及各类国家的官僚机构如何运作,就能很好地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国际关系的科学学派也把危机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他们多采用定量方法,并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模拟。不过,由于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涉及的变量太多,根本不可能进行准确和有效控制。[28]所以,用科学方法研究出的结果难免漏洞百出。与科学方法相比,基于叙述的外交史的方法则可靠得多,因为内阁的会议记录和其他的政府正式文件为重构政府的决策过程提供了可靠依据。[29]不过,从借鉴的角度来说,历史细节太过复杂,决策者不太可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研究和分析迫在眉睫的现实国际问题与历史上出现的相似问题的异同。[30]由于理论具有高度的简约性,如果能用理论正确地概括某种历史现象,就能对决策者作出决策起指导作用。例如决策者只要理解修昔底德总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即“斯巴达对雅典势力增长的恐惧”,在决策时就会或多或少地受这一理论的指导,虽然他可能不会去逐字逐句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此,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历史学家务必要把经验材料上升到理论高度。当然,对于历史学家的这一追求,国际关系理论家深表怀疑。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普遍对国际关系史研究存有偏见,认为历史编纂学太缺乏理论取向和普遍性。[31]他们还认为,历史学家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追求的是叙述性解释而非理论性解释,在方法论上重视对特定事件叙述的精确性和描述的完整性。[32]这实在是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历史学家和历史功能的误解!确切地说,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国际关系史的沉淀与升华。正如熊彼特把经济学的内容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那样,[33]国际关系也是国际关系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理论要保证自身的可靠性,就必须从历史中寻求依据,否则只能是错误百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贸易迅猛发展。相互依存论者便依此断言,国家间传统上彼此对立的利益被贸易关系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大国间几乎不可能再爆发战争。但戴尔·卡普兰的历史个案研究却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的贸易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这并未能够阻止欧洲国家大打出手。”[34]由此可见,一种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建立在缜密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推论的基础之上。四、历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及其克服历史是典型的经验学科。就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卷首所言,“一切知识自经验始。”\n国际关系学科也不例外,要认识和理解时下的国际关系现状,就必须研究国际关系史。没有国际关系史研究,任何国际关系研究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作为经验学科的历史,如同其他任何一门经验学科一样,存在着普遍的和自身特殊的局限性。第一,如果研究只停留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就不能真正认识普遍性和必然性。当然,我们不否认一般的经验学科里包含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是空泛的、不确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偶然的和外在的。不能真正认识普遍性和必然性,也就不能满足人类固有的理性要求。以布鲁斯·拉塞特对民主和平问题的研究为例。拉塞特把冷战期间国家间关系的史实进行配对,其中双方都是民主国家的共3878对,一方是非民主国家或双方均为非民主国家的共25203对。在双方都是民主国家的3878对关系中,相互间没有发生争端的为3864对,相互争端诉诸武力威胁的有2对,达到显示武力的有4对,达到诉诸武力的为8对,而争端升级到公认的战争程度的则为零。而一方或双方均为非民主国家的关系配对中,达到威胁使用武力的有39对,达到显示武力的有116对,达到使用武力的为513对,达到战争级别的有32对。[35]拉塞特就是以这种大跨度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来论证“民主和平论”\n成立。乍看起来,拉塞特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他的这一研究拘泥于冷战期间民主国家间没有打过仗这一现象,没有看到现象形成背后的各种特殊原因,如利益集团的影响、统治者的利益估算、甚至一些极为偶然的事件都可能使所谓民主国家间的争端以和平方式解决。所以,拉塞特的论证难以让人信服。第二,一般而言,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或情节进行描述、解释,只附带进行理论概括,并且在做理论概括时受到明确的时空观念的限制。例如当我们要证明某些要素与通货膨胀有关时,经济学是通过对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概括来探讨通货膨胀问题;以经济史方法研究同一个主题时,它所注重的则是通货膨胀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国家中的发展,通常不做大篇幅的理论阐述。就像经济史缺乏经济理论的简约性那样,国际关系史也缺乏理论上的简约性。理论犹如大厦,历史则是建筑大厦的材料。通常情况下,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一座美丽的房子,而不是一堆杂乱的砖头和钢材。况且,历史学家如果不了解事件的典型特征,不了解连贯事件的一般规律,也不可能作出连贯的、有意义的叙述。例如,历史上一位将军因为害怕而落荒而逃,一支军队因一条特别泥泞的道路延误了撤退,历史学家不需要求助于心理学家也能知道恐惧的作用,无需求助于物理学家就能了解陷入泥淖的后果。但是,只拥有这种基于常识的知识往往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更加详尽、更加精确的关于复杂事实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粗疏的观察所能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知识。历史研究的上述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把国际关系史研究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以及其他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有诸多好处。历史学家的长处,即对国际现象来龙去脉的准确把握能帮助使用科学方法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进行长期预测,也就是历史学家能帮助国际关系理论家准确定位他们规律性理论概括所能应用的条件和环境。历史分析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根据实证证据为衡量各种观点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历史事实能成为纯粹抽象分析过程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能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受益,把理论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尤其应指出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家能帮助历史学家看到事物发展的模式,否则,历史学家仅仅只能看到一些独立的事件。就如加迪斯所说,如果没有理论,“一切都只能是瞎猜”。[36]此外,理论还有助于历史学家摆脱对实证主义的过分迷信,给他们提供更为广泛的解释模型和范式,使他们对自己方法论和认识论中的先决条件进行更为认真的思考,有助于他们审视重复出现的模式和独立存在的类比。总的来说,理论会帮助历史学家获得更广泛、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的概要性判断。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来指导宏观历史研究的范例,当属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肯尼迪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都包含有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分析。对于国际政治时空关系的准确把握,以及把国别政治和区域政治恰到好处地纳入到全球地理—政治大框架内,使肯尼迪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杰出战略分析家。可见,在历史学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许多值得彼此借鉴的东西,所以硬说哪一种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更为重要是没有意义的。“从科学的标准来看,能完整描述事件之间关系的并不就是好的历史,因为任何历史都受理论性假定和模式的推动,更多的理论化能使那些模式更加明晰,分析起来有说服力。同样,能缜密地阐述逻辑关系的理论结构并不就是好的理论,因为好的理论必须在复杂的条件下能被经验证实,对历史背景的更多关注有助于揭示理论的时空(以及分析)的适用范围。”[37]因此,只有真正借鉴其他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回归到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位置。注释:1.HedleyBull,“InternationalTheory:TheCaseforaClassicalApproach”,inKlausKnorrandJamesN.Rosenau,eds.,ContendingApproachestoInternationalPolitics,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9,pp.20—22.2.黑伦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代表作是:A.H.L.Heeren,AManualoftheHistoryofthePoliticalSystemofEuropeandItsColonies:FromItsFormationattheCloseoftheFifteenthCenturytoItsRe2establishmentupontheFallofNapoleon,London:H.G.Bohn,1846;\n兰克相关的代表作是其极其出名的短文《论列强》:LeopoldvonRanke,“OnGreatPowers”,inTheTheoryandPracticeofHistory,editedwithanintroductionbyGeorgG.IggersandKonradvonMoltke,Indianapolis,TheBobbs2MerrillCompany,Inc.,1973。3.参见RichardB.Finnega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DisputedSearchforMethod”,TheReviewofPolitics,Vol.34,No.1,Jan.,1972。4.参见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JohnL.Gaddi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EndoftheColdWar”,inSeanM.Lynn2Jones,ed.,TheColdWarandAfter:ProspectforPeace,Cambridge:TheMITPress,1994。5.预测到冷战可能以和平方式结束的学者是约翰·加迪斯。参见:JohnL.Gaddis,“HowtheColdWarMightEnd”,Atlantic,May1990。在这篇文章中,加迪斯竟然准确预测到了冷战结束的方式,即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耗尽国力而垮台,苏联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6.这种回归表现在一些国际关系领域的著名学者呼吁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如PaulW.Schroeder,“QuantitativeStudiesintheBalanceofPower:AnHistorianReaction”,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21,No.1,March1977;JohnL.Gaddis,“ExpandingtheDataBase:Historians,PoliticalScientists,andtheEnrichmentofSecurityStud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2,No.1,Summer1987;PaulW.Schroeder,“HistoricalRealityvs.Neo2re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Summer1994;IanS.Lustick,“History,Historiography,and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0,No.3,September1996;ColinElmanandMiriamFendiusElman,“Correspondence:Historyvs.Neo2realism:ASecondLook”,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B.K.Gill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ProcessesofWorldHistory:ThreeApproaches”,inHughC.Dyer,ed.,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Art,NewYork:St.MartinÄsPress,1989。1997年夏季卷的《国际安全》杂志约请了美国一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撰文讨论历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论及历史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如: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谢华:《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理论探索》2003年第3期等。7.ErnestSatow,AGuidetoDiplomaticPractice,2vols,London:Longmans,Green,1917,p.85.8.HaroldNicolson,TheEvolutionofDiplomacy,NewYork:Collier,1962,p.85.9.FrancoisdeCalliéres,OntheMannerofNegotiatingwithPrinces,NotreDame: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63,p.3.10.JamsBryce,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1922,pp.3—4.\n转引自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11.〔英〕H·P·里克曼:《狄尔泰》,殷晓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1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页。13.〔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14.同上书,第3页。15.〔英〕汉迪·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载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198页。1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17.参见FelexGilbert,“Machiavelli:TheRenaissanceoftheArtofWar”,inPeterParet,ed.,MakersofModernStrategy:FromMachiavellitotheNuclearAg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chapter1。1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19页。19.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学家的选择与偏见》,载于《大学活叶文库》(第6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20.〔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载于《大学活叶文库》(第6辑),第3—4页。21.MartinWight,PowerPolitics,London:LeicesterUniversityPress,1978,p.25.22.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94页。23.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四卷),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1页。24.〔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2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26.LudwigDehio,ThePrecariousBalance:ThePoliticsofPowerinEurope,1494—1945,London:Chatto&Windus,1963;A.J.P.Taylor,TheStruggleforMasteryinEurope,1848—1918,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54;WilliamL.Langer,EuropeanAlliancesand\nAlignments,1871—1890,NewYork:AlfredA.Knopf,Inc.,1966.27.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217页。28.国际关系领域的变量之多,可以参见美国学者布里安·黑利和阿瑟·斯泰恩的一篇研究均势的论文,他们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50个基本图表和110个半圆的基础上,其中还包括30个双边组合(dyads)和80个三边组合(triads)。参见BrianHealyandArthurStein,“TheBalanceofPowerinInternationalHistory:TheoryandReality”,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17,March1973,p.56。29.AlanSked,“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HistorianÄsView”,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Art,NewYork:St.MartinÄsPress,1989,p.90.30.ErnestMay,“Lessons”ofthePast:TheUseandMisuseofHistoryinAmericanForeignPolic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3,p.xi.31.JackS.Levy,“TooImportancetoLeavetotheOther:HistoryandPoliticalSciencein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2,No.1,Summer1997.32.ColinElmanandMiriamFendiusElman,“DiplomaticHist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RespectingDifferenceandCrossingBoundar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2,No.1,Summer1997,p.7.3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页。34.DaleC.Copeland,“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War:ATheoryofTradeExpectations”,inMichaelBrown,ed.,TheoriesofWar,andPeace,Cambridge:TheMITPress,1998,p.465.35.BruceRussett,“TheFactofDemocraticPeace”,inMichaelBrown,ed.,DebatingtheDemocraticPeace,p.80.36.JohnL.Gaddi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EndoftheColdWar”,inSeanM.Lynn2JonesandStevenE.Miller,eds.,TheColdWarandAfter:ProspectsforPeace,Cambridge:TheMITPress,1993,p.325.37.JackS.Levy,“TooImportancetoLeavetotheOther:HistoryandPoliticalSciencein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p.32—33.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