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8 发布 |
- 37.5 KB |
- 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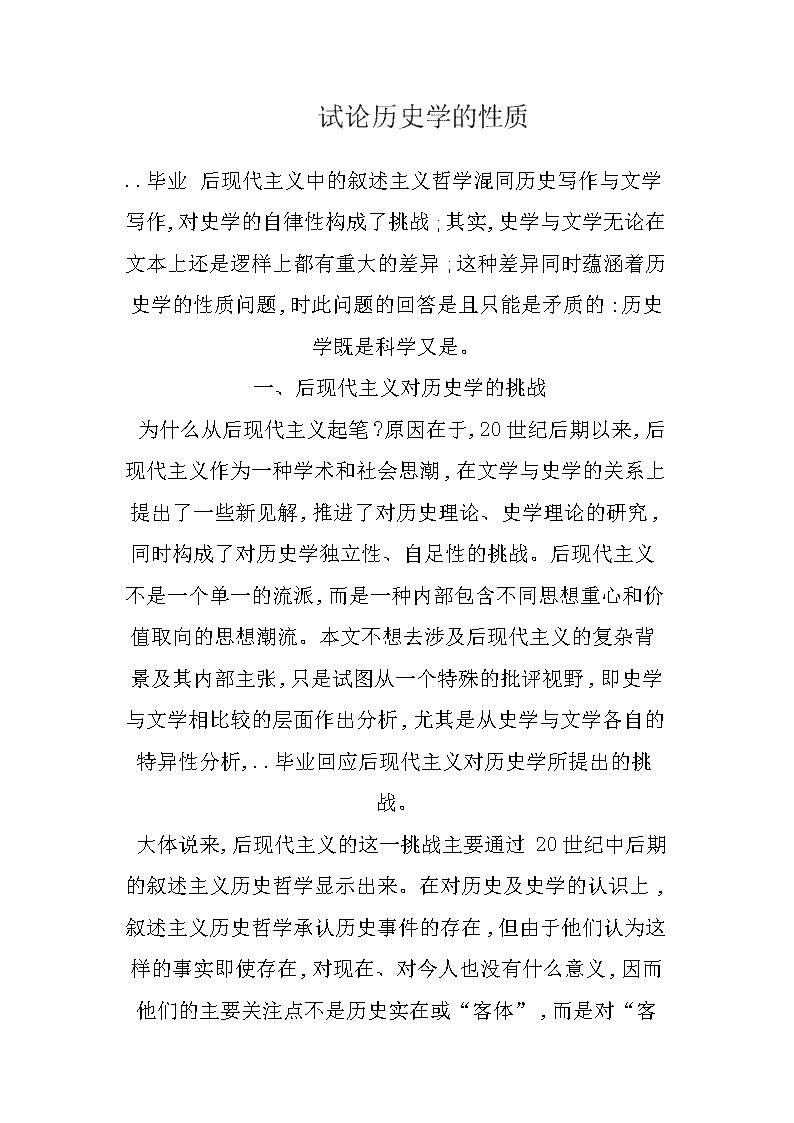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试论历史学的性质
试论历史学的性质..毕业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毕业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n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n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着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着作。那么,以历史为对象的史学与文学是何种关系呢?\n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n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n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n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三、史学的双孟品格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n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n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