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8 发布 |
- 37.5 KB |
- 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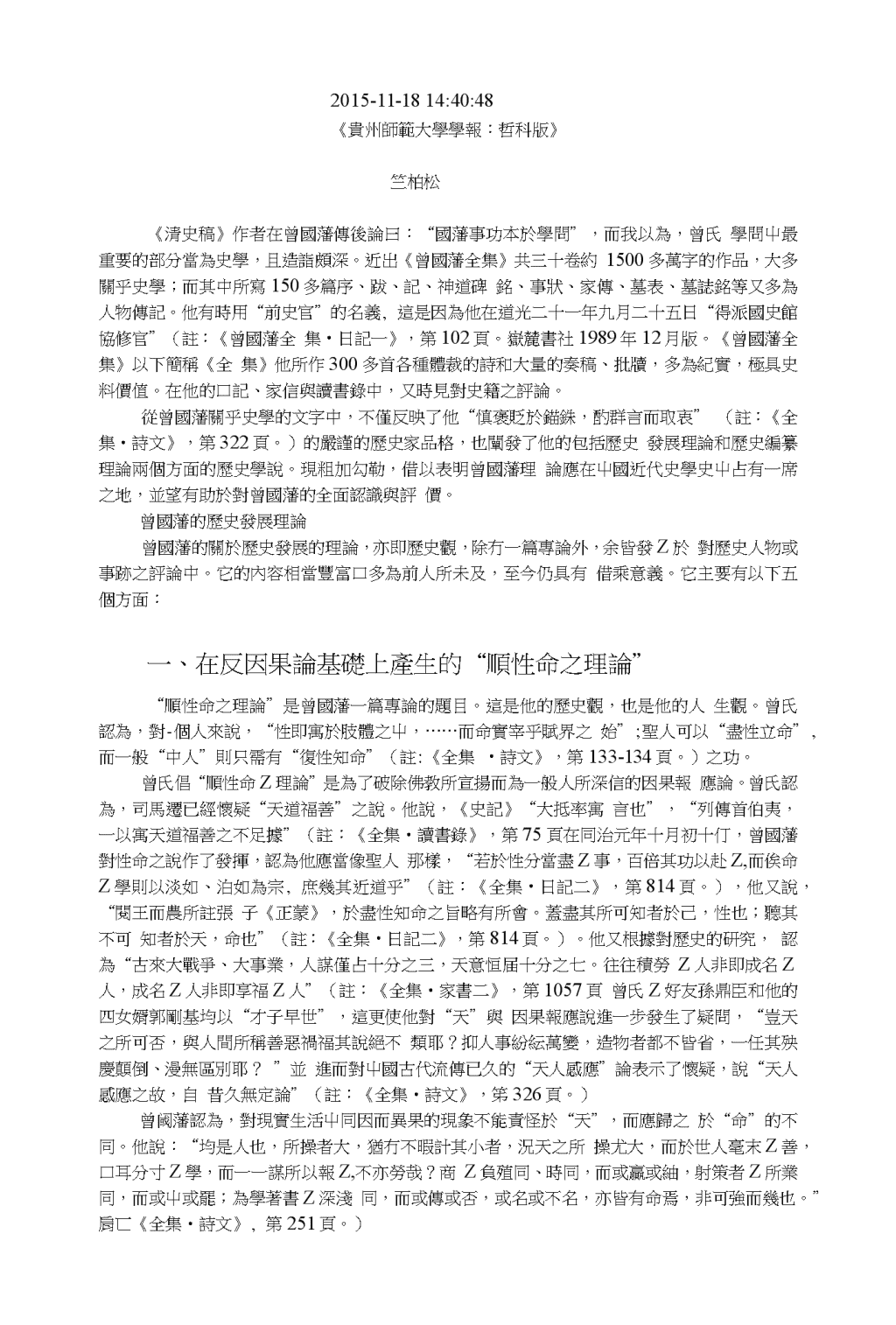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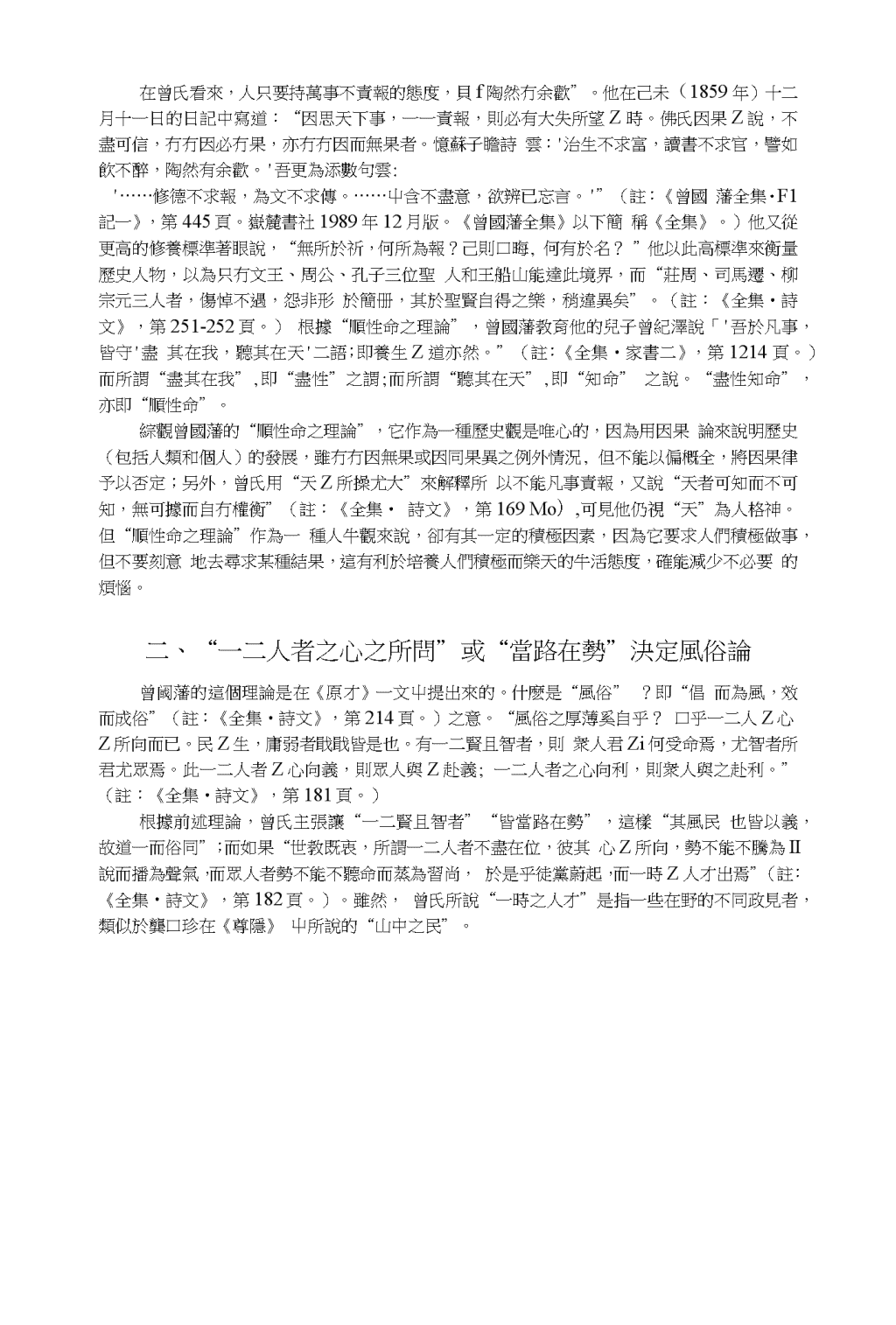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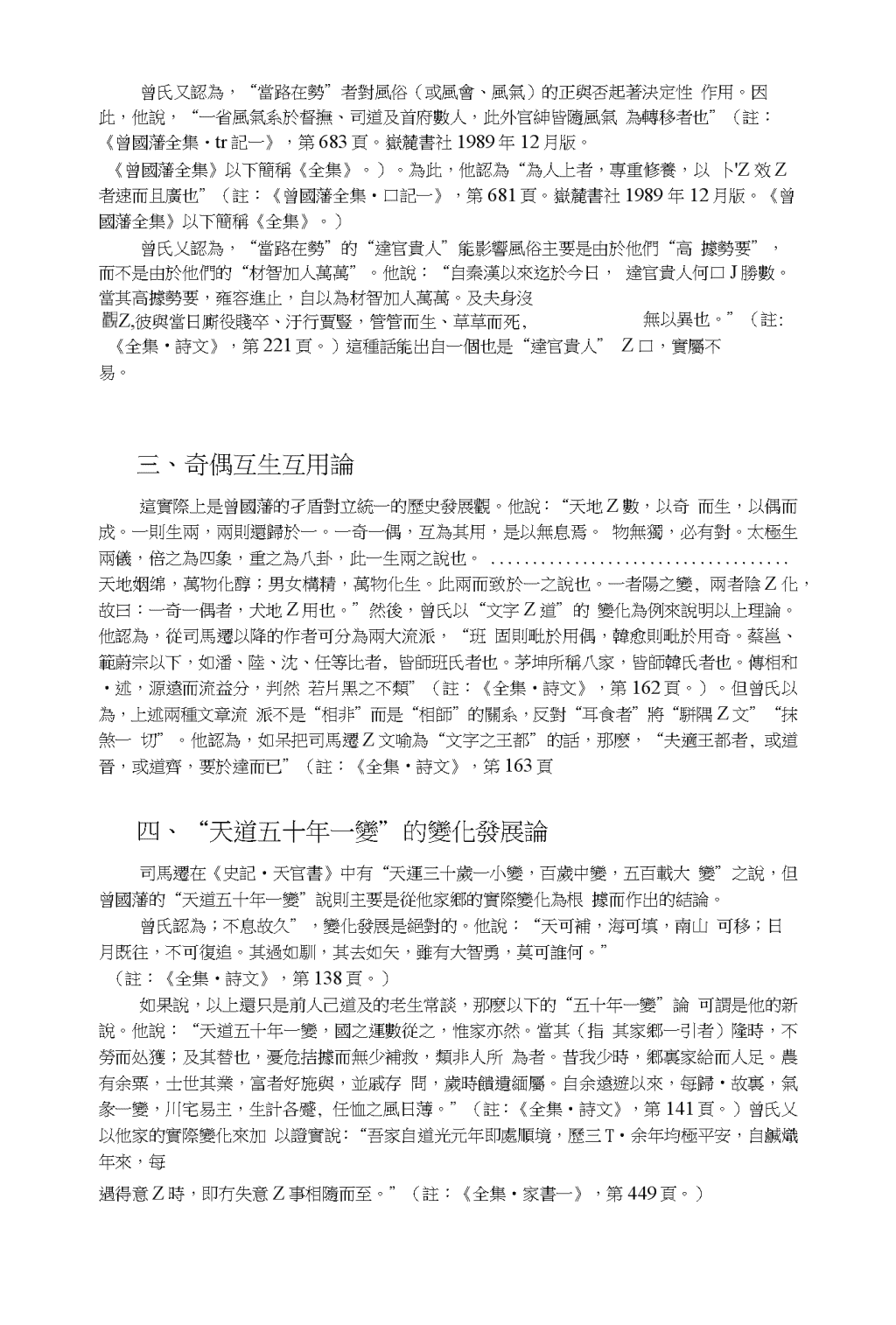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曾国藩历史学说研究
2015-11-1814:40:48《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哲科版》竺柏松《清史稿》作者在曾國藩傳後論曰:“國藩事功本於學問”,而我以為,曾氏學問屮最重要的部分當為史學,且造詣頗深。近出《曾國藩全集》共三十卷約1500多萬字的作品,大多關乎史學;而其中所寫150多篇序、跋、記、神道碑銘、事狀、家傳、墓表、墓誌銘等又多為人物傳記。他有時用“前史官”的名義,這是因為他在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得派國史館協修官”(註:《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102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他所作300多首各種體裁的詩和大量的奏稿、批牘,多為紀實,極具史料價值。在他的口記、家信與讀書錄中,又時見對史籍之評論。從曾國藩關乎史學的文字中,不僅反映了他“慎褒貶於錨銖,酌群言而取衷”(註:《全集•詩文》,第322頁。)的嚴謹的歷史家品格,也闡發了他的包括歷史發展理論和歷史編纂理論兩個方面的歷史學說。現粗加勾勒,借以表明曾國藩理論應在屮國近代史學史屮占有一席之地,並望有助於對曾國藩的全面認識與評價。曾國藩的歷史發展理論曾國藩的關於歷史發展的理論,亦即歷史觀,除冇一篇專論外,余皆發Z於對歷史人物或事跡之評論中。它的內容相當豐富口多為前人所未及,至今仍具有借乘意義。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在反因果論基礎上產生的“順性命之理論”“順性命之理論”是曾國藩一篇專論的題目。這是他的歷史觀,也是他的人生觀。曾氏認為,對-個人來說,“性即寓於肢體之屮,……而命實宰乎賦界之始”;聖人可以“盡性立命”,而一般“中人”則只需有“復性知命”(註:《全集•詩文》,第133-134頁。)之功。曾氏倡“順性命Z理論”是為了破除佛教所宣揚而為一般人所深信的因果報應論。曾氏認為,司馬遷已經懷疑“天道福善”之說。他說,《史記》“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註:《全集•讀書錄》,第75頁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十仃,曾國藩對性命之說作了發揮,認為他應當像聖人那樣,“若於性分當盡Z事,百倍其功以赴Z,而俟命Z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註:《全集•日記二》,第814頁。),他又說,“閱王而農所註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註:《全集•日記二》,第814頁。)。他又根據對歷史的研究,認為“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届十分之七。往往積勞Z人非即成名Z人,成名Z人非即享福Z人”(註:《全集•家書二》,第1057頁曾氏Z好友孫鼎臣和他的四女婿郭剛基均以“才子早世”,這更使他對“天”與因果報應說進一步發生了疑問,“豈天之所可否,與人間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耶?抑人事紛紜萬變,造物者都不皆省,一任其殃慶顛倒、漫無區別耶?”並進而對屮國古代流傳已久的“天人感應”論表示了懷疑,說“天人感應之故,自昔久無定論”(註:《全集•詩文》,笫326頁。)曾阈藩認為,對現實生活屮同因而異果的現象不能責怪於“天”,而應歸之於“命”的不同。他說:“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冇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Z善,口耳分寸Z學,而一一謀所以報Z,不亦勞哉?商Z負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紬,射策者Z所業同,而或屮或罷;為學著書Z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肩匸《全集•詩文》,第251頁。)\n在曾氏看來,人只要持萬事不責報的態度,貝f陶然冇余歡”。他在己未(1859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因思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Z時。佛氏因果Z說,不盡可信,冇冇因必冇果,亦冇冇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雲:'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吾更為添數句雲:'……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屮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註:《曾國藩全集・F1記一》,第445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他又從更高的修養標準著眼說,“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口晦,何有於名?”他以此高標準來衡量歷史人物,以為只冇文王、周公、孔子三位聖人和王船山能達此境界,而“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非形於簡册,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註:《全集•詩文》,第251-252頁。)根據“順性命之理論”,曾國藩教育他的兒子曾紀澤說「'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Z道亦然。”(註:《全集•家書二》,第1214頁。)而所謂“盡其在我”,即“盡性”之謂;而所謂“聽其在天”,即“知命”之說。“盡性知命”,亦即“順性命”。綜觀曾國藩的“順性命之理論”,它作為一種歷史觀是唯心的,因為用因果論來說明歷史(包括人類和個人)的發展,雖冇冇因無果或因同果異之例外情況,但不能以偏概全,將因果律予以否定;另外,曾氏用“天Z所操尤大”來解釋所以不能凡事責報,又說“天者可知而不可知,無可據而自冇權衡”(註:《全集•詩文》,第169Mo),可見他仍視“天”為人格神。但“順性命之理論”作為一種人牛觀來說,卻有其一定的積極因素,因為它要求人們積極做事,但不要刻意地去尋求某種結果,這有利於培養人們積極而樂天的牛活態度,確能減少不必要的煩惱。二、“一二人者之心之所問”或“當路在勢”決定風俗論曾阈藩的這個理論是在《原才》一文屮提出來的。什麽是“風俗”?即“倡而為風,效而成俗”(註:《全集•詩文》,第214頁。)之意。“風俗之厚薄奚自乎?口乎一二人Z心Z所向而已。民Z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Zi何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Z心向義,則眾人與Z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註:《全集•詩文》,第181頁。)根據前述理論,曾氏主張讓“一二賢且智者”“皆當路在勢”,這樣“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而如果“世教既衷,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Z所向,勢不能不騰為II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Z人才出焉”(註:《全集•詩文》,第182頁。)。雖然,曾氏所說“一時之人才”是指一些在野的不同政見者,類似於龔口珍在《尊隱》屮所說的“山中之民”。\n曾氏又認為,“當路在勢”者對風俗(或風會、風氣)的正與否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他說,“一省風氣系於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氣為轉移者也”(註:《曾國藩全集・tr記一》,第683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為此,他認為“為人上者,專重修養,以卜'Z效Z者速而且廣也”(註:《曾國藩全集•口記一》,第681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曾氏乂認為,“當路在勢”的“達官貴人”能影響風俗主要是由於他們“高據勢要”,而不是由於他們的“材智加人萬萬”。他說:“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口J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Z,彼與當日廝役賤卒、汙行賈豎,管管而生、草草而死,無以異也。”(註:《全集•詩文》,第221頁。)這種話能出自一個也是“達官貴人”Z口,實屬不易。三、奇偶互生互用論這實際上是曾國藩的孑盾對立統一的歷史發展觀。他說:“天地Z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為四象,重之為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天地姻绵,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Z化,故曰:一奇一偶者,犬地Z用也。”然後,曾氏以“文字Z道”的變化為例來說明以上理論。他認為,從司馬遷以降的作者可分為兩大流派,“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範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和•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片黑之不類”(註:《全集•詩文》,第162頁。)。但曾氏以為,上述兩種文章流派不是“相非”而是“相師”的關系,反對“耳食者”將“駢隅Z文”“抹煞一切”。他認為,如呆把司馬遷Z文喻為“文字之王都”的話,那麽,“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註:《全集•詩文》,笫163頁四、“天道五十年一變”的變化發展論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有“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歲中變,五百載大變”之說,但曾國藩的“天道五十年一變”說則主要是從他家鄉的實際變化為根據而作出的結論。曾氏認為;不息故久”,變化發展是絕對的。他說:“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馴,其去如矢,雖有大智勇,莫可誰何。”(註:《全集•詩文》,第138頁。)如果說,以上還只是前人己道及的老生常談,那麽以下的“五十年一變”論可謂是他的新說。他說:“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指其家鄉一引者)隆時,不勞而处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據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為者。昔我少時,鄉裏家給而人足。農有余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並戚存問,歲時饋遺緬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裏,氣彖一變,川宅易主,生計各蹙,任恤之風日薄。”(註:《全集•詩文》,第141頁。)曾氏乂以他家的實際變化來加以證實說:“吾家自道光元年即處順境,歷三T•余年均極平安,自鹹熾年來,每遇得意Z時,即冇失意Z事相隨而至。”(註:《全集•家書一》,第449頁。)\n五、喜戚以境、動止由勢論曾氏的環境、形勢決定論最早表述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初四口致弟信中。他說:“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Z所處,求退不能。”(註:《全集•家書一》,第197頁。)這裏他捉出了“勢”對人Z束縛。鹹豐九年(1859年)五刀十四日的日記中,曾氏進一步把“勢”視作驅使人行動的最重要原因。他說:“思夫人皆為名所驅,為利所驅,而尤為勢所驅。”(註:《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386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卜禽稱《全集》。)同年8月,在參觀剛落成的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時,曾氏冇感而發道:“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Z颦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歡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在這裏提出了喜戚由境說。曾氏乂進一步認為,“豪傑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郁郁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冇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已,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了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Z內,蓋幾幾不能自克”(註:《全集•詩文》,第260頁。)。在這裏,曾氏並未把自己視作“君子人”,承認自己同樣受“境”和“勢”的影響,承認自己被圍闲在鄱陽湖時有欲投水自盡之舉動。能這樣解剖自己,也屬不易。上述環境與形勢決定論,應該說是唯物的,且頗具新意,促人深思。曾國藩的歷史編纂理論曾國藩一生中對史學確是情有獨鐘,用力甚勤。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致弟函屮,在所附寄的自立課程屮,第五項即“讀史,二十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註:《全集•家書一》,第49頁。)。在《讀書錄》中,更可知他不僅通讀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文獻通考》等,而冃都做了筆記,對史書的內容與作者時冇評論。他的歷史編纂理論就闡發於這種評論和其他有關文字之中。現介紹其主要內容如下:一、關於歷史編纂之價值或目的1•使“來者勿忘”與“使來者怵然起敬”曾氏在其所撰並手書的《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中說:“第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註:《全集•詩文》,第19頁。)在《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屮,曾氏“粗述殉難者之慘”,目的在“使來者怵然起敬”(註:《全集•詩文》,第277頁。)曾氏所作家史性質Z《大界墓表》,敘述了其祖父曾玉屏的奮鬥史,目的在“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冇眾征,無虛美雲”(註:《全集•詩文》,第328頁。)其重點亦在“無忘”。2•“俾來者有考焉”。這裏是指為以後的歷史研究提供史料。曾氏之《何君殉難碑記》記敘其好友何桂珍“行善獲禍”而“橫死”的事跡,目的在“俾來者有考焉”(註:《全集•詩文》,第331頁。)。3•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以便不斷改革進步。在《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中,曾氏坦陳楚軍水師取得所謂勝利而付出的巨大代價,從而告誡後人要“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而在“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相對制宜”,“俾日新而月盛”(註:《全集•詩文》,第267頁。)4•欲借歷史以表感慨與發泄郁憤。曾氏在讀《史記》後說:“太史(指司馬遷一引者)傳莊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讀《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為師,非自著書,則將無所托以垂於不朽。次管、晏傳,傷己不得鮑叔者為Z知己,又不得如晏了者為Z薦達。此外如子婿Z憤、屈賈Z\n枉,皆借以自鳴其郁耳。非以此為古來偉人計功簿也”(註:《全集•讀書錄》,第75頁曾氏的“歷史不是古來偉人計功簿”的說法,似是前人所未發之創見,很可能為以後梁啟超類似說法之張木。而曾氏自己所寫的傳記性作品,也可說“大抵率寓言”,也是“借以自鳴其郁”。如《何君殉難碑記》,就是對何桂珍“横死”後仍“不免身後Z余責”,甚至“赤舌燒城”、“群毀所歸”情況的抗議,並借以發泄自己受到類似遭遇的郁憤。乂如在《出昆圃先生六十壽序》中,曾氏以出昆圃“勿輕幹人”一語,借題發揮,也發泄了他對科舉制度之憤慨。他說:“今世之士,自束發受書,即以幹祿為鵠,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僥福。祿利無盡境,則幹人無窮期。卜•以此求,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註:《全集•詩文》,第328頁。)批判可謂深刻!5•欲借歷史來說明一些道理,以對後人進行教育。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註:《史記•太史公自序九)。如在《湘鄉昭忠祠記》中,曾氏即欲借“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州而戡人亂”的歷史來說明“拙且誠者Z效”,並教育今後的湘鄉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裏”(註:《全集•詩文》,第137頁。)。二、關於歷史編纂內容1・主張史書主要記載“經世大法”,以便“辨後世因革之要”,且以此作為評判以往史書之標準。他說:“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註:《全集》本將“而八書”斷於“三古”後,誤。)頗病其略;班氏《誌》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誌》(按指鄭樵《通誌》一引者)非其倫也。……杜、馬辨後世因革Z要,……”(註:《全集•詩文》,第304頁曾氏這一標準可謂高屋建範,洞中竅要,很有見地。2.主張在史書中增加並突出關於禮的內容,並以此作為評判以往史書優劣的另一標準。他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範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Z遺意。”他又說:“而秦樹澧氏(按指秦蕙山一引者)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傅於秦書之次,……以世之多故,握槊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發固已衰矣!”(註:《全集•詩文》,第250頁。)據此,《清史稿》曾傳雲,曾氏“牺補鹽課、海運、錢法、河提為六卷”。但筆者以為,此說與曾氏上述說法不合,彳以•A事實o°什麽是“禮”?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一附論中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在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從此可見,在司馬光看來,禮即名分、紀綱。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即以正名分、守名分,也就是禮作為編纂歷史的最重要的指導思想(即所謂的“義”)。但曾氏上述關於禮的論述卻與司馬光大異其趣。他認為禮的內容為“天文、地理、軍政、官制”再加上“食貨”等,這就無異更新了禮的內涵,不再像司馬光所說的那樣充滿封建禮教氣味。而更為可貴的是,他擬補《五禮通考》食負Z缺,雖未完成。仍值得稱道。3•主張在史書中對技術性內容“略著大指”即可,不能“累牘不休”。他說:“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劑之宜,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為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廢,……若遷實通方術,而借以门矜其多能,斯又淺者徒也。”(註:《全集•詩文》,第256頁。)應該說,曾氏對《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的上述批評是正確的,但因此譏司馬遷為“自矜其多能”之“淺者徒”\n,則乂未免過當。4•贊揚範曄在《後漢書》中創立《列女傳》,但主張在內容上著重寫婦女的“門內庸行,恭儉励苦”,反對“以奇特相勝”。關於寫《列女傳》Z必耍,曾氏說:“一家Z中,男職外,女職內,其輕重略相等。……則範氏立篇Z意,誠亦不為無見也。”(註:《全集•詩文》,第158頁。)曾氏之男女“輕重略相等”說,在當時應該說是一種很進步的思想。關於《列女傳》的內容,曾氏認為,“明乎至庸至難之道,不事畸異”(註:《全集•詩文》,第195頁。)應是“修史傳列女者”之訓,因為,“異則異矣,而難為式也。”(註:《全集•詩文》,第196頁。)曾氏還將上述主張付諸實踐。他先後為二十多位婦女寫了壽序、墓誌銘等,都貫穿了“至庸至難”的指導思想。特別是他寫的《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按:歐陽氏姑婦為曾國藩的嶽祖母與嶽母),在文後他以“前史官”的名義寫道:“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犬卜'Z至難,孰逾是哉!”(註:《全集•詩文》,第179頁。)三、關天對歷史人物之評價在屮國封建史學屮,以“正名分”為“義”,而將人物褒貶作為實現“義”的主要手段。在中國古代,強烈反對在史書中搞主觀褒貶並斥之為“欺人之學”的史學家只有鄭樵。而在中國近代,曾國藩反對任意褒貶歷史人物Z主張相當突岀,可說無岀其右者。曾氏在己未(1859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記中指曲“強分黑口,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分善惡,品地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存。此涼德之端也。”(註:《曾國藩全集•仃記一》,第412頁。嶽麓書社1989年12月版。《曾國藩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在《書歸震川文集後》中,曾氏又申論道:“蓋古Z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註:《全集》本將“後世”斷於“君子”前,誤。),君子恥焉。”(註:《全集•詩文》,第277頁。)曾氏認為,由於過去的史書過分地對“從古軒赫人”“銘功袜德”,人間已不存在所謂的“真史”。對此,他在七言占詩《反長歌行》中寫道:“君看從古軒赫人,一半名場誇毗子。今晨令問傾王侯,明日枯肉飽朝蟻。銘功袜徳千萬言,可信人間有真史!”(註:《全集•詩文》,第148頁。)他對過去“軒赫人”和史書的鄙薄之情溢於言表。這種言論出於也屬“軒赫人”之口,可謂難得。曾國藩應人Z求所寫壽序、墓誌銘等,客觀上要求他只能褒不能貶。但他給自己定了四條原則,避免褒“過其實”。這就是,“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巨,不明也;濫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為人友而不相勖以君子者,不忠也。”(註:《全集•詩文》,第44頁。)曾氏又指出,歷史家Z愛憎好惡會影響對歷史人物Z評價。他指出《史記》屮因受影響評價者:“壺遂、III仁皆與子長深交,故敘梁趙諸臣多凝切。”(註:《全集•讀書錄》,第83頁。)乂說:“平津(按指公孫弘一引者)亦賢相,而太史公腿非刺之,蓋子長褊衷於汲黯、董仲舒。”(註:《全集•讀書錄》,第84頁。)而因惡影響評價者,在《史記》中是:“子長最惡暴秦,故謂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實則兩人Z傾險亦相等耳,特秦挾最勝Z勢,故張儀尤為得計。”(註:《全集•讀書錄》,第76頁。)曾氏對司馬遷Z上述評論,應該說是中肯的。\n四、關於史文寫作關於史文寫作,曾氏自以《史記》為圭臬,並從中歸納出了兩條帶普遍性的原則。一是史文宜講剪裁,耍敘次分明。他從讀《南越尉陀列傳》中得出了“記事Z文,宜講剪裁之法”(註:《全集•讀書錄》,第84頁。)的結論。二是史文應“潔”潔”似指簡練之意。曾氏在讀《蕭相國世家》後寫道「蕭相之功,只從獵狗及鄂君兩段指點,其余卻皆從要緊處著筆。實事當有數I•百案,概不鋪寫,文之所以高潔也。後人為之,當累數萬言不能休矣。”(註:《全集•讀書錄》,第73頁。)又在讀《朝鮮列傳》後與道:“事緒繁多,敘次明晰,柳了厚所稱太史Z潔也。”(註:《全集•讀書錄》,第85頁。)曾氏反對“造為瑰瑋奇麗之辭”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的史文。他說:“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為瑰瑋奇麗之辭,仿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為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冇若附贅懸疣,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跡,動稱卓絕,若合占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Z畫師寫真,衆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所圖Z人同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Z交,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之矣。”(註:《全集•詩文》,笫136、322-323頁。)曾氏此論,至今仍能發人深省。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