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8 发布 |
- 37.5 KB |
- 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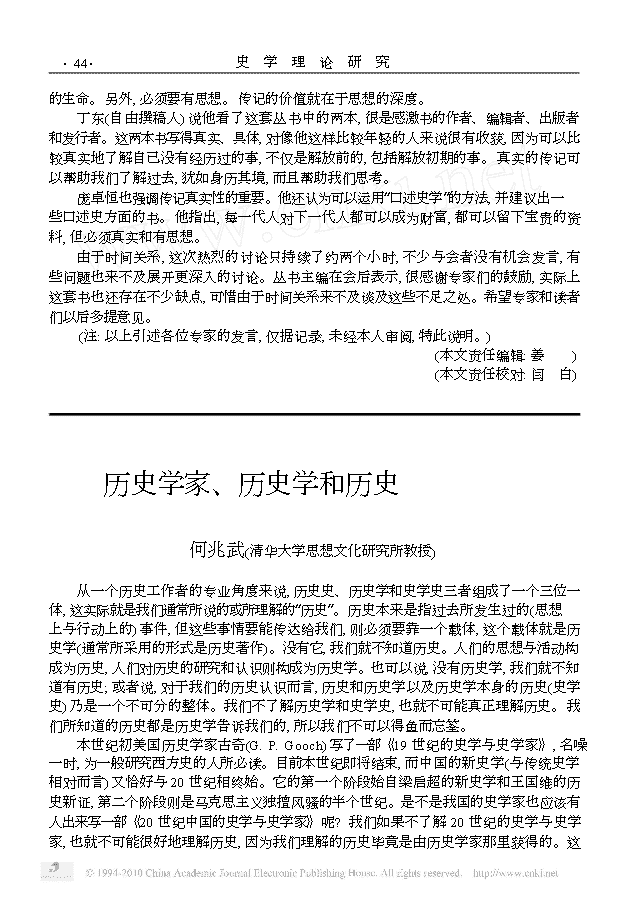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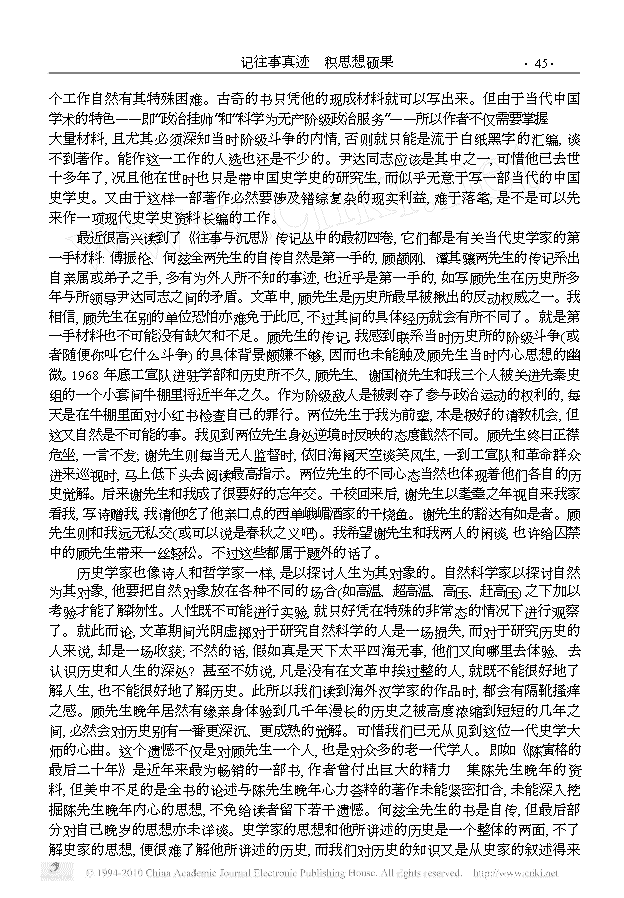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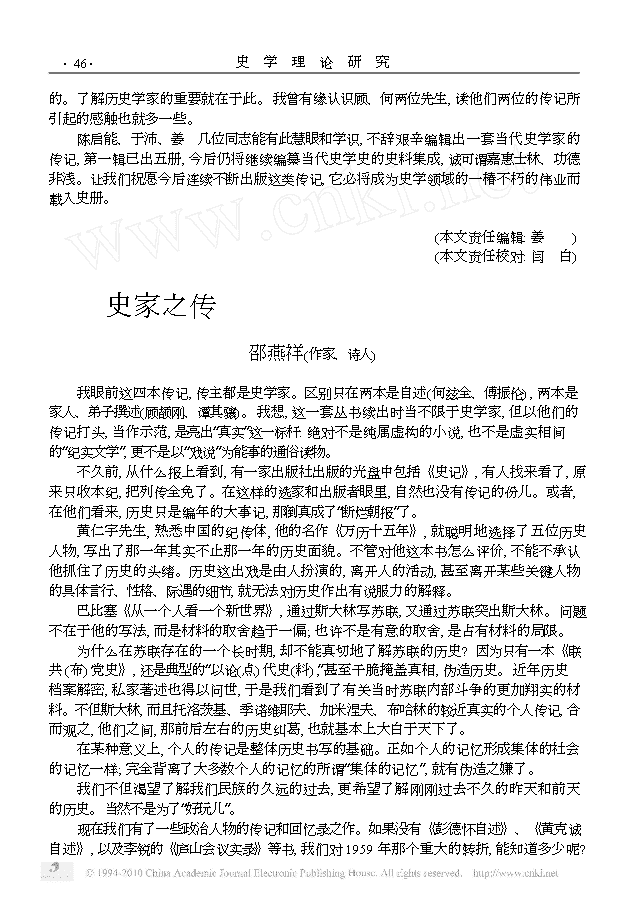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历史学家_历史学和历史
·44·史 学 理 论 研 究的生命。另外,必须要有思想。传记的价值就在于思想的深度。丁东(自由撰稿人)说他看了这套丛书中的两本,很是感激书的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和发行者。这两本书写得真实、具体,对像他这样比较年轻的人来说很有收获,因为可以比较真实地了解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不仅是解放前的,包括解放初期的事。真实的传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犹如身历其境,而且帮助我们思考。庞卓恒也强调传记真实性的重要。他还认为可以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并建议出一些口述史方面的书。他指出,每一代人对下一代人都可以成为财富,都可以留下宝贵的资料,但必须真实和有思想。由于时间关系,这次热烈的讨论只持续了约两个小时,不少与会者没有机会发言,有些问题也来不及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丛书主编在会后表示,很感谢专家们的鼓励,实际上这套书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可惜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谈及这些不足之处。希望专家和读者们以后多提意见。(注:以上引述各位专家的发言,仅据记录,未经本人审阅,特此说明。)(本文责任编辑:姜 )(本文责任校对:闫 白) 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何兆武(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从一个历史工作者的专业角度来说,历史史、历史学和史学史三者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这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或所理解的“历史”。历史本来是指过去所发生过的(思想上与行动上的)事件,但这些事情要能传达给我们,则必须要靠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历史学(通常所采用的形式是历史著作)。没有它,我们就不知道历史。人们的思想与活动构成为历史,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则构成为历史学。也可以说,没有历史学,我们就不知道有历史;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历史认识而言,历史和历史学以及历史学本身的历史(史学史)乃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我们不了解历史学和史学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得鱼而忘筌。本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古奇(G.P.Gooch)写了一部《19世纪的史学与史学家》,名噪一时,为一般研究西方史的人所必读。目前本世纪即将结束,而中国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对而言)又恰好与20世纪相终始。它的第一个阶段始自梁启超的新史学和王国维的历史新证,第二个阶段则是马克思主义独擅风骚的半个世纪。是不是我国的史学家也应该有人出来写一部《20世纪中国的史学与史学家》呢?我们如果不了解20世纪的史学与史学家,也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历史,因为我们理解的历史毕竟是由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这\n记往事真迹 积思想硕果·45·个工作自然有其特殊困难。古奇的书只凭他的现成材料就可以写出来。但由于当代中国学术的特色——即“政治挂帅”和“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作者不仅需要掌握大量材料,且尤其必须深知当时阶级斗争的内情,否则就只能是流于白纸黑字的汇编,谈不到著作。能作这一工作的人选也还是不少的。尹达同志应该是其中之一,可惜他已去世十多年了,况且他在世时也只是带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生,而似乎无意于写一部当代的中国史学史。又由于这样一部著作必然要涉及错综复杂的现实利益,难于落笔,是不是可以先来作一项现代史学史资料长编的工作。最近很高兴读到了《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中的最初四卷,它们都是有关当代史学家的第一手材料:傅振伦、何兹全两先生的自传自然是第一手的,顾颉刚、谭其骧两先生的传记系出自亲属或弟子之手,多有为外人所不知的事迹,也近乎是第一手的,如写顾先生在历史所多年与所领导尹达同志之间的矛盾。文革中,顾先生是历史所最早被揪出的反动权威之一。我相信,顾先生在别的单位恐怕亦难免于此厄,不过其间的具体经历就会有所不同了。就是第一手材料也不可能没有缺欠和不足。顾先生的传记,我感到联系当时历史所的阶级斗争(或者随便你叫它什么斗争)的具体背景颇嫌不够,因而也未能触及顾先生当时内心思想的幽微。1968年底工宣队进驻学部和历史所不久,顾先生、谢国桢先生和我三个人被关进先秦史组的一个小套间牛棚里将近半年之久。作为阶级敌人是被剥夺了参与政治运动的权利的,每天是在牛棚里面对小红书检查自己的罪行。两位先生于我为前辈,本是极好的请教机会,但这又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我见到两位先生身处逆境时反映的态度截然不同。顾先生终日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谢先生则每当无人监督时,依旧海阔天空谈笑风生,一到工宣队和革命群众进来巡视时,马上低下头去阅读最高指示。两位先生的不同心态当然也体现着他们各自的历史觉解。后来谢先生和我成了很要好的忘年交。干校回来后,谢先生以耄耋之年视自来我家看我,写诗赠我,我请他吃了他亲口点的西单峨嵋酒家的干烧鱼。谢先生的豁达有如是者。顾先生则和我远无私交(或可以说是春秋之义吧)。我希望谢先生和我两人的闲谈,也许给囚禁中的顾先生带来一丝轻松。不过这些都属于题外的话了。历史学家也像诗人和哲学家一样,是以探讨人生为其对象的。自然科学家以探讨自然为其对象,他要把自然对象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如高温、超高温、高压、赶高压)之下加以考验才能了解物性。人性既不可能进行实验,就只好凭在特殊的非常态的情况下进行观察了。就此而论,文革期间光阴虚掷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是一场损失,而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却是一场收获;不然的话,假如真是天下太平四海无事,他们又向哪里去体验、去认识历史和人生的深处?甚至不妨说,凡是没有在文革中挨过整的人,就既不能很好地了解人生,也不能很好地了解历史。此所以我们读到海外汉学家的作品时,都会有隔靴搔痒之感。顾先生晚年居然有缘亲身体验到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之被高度浓缩到短短的几年之间,必然会对历史别有一番更深沉、更成熟的觉解。可惜我们已无从见到这位一代史学大师的心曲。这个遗憾不仅是对顾先生一个人,也是对众多的老一代学人。即如《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是近年来最为畅销的一部书,作者曾付出巨大的精力 集陈先生晚年的资料,但美中不足的是全书的论述与陈先生晚年心力荟粹的著作未能紧密扣合,未能深入挖掘陈先生晚年内心的思想,不免给读者留下若干遗憾。何兹全先生的书是自传,但最后部分对自己晚岁的思想亦未详谈。史学家的思想和他所讲述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的两面,不了解史家的思想,便很难了解他所讲述的历史,而我们对历史的知识又是从史家的叙述得来\n·46·史 学 理 论 研 究的。了解历史学家的重要就在于此。我曾有缘认识顾、何两位先生,读他们两位的传记所引起的感触也就多一些。陈启能、于沛、姜 几位同志能有此慧眼和学识,不辞艰辛编辑出一套当代史学家的传记,第一辑已出五册,今后仍将继续编纂当代史学史的史料集成,诚可谓嘉惠士林、功德非浅。让我们祝愿今后连续不断出版这类传记,它必将成为史学领域的一椿不朽的伟业而载入史册。(本文责任编辑:姜 )(本文责任校对:闫 白) 史家之传邵燕祥(作家、诗人)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作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更不是以“戏说”为能事的通俗读物。不久前,从什么报上看到,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光盘中包括《史记》,有人找来看了,原来只收本纪,把列传全免了。在这样的选家和出版者眼里,自然也没有传记的份儿。或者,在他们看来,历史只是编年的大事记,那倒真成了“断烂朝报”了。黄仁宇先生,熟悉中国的纪传体,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就聪明地选择了五位历史人物,写出了那一年其实不止那一年的历史面貌。不管对他这本书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他抓住了历史的头绪。历史这出戏是由人扮演的,离开人的活动,甚至离开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行、性格、际遇的细节,就无法对历史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通过斯大林写苏联,又通过苏联突出斯大林。问题不在于他的写法,而是材料的取舍趋于一偏;也许不是有意的取舍,是占有材料的局限。为什么在苏联存在的一个长时期,却不能真切地了解苏联的历史?因为只有一本《联共(布)党史》,还是典型的“以论(点)代史(料)”,甚至干脆掩盖真相,伪造历史。近年历史档案解密,私家著述也得以问世,于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当时苏联内部斗争的更加翔实的材料。不但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较近真实的个人传记,合而观之,他们之间,那前后左右的历史纠葛,也就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了。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传记是整体历史书写的基础。正如个人的记忆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一样;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个人的记忆的所谓“集体的记忆”,就有伪造之嫌了。我们不但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久远的过去,更希望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儿”。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作。如果没有《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我们对1959年那个重大的转折,能知道多少呢?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