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8 发布 |
- 37.5 KB |
- 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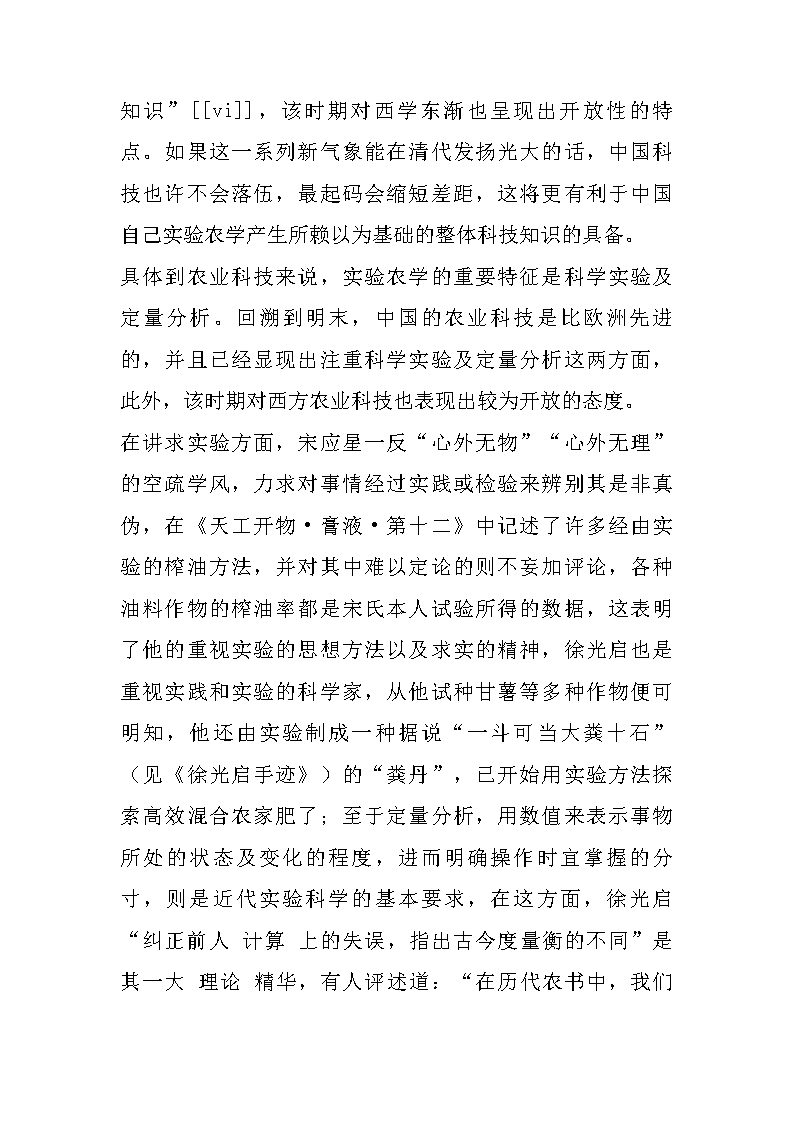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甲午战争前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观念约束
甲午战争前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观念约束[摘要]:甲午战争前,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化受到统治者和“士”的观念约束。具体地,对统治者来说,经世致用科技目的观的政治功利性特征、“华夏中心主义”对西方科技的排斥作用、“中体西用”观对物质层面的西方科技的偏重;对“士”来说,重文轻理观念、实用主义的科技目的观,这些都约束了中国实验农学的产生。[关键词]传统农学;实验农学;观念约束一、问题的提出法国的谢和耐认为,中国的农业在18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从中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来看,中国的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之前最科学和最发达者[[i]]。而西方农学,正如李比希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在那时“农业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田地肥瘦的道理,也不知道在作物的影响\n下,肥力减退的原因。除了阳光、露水、雨水的作用以外,农民对作物所必需的其他条件,几乎毫无所知。至于大家议论的土壤,也只是为作物提供生长的处所。”[[ii]],但西方实验农学一出现,便将中国传统农学抛在了后面。其实,西方的农业技术也有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过程,“无论中西,所有于十六世纪前农事新技术之改革均非由学者计划实验所获得,却多为躬耕之农夫实地耕作之辛苦经验。旧时农书确曾记述农业之改进,然此类记述均为没没无闻之农夫经验累积或偶有灵感之结果。技术之改进全非来自上层人士,而均出自基层农夫者。”[[iii]],在十七世纪时,中西农书“重点虽各不同,但却具有相似之水准,此一局势到十八世纪时始全部改观。此后,中国之农书一直沿用同一传统发展,丝毫未受欧洲学术之影响”,但是,至十八世纪“欧洲农业也由传统技术转而成为一门实验科学。”[[iv]]。对中国来说,其实早在明末,中国科技总体上出现了又一个高峰,此时出现了众多的优秀科学专著,难能可贵的是出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新气象,陈美东先生对明末科学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显现的一些特点“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v]]另外,正如袁翰青先生对徐光启所做的评价:“\n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vi]],该时期对西学东渐也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如果这一系列新气象能在清代发扬光大的话,中国科技也许不会落伍,最起码会缩短差距,这将更有利于中国自己实验农学产生所赖以为基础的整体科技知识的具备。具体到农业科技来说,实验农学的重要特征是科学实验及定量分析。回溯到明末,中国的农业科技是比欧洲先进的,并且已经显现出注重科学实验及定量分析这两方面,此外,该时期对西方农业科技也表现出较为开放的态度。在讲求实验方面,宋应星一反“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空疏学风,力求对事情经过实践或检验来辨别其是非真伪,在《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中记述了许多经由实验的榨油方法,并对其中难以定论的则不妄加评论,各种油料作物的榨油率都是宋氏本人试验所得的数据,这表明了他的重视实验的思想方法以及求实的精神,徐光启也是重视实践和实验的科学家,从他试种甘薯等多种作物便可明知,他还由实验制成一种据说“一斗可当大粪十石”(见《徐光启手迹》)的“粪丹”,已开始用实验方法探索高效混合农家肥了;至于定量分析,用数值来表示事物所处的状态及变化的程度,进而明确操作时宜掌握的分寸,则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基本要求,在这方面,徐光启“纠正前人计算上的失误,指出古今度量衡的不同”是其一大理论精华,有人评述道:“\n在历代农书中,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像徐光启这样严格地注意数字表达的准确性”[[vii]],徐光启注意到了作定量分析的重要,他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故也,此须接续讲求”[[viii]]他还重视智能训练的几何学,这从他重视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可看出,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ix]],《天工开物》也注重数量表达,“《开物》的定量表达比之《农政全书》毫不逊色”,宋应星曾对水稻栽培知识力求以数值来表示其量化程度,《天工开物》的对稻田本田比、秧龄和早穗、再生秧技术、早晚稻需水量、供水和结实关系等是其他几大农书所不具备的[[x]],这些都涉及到数量表达;在对待西方农业科技方面,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不是对其简单排斥,而是通过翻译吸收(如徐光启把《泰西水法》收录在《农政全书》之中)力求达到“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n[[xi]]的目的,与清前期统治者对西学的态度相比,可以显示出其高瞻远瞩。可以说,到明末时期,中国的传统农学已踏上了实验农学的门槛,清代前中期是中国传统农学有可能向实验农学转化的关键时期,可惜的是没有实现这一突破。在清前中期的一二百年时间内,实验农学始终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化没有实现。直到19世纪90年代,甲午海战的失败令统治者、士大夫、官僚们的思想大为震动,并认识到中国的科技落后、政治腐败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戊戌变法”以六君子的被杀而成为过眼烟云,但变法失败后,引进和推广近代农业科技没有停止,此后的农业政策一变封建时代的劝农措施而成为鼓励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是,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为什么不能象欧洲一样开始实现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化?从需求方面来看,也许中西方农民对实验农学的需求有侧重点及程度上的差异[[xii]],需求总会是存在的,问题是供给的缺乏,已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明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节约土地的高产技术并不缺乏需求的话,那么对于实验农学的阙如与滞后就只能从技术供给的方面去寻找原因了。”\n[[xiii]]。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传统农学以经验为基础,农民的农业生产实践对传统农学的丰富与发展作用很大,但实验农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以科学为基础,不是经验的积累所能胜任的,而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是没有知识的,其对实验农学的供给便无能为力了。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化受到的约束是多方面的。任何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以及引进,离不开人的作用,而人都是具有一定文化观念的。本文将对甲午战争前清代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过程所受到的观念约束进行分析。知识分子在实验农学的产生与发展中作用重大,中国的“士”的科技观念不可忽视,并且,在清代,封建专制也体现在统治者对文化方面,统治者的话具有“一言九鼎”的作用,统治者的观念通过制度实施的环节便对农业科技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本文分析统治者以及士的观念对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约束状况。[[i]]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418页。[[ii]]J·李比希著、刘更令译《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农业出版社1983年出版。[[iii]]、[4]《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丛书16,布瑞著,李学勇译《中国农业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发行,第135页、138页。[[v]]陈美东:《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转引自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vi]]袁翰青《袁翰青文集》,科学技术二、统治者的观念约束(一)经世致用的科技目的观。这种经世致用具有突出的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说封建统治者完全不重视农业科技是不顾事实的,中国\n官方大型农书的出版,重农政策的推行,农业科技的推广,这些都离不开统治者的重视。就说在清朝,康熙皇帝推广“御稻”及双季稻,清朝皇帝写了许多劝农诗,也足见其对农业技术不是不关心的。统治者这样做,主要是对国计民生有用,与经世致用的科技目的观是一致的。毕竟,历代朝廷尽力保存及发展农业科技成果是因为国家赋税之重心来自农民。有学者对这种经世致用的内涵作了剖析后认为,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这种务实精神的伦理特征,不仅体现在发展农业或与军事有关的科学上,而且还渗透于其他各门学科中。”[[i]],说到底,历朝统治者把文化包括科技是作为政治的附庸的,这种经世致用具有突出的政治功利性的特点,统治者认为是不是致用非常关键,国家统治者有没有认识到某种科技对他的治国方略有重要意义,便会对这种科学的发展及其趋势有关键性影响。席泽宗先生分析了康熙科学政策的一系列失误,而这些失误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ii]]。其实,究其原因,清前期的统治者并未看到科技进步对国家的持久强盛的极端重要性。科技进步在统治者的施政目标中重要性不大,该时期统治者的施政目标,仍与其他封建皇帝一样,把增加人口、垦辟土地、扩大疆域、增加赋税、维持社会稳定作为主要立足点,问题\n是此时已与以前的封建王朝不同,西方的近代科技已开始发展,而其现实的、潜在的力量远非康熙大帝所能预想。康熙大帝如果意识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中国的持久强盛的重要作用,他们为了维护皇族利益及维持其统治会重视科技的,事实也是,1840年后,统治者认识到了西洋科技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学习他的“长技”,难以再鄙弃其为“夷技”了。关于经世致用科技目的观的政治功利性的内在缺陷,早在康熙时期就有西人有所认识,巴多明在致德梅朗的信中写道:“尽管康熙皇帝让人重编了数表,又把那么些好的仪器都放在观象台内,并且他也知道这些望远镜与座钟对准确观象是多么重要,但却从没有命令他的数学家利用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人大反特反新发明,并且强调自己民族崇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iii]]他们是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而非一般百姓,他们的观念通过制度实施的环节对社会和人民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统治者既然看不到科技对国家持久强盛的重要作用,他们通过文字狱、八股取士、组织整理古籍而束缚知识分子的创新便不足为奇了。这样,知识分子便更加轻视科技这类“雕虫小技”、轻视劳动,而只知埋头古书之中。\n对农业科技来说,清前期,统治者在对科技功能认识上的偏差,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对农业科技的钻研,在1840年以后,一些受西学影响较深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看到西方近代农业胜过中国传统农业,纷纷提出学习西洋的农业技术。但统治者引进吸收哪些科技是能经世致用呢?这时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利用同样显示出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政治功利性,对农业改良并未足够注意,梁启超指出“自从失香港、火烧圆明园之后,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利炮’”[[iv]]他对轻视农业表达了忧虑:“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v]],张謇也指出了农业的重要:“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不在商也,在于工与农,而农尤要”[[vi]]。统治者忽视农业改良而重视船坚利炮以及机器,这有当时不得不应对内外交困之局面的原因,但“洋务派”主观上“求强”、“求富”的政治功利性及短视性质,对引进西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表现在农业方面,虽然已步入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又使得人口锐减、荒地广阔,但统治者仍不注重吸收西方实验农学的成果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是把其职能主要定位在垦地变广和赋税增多上面,可以说仍在传统农业科技上运作,这就决定了该时期对西方实验农学的引进和利用不可能有大的动作。(二)“华夏中心主义”这在1840年前的清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席泽宗先生分析出康熙虽然努力学习西方科学,但“\n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炫耀自己,批评别人”[[vii]],确实,康熙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结合其晚年一怒之下令凡不遵守利马窦遗法的教徒一律出境,其后的雍正因党派之争而逐教,我们可以看出,引进西方科技在他们的施政目标中,重要性是微乎其微的,同时,他们所极为看重的是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文化体系、政治体系。他们夜郎自大,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掩耳不闻、视而不见,以中央大国自居,当他发现他所需要的“夷技”与其“华夏中心主义”以及中国的文化、政治体系冲突时,做出如此驱逐的政策是当然的。即使是较爱好西洋科技的康熙大帝,他对西洋机器的功能是认可的,并且认为此类“夷技”无关治国大局,可以“节取其技能”,但同时“禁传其学术”,因为中华帝国在文化上、学术上还是优越的,他同时提倡西学中源,也反映了这一点。统治者对外来文化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也助长了一些保守士大夫的排斥外来文明的意识,不利于对外来科技的吸收和利用。(三)“中体西用”如果说清前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华夏中心论”阻断了明末清初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话,那西洋人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国门后,中国对西学的第二次移植,则是中华民族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特殊境遇下的自我调整。总体上说,在这次移植过程中,可以说已认识到西洋科技是“长技”,并想通过“师夷长技”而达到“\n制夷”“图强”“求富”的目的,但这次运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其行动纲领的,如果“师夷长学”,以洋人为先生,是中国文化断难接受的,它实际上反映了皇族、官僚、士大夫等统治阶层把西学作为一种手段用来达到维护中国的“圣教礼治”的目的,达到努力维护他们等级特权及利益的目的。这种只注重西学物质层面的功利性质是这次运动的内在缺陷,其固然能促成一时一事的解决,却无法促成科学事业发展的持久推动力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中国科技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虽然对物质层面的西方科技的引进是必须的,毕竟,文艺复兴后的技术不是以经验、而是以科学为基础,此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是以突变形式、而不是以渐进形式向前发展的,只有在科学上有所创新,才会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才会产生领先于别人的技术,若仅仅是模仿、改进别人的技术,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的结局是与此缺陷有关的。当时的情况是,已认识到了西洋科技的威力,但主要只是注重物质层面的技术及机器[[viii]],提倡“师夷长技”而已,没有对此类技术的基础——科学,予以注意,对于这内在缺陷,梁启超曾对那时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的状况予以批评[[ix]],是有道理的。洋务运动的内在缺陷对引进西方实验农学有重要影响。在\n“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利炮”以及机器设备,其他的便会放在次要地位了,他一方面表现在对农业改良的忽视,当时清政府虽也主张学习西方,但主要精力用于兴办“洋务”,即通过训练新军、兴办工业来“自强”和“求富”,其并未认识到学习西方实验农学的重要性,这就堵塞了农业改良的道路,正如孙中山所评价的,“我国家自欲引西法以来,唯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x]]。梁启超也在《西学书目表》中对这一点有所评述,他说“论者每谓重商贱农,非也。彼中农家近率改用新法,以化学粪田,以机器收获,每年所入视旧法最少亦可增一倍。中国若能务此,岂患贫耶?”并对洋务不以这些为重而感到可惜。另一方面,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表现在对西洋机器的重视,洋务派的重视欧洲机器,自然包括着对机械农具的一定程度的重视,早在50年代,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已注意到西方农器不用耒耜,但“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xi]]近代洋务派思想的奠基人冯桂芬也曾主张用“西人耕具”来种田,以提高耕作效率,此后,王韬也建议政府购买西洋仪器“以利耕播”\n,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出现了大量荒地,资产阶级一些经济学家已看到大机器生产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有效法资本主义农业的思想,当时有记载说“至于垦辟之事,发逆初平,三吴当事,拟用西洋机器,事虽未行,然可想见其器必用。”[[xii]]这种注意学习西方农业科技表层上东西的特征与洋务派总体上的中体西用是一致的。[[i]]陈爱华:《试论我国传统科学精神的伦理特征与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期。[[ii]]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iii]]转引自韩琦:《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分析》,载于韩琦著:《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五章第二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iv]]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版33页。[[v]]梁启超:《西书提要的农学总序》,《饮冰室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vi]]张謇《请兴农会奏》,《戊戌变法》二,307页[[vii]]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viii]]也有人眼界较开阔,如冯桂芬主张设翻译公所,“择其有理者而译之”,已主张“师夷长学”。[[ix]]葛懋春等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86。\n[[x]]孙中山:《上李鸿章之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xi]]魏源:《海国图志》卷十。[[xii]]《开垦荒地说》,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三《申报》。三、“士”的观念约束(一)“重文轻理”观念中国的“士”有一向看轻“艺成而下”的学问的传统,他们关心的是努力迎合科举制度来升官济世。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士人并不是一贯轻视科技和实践的,在唐代和宋代,朝廷的学校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科目,比如天文、数学等,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些自然科学的学习是有利于农学的发展的,有学者认为从《氾胜之书》中“足以显示汉代农学家均为亲身耕作者,对农耕技术常能洞悉详情。”[[i]],大概秦汉以后,“士”越来越远离农业实践了,清吴邦庆在《泽农要录》(1824)中也指出“古无不学之农”并且“古亦少不农之士”,但是后来的情况是“后世农勤耒耜,而士习章句,判若二途,故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於书,士鄙其土而未由详究其理,即今世传有《齐民要术》、《农桑辑要》诸书,亦不过供学者之流览,於服田力穑者毫无裨补也。”梁启超也指出中国的“士”脱离实践、脱离实验的弊端,“\n秦汉以来,学术日趋无用,……役实南亩者,不识一字,……故学者不农,农者不学……重可概矣。”[[ii]],有人指出“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iii]],清代的文化专制更趋加强,通过文字狱、八股取士、组织整理古籍而束缚知识分子的创新活动,这些也导致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更加鄙弃劳作,知识分子在科技上不敢有创新。“明清进士共51090人,而进士出生的农学家仅14人。”“在重文轻理的指导思想下,整个封建社会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总量已经很少,其中从事农学的自然少之又少。”[[iv]],事实上,即使是农学著作,书中引经据典长编累牍,甚至书中不乏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之词其中很少亲身实践的内容,这在《授时通考》中得到充分体现。知识分子以升官济世为使命,忽视了农学的发展需要脑力劳动的探索才能加深认识其规律,忽视了劳动与实践的重要性,这使得传统农学自发地向实验农学转化几乎不可能,如果与西方知识分子在此转化中的所起的作用作个比较,会更清楚,西方知识分子在实验农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八世纪以来“无分职业者或业余者,许多工程师、土壤学者、测量员、以及植物学者均投入农业之研究\n,并群起发表最新之原理及发明,其后也引发各学者相互辩论各学理之优劣,故自十八世纪以来,有关农业之出版物(如书籍及小册)、专利之申请、以及杂志期刊等,已大批涌现。十七世纪时来华之欧洲人士,对中国农业之成就获有深刻之印象,并携回中国之农书,以图自其中学习农业经营之方法与技术,但欧洲农业于十八世纪在知识及技术发生革新之后,不久即超越东方农书所已提供之农业学术矣。”[[v]]。(二)实用主义的目的观。中国的士除了“重文轻理”外,也有少部分人从事科技包括农业科技的研究,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点区别的是,中国的“士”缺乏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神圣使命的精神,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达到实用。确实,中国历代农学家,始终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科学目的观,毕竟是实用观念,就说著名的《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也是以切合实用为主要目标的,即便是在清末,知识分子所介绍的西方农学“是一种表象化的农业技术,或者说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技术”[[vi]],仍然是体现实用主义的主旨的。传统农学的实用主义特征自不用说,在中国整体科学研究方面,也是实用主义的,即使是抽象性较强的数学,16世纪以前的数学书籍大都是应用问题解法的集成。对天文的研究,目的也是主要预测未来皇朝的命运和政治的变迁。“士”\n的实用主义目的观的致命弱点是,由于缺乏对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神圣使命的精神,当他达到了实用的目的时,这种学问便停止进步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发展到清代,已是很完善了,若没有启蒙文化及近代科技的刺激和影响,确实难以再在原有的路径下有大的突破,无非还是精耕细作而已,农书仍是对数量略有增多的实用性经验的总结。实验农学是另一个情况,有人详细论述了“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指出“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vii]],这样的话,中国的农学落后应从18世纪向前找,1665年虎克用他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这是生物学和农学上的一件大事,试想,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研究一向重实用,会磨出镜子研究当时看不出实用价值的细胞吗?会进而研究当时不会提高产量的动植物受精现象?会费尽心思研究植物吸进去的是氧气还是二氧化碳吗?不大可能。致用与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求真”其实是统一的、一致的,致用性是源于真理性的;但是,科学是以探索自然、发现规律即“求真”为根本目的,有的科学知识,如对细胞、DNA的发现,可以一时离开致用性,但不可一时离开真理性,此类科学虽不直接以“致用”\n为直接目的,但是,以技术为中介,科学依然能达到致用的目的,如DNA的发现和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开辟了生命科学领域的新纪元,并且,科学基础上的技术远比致用目的观指导下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产生更强的社会功能。如只以实用主义为目的,不利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入探讨。已有人指出中国的“士”的实用主义的目的观的缺陷,巴多明指出中国人“只是做到他们自认为需要的那一步”,认为“他们没有那种促使科学进步的远见、紧迫感,而且他们局限于单纯的需要,依照他们所接受关于个人幸福及国家的安定的概念,他们不认为应该着急,也不必苦心积虑地钻研纯思辨的事物,这类事物既不能使人更幸福,也不能使人更安宁。”[[viii]],钱宝琮先生认为,外国人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而中国人太重实用,这是在中国科学不为人重视的原因[[ix]]。此缺陷可能是东方科学研究之通病,法国哲学家列·卢宾指出东方的科学在存在的许多世纪之中,甚至和希腊科学接触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以达到纯粹的思辨和演绎普遍原理的阶段”[[x]]。[[i]]《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丛书16,布瑞著,李学勇译《中国农业史》上册,台湾\n商务印书馆1994年发行70页。[[ii]]梁启超:《农学报序》,1897年。[[iii]]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清代农学的成就和问题》234页,该文对中国“重文轻理”作了详细分析。[[iv]]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从明清时期的农业科学家看农业人才问题》246页。[[v]]《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丛书16,布瑞著,李学勇译《中国农业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发行139页。[[vi]]曹幸穗:《启蒙和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vii]]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清代农学的成就和问题》234页农业考古1990年1期。[[viii]]转引自韩琦:《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分析》,载于韩琦著:《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五章第二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ix]]转引自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原载《科学》第28卷第3期,1946年9月。\n[[x]]转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142页。四、小结甲午战争前,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观念约束主要可分为统治者和“士”两方面,具体地,对统治者来说,经世致用科技目的观的政治功利性特征、“华夏中心主义”对西方科技的排斥作用、“中体西用”观对物质层面的西方科技的偏重;对“士”来说,重文轻理观念、实用主义的目的观,这些都约束了中国实验农学的产生。IdeaRestrictionsofTransformationfromTraditionaltoExperimentalAgronomybeforeJiaationfromTraditionaltoExperimentalAgronomyoreattentiontohumanitiesthansciences,ergenceofExperimentalAgronomyinChina.Keyy,ExperimentalAgronomy,IdeaRestriction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