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7 发布 |
- 37.5 KB |
- 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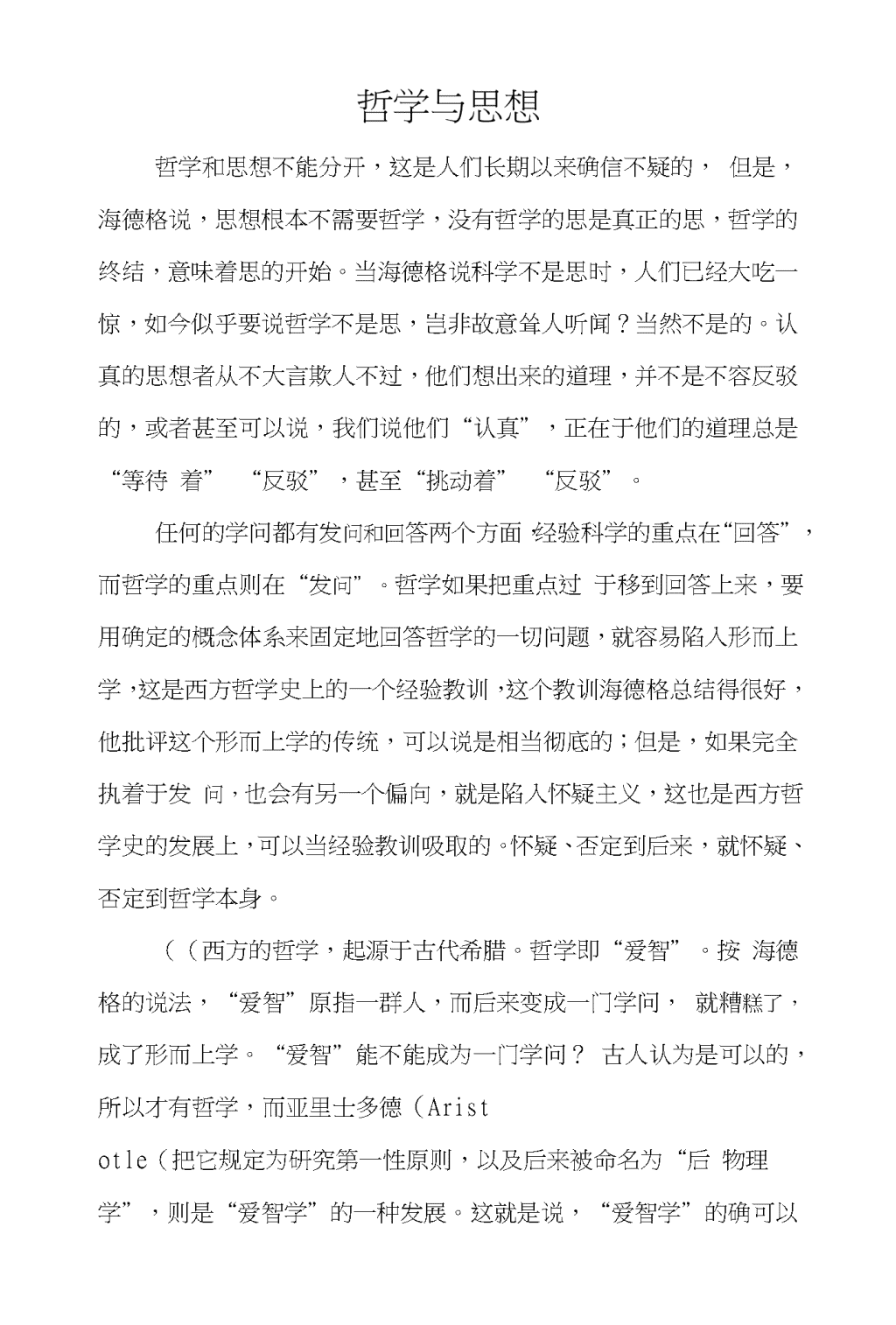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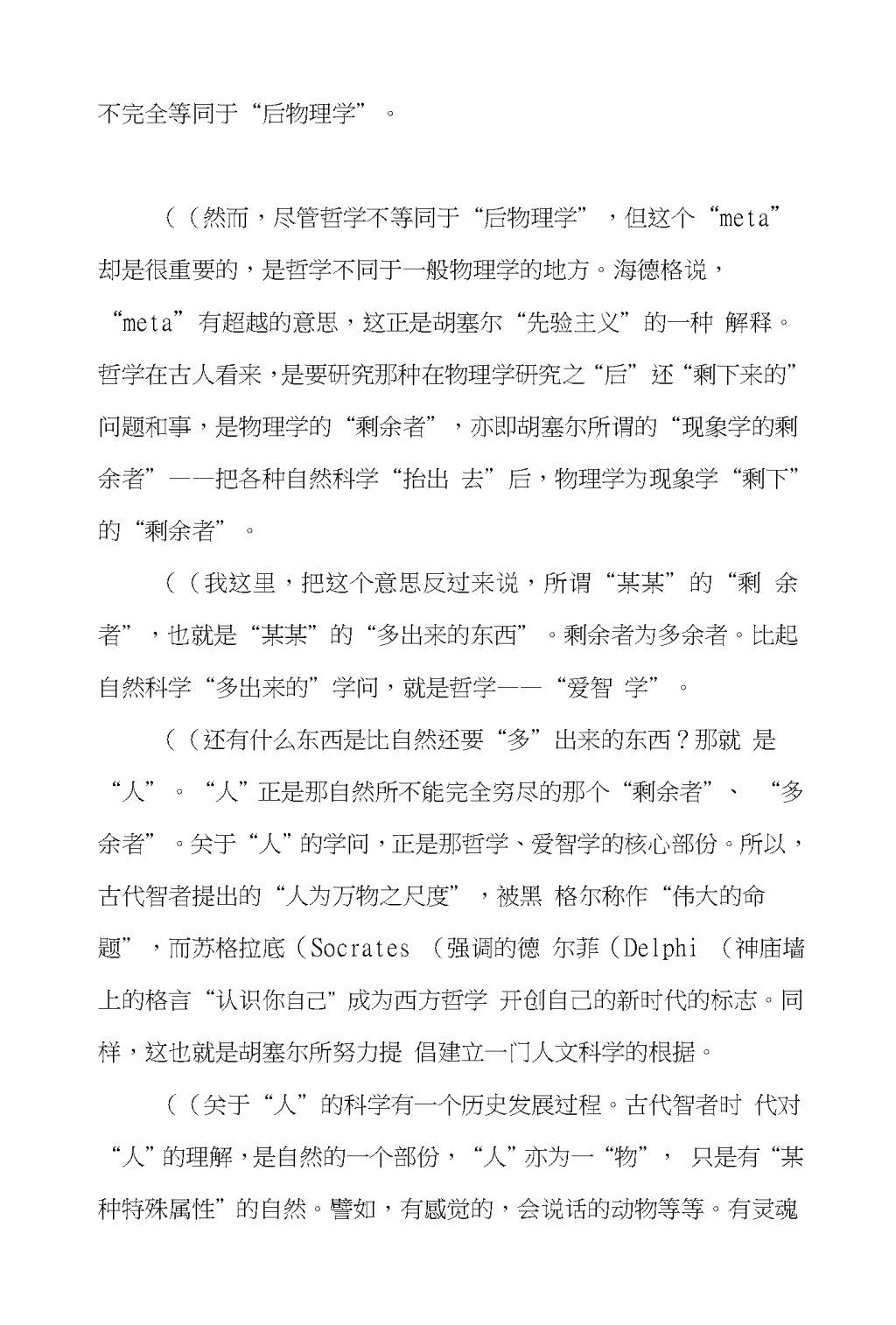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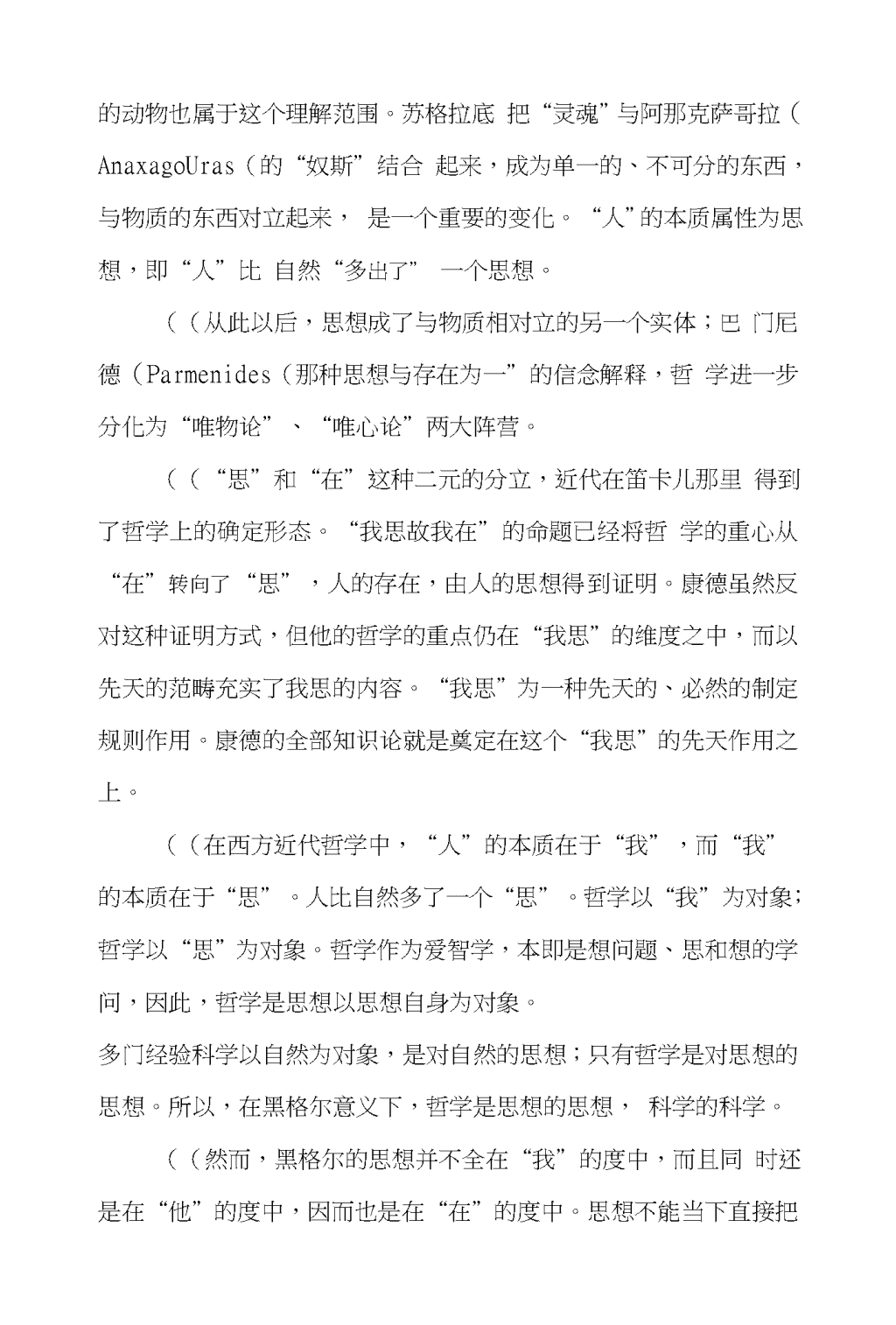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哲学与思想
哲学与思想哲学和思想不能分开,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确信不疑的,但是,海德格说,思想根本不需要哲学,没有哲学的思是真正的思,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思的开始。当海德格说科学不是思时,人们已经大吃一惊,如今似乎要说哲学不是思,岂非故意耸人听闻?当然不是的。认真的思想者从不大言欺人不过,他们想出来的道理,并不是不容反驳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我们说他们“认真”,正在于他们的道理总是“等待着”“反驳”,甚至“挑动着”“反驳”。任何的学问都有发问和回答两个方面,经验科学的重点在“回答”,而哲学的重点则在“发问”。哲学如果把重点过于移到回答上来,要用确定的概念体系来固定地回答哲学的一切问题,就容易陷入形而上学,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经验教训,这个教训海德格总结得很好,他批评这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可以说是相当彻底的;但是,如果完全执着于发问,也会有另一个偏向,就是陷入怀疑主义,这也是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上,可以当经验教训吸取的。怀疑、否定到后来,就怀疑、否定到哲学本身。((西方的哲学,起源于古代希腊。哲学即“爱智”。按海德格的说法,“爱智”原指一群人,而后来变成一门学问,就糟糕了,成了形而上学。“爱智”能不能成为一门学问?古人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才有哲学,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它规定为研究第一性原则,以及后来被命名为“后物理学”,则是“爱智学”的一种发展。这就是说,“爱智学”\n的确可以不完全等同于“后物理学”。((然而,尽管哲学不等同于“后物理学”,但这个“meta”却是很重要的,是哲学不同于一般物理学的地方。海德格说,“meta”有超越的意思,这正是胡塞尔“先验主义”的一种解释。哲学在古人看来,是要研究那种在物理学研究之“后”还“剩下来的”问题和事,是物理学的“剩余者”,亦即胡塞尔所谓的“现象学的剩余者”——把各种自然科学“抬出去”后,物理学为现象学“剩下”的“剩余者”。((我这里,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所谓“某某”的“剩余者”,也就是“某某”的“多出来的东西”。剩余者为多余者。比起自然科学“多出来的”学问,就是哲学——“爱智学”。((还有什么东西是比自然还要“多”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人”。“人”正是那自然所不能完全穷尽的那个“剩余者”、“多余者”。关于“人”的学问,正是那哲学、爱智学的核心部份。所以,古代智者提出的“人为万物之尺度”,被黑格尔称作“伟大的命题”,而苏格拉底(Socrates(强调的德尔菲(Delphi(神庙墙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成为西方哲学开创自己的新时代的标志。同样,这也就是胡塞尔所努力提倡建立一门人文科学的根据。((关于“人”的科学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古代智者时代对“人”的理解,是自然的一个部份,“人”亦为一“物”,只是有“某种特殊属性”的自然。譬如,有感觉的,会说话\n的动物等等。有灵魂的动物也属于这个理解范围。苏格拉底把“灵魂”与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Uras(的“奴斯”结合起来,成为单一的、不可分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对立起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人”的本质属性为思想,即“人”比自然“多出了”一个思想。((从此以后,思想成了与物质相对立的另一个实体;巴门尼德(Parmenides(那种思想与存在为一”的信念解释,哲学进一步分化为“唯物论”、“唯心论”两大阵营。((“思”和“在”这种二元的分立,近代在笛卡儿那里得到了哲学上的确定形态。“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已经将哲学的重心从“在”转向了“思”,人的存在,由人的思想得到证明。康德虽然反对这种证明方式,但他的哲学的重点仍在“我思”的维度之中,而以先天的范畴充实了我思的内容。“我思”为一种先天的、必然的制定规则作用。康德的全部知识论就是奠定在这个“我思”的先天作用之上。((在西方近代哲学中,“人”的本质在于“我”,而“我”的本质在于“思”。人比自然多了一个“思”。哲学以“我”为对象;哲学以“思”为对象。哲学作为爱智学,本即是想问题、思和想的学问,因此,哲学是思想以思想自身为对象。多门经验科学以自然为对象,是对自然的思想;只有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所以,在黑格尔意义下,哲学是思想的思想,科学的科学。((然而,黑格尔的思想并不全在“我”的度中,而且同时还是在“他”的度中,因而也是在“在”的度中。思想不\n能当下直接把握自身,必须通过“在”、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自己把握自己,因而对黑格尔来说,思想自身的把握,为一个辩证的过程。思想——人之本质,在“他在”中显现自身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哲学预先设立了一个活泼的、外向性的“精神”,先“他在”化而又期待、争取着向自身“复回”。这就是说,黑格尔设定了一个与存在可合、可分的绝对的思想,而胡塞尔则认定思想原就在生活的世界之中。作为剩余者的“思”,并不是概念性的“纯思”,而是非概念性的“纯心理”。纯思是抽象的;纯心理则是具体的。纯思的“我”为思想者,纯心理的“我”则是生活中的“人”。((人不但“活动”起来一因为精神本是活泼的,而且“实在”起来,现象学的剩余者、多余者为“有”,而非“无”。纯思的度,为“无”的度,为“无度”一无限。沙特(Jean—Paul(Sartre(说,人给世界增加个“无”,思想、意识为不存在。但我们却确确实实地知道人“有”思想,人“在”思想。“思”和“在”在人身上,绝不可分。我思与我在绝不可分。我思不是无,而是有;我在不是物,而是人。我之“思”,必为“在”;我之“在”,亦必有“思”。((我之“在”不是“在”那虚无缥缈、乌何有之乡,而是“在”一个世界中,在时空中,在世间。我之“思”和我之“在”不可分,即我之思和我之世界不可分。我在世界中,即思在世界中,既非纯思,亦非纯有。\n((纯思为无,“纯有”又何为?((纯有可以不是“有”之概念,因为概念为无,这个纯有就与无同一,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纯有应是实实在在的“有”;但是这个“有”对智慧、思想就是封闭的,是智慧之光未曾照耀到的地方。纯有为暗,为玄,为幽、为冥。暗不是无,而是实在的“有”。纯而又纯的“有”,为玄而又玄的“在”。对这个“有”如硬要去思它,则必是玄思、冥想,如同在黑夜中玄思冥想。这是一种脱离世界的思。玄思、冥想与幻想、幻听一样,为疯的病根。长期以来,西方人企用形而上学来治疗这种玄思冥想的病,想通过一个清楚明白的概念学说体系使那个“暗”,那个纯有,“明”起来,但逐渐被发现,疗效甚微。((“有”可以被想象成纯而又纯,不但可以概念化,而且也可以成为暗,但“是”则必要“是”些什么。有可以想象成无名之朴,惚兮恍兮;但“是”则必有“名”相随。纯有之暗,可以是真实的,其中有象,其象还可以甚真,但不可为真理。真理为真之即以为真之理;亦即是什么之所以为是什么之理。西方人把“是”动名词化,为一纯粹之“是”,从而把“是”当作“有”,于是把这个纯有当作哲学之对象,才有以纯有为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把无限当作一个全体性的什么来研究,似乎这个无限也可以对象化成为一个什么,从而可以用范畴体系去把握它,这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办法。这种学问的体系与物理学无异,但其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不同于物理学,是在物理学之外,之上,之后的。作为形而上\n学的哲学是西方人用来医治思想病的一种不太好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学式的哲学,源于西方远古的某种崇拜。西方哲学在其母胎里留有这种原始宗教崇拜的痕迹。泰利士(Thales(的“水”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之“anei(Pov”原为暗、无定,哲学就是要研究这个不透明的暗的本源。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是西方哲学史上很关键的人物,他的“A0Yo(”使古代希腊人摆脱那原始崇拜的影响,有了烛照一切的火;但由于那个万有之全的深渊仍在作祟,所以那个“入oY0(”渐渐竟成为只有一种先天形式意义的逻辑。逻辑是健全的理性,而且只有逻辑才是健康的,但逻辑却只是形式,只是思想的形式。这就是说,思想只有在没有内容的情况下,才是健康的、明亮的;哲学之\n所以使人健康,就在于它是形式的、纯思想的学问。这样,只有在“思”与“在”分离的情况下,“思”的病才能治愈这是传统哲学的一种隔离治疗法。((然而,纯思只能与纯有对立,而不能真正使它“明”起来;相反,纯有却为康德的物自身那样常扰乱人的思想;“有”对“思”有一种威胁性,纯有的观念对思想言,竟是一种病毒。人既是万物“多”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剩余者、多余者,万物却时时在吸收、吞噬着这个多余者。病是不可回避的,死对个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固然不能真的经验自己的死,但纯有的“暗”却时时提示着死的意味。康德对崇高的分析,揭示过这方面的问题,而当代西方经常可以遇到的那令人目眩的绘画、雕塑,同样是这个纯有的提示者。冥思、玄想、幽思然为怪,为病,但亦还吸引着一部份人。哲学要真正摆脱这种玄思、冥想,还要作出相当的努力。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不能真的治好思想的病而只能掩盖这种病,使那个病源——纯有、无限、大全等等在暗暗地滋长、繁殖、蔓延。((这样,保护、纵容玄思、冥想病的形而上学本身也成了一种思想的病,而常常受到批判。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指出,那个大全、无限本不是某种特殊的什么,不是万有中的“一有”,而是一个思想,一个理念,万物都是有限的、相对的,而唯有思想和理念,才是无限的、绝对的。特别是黑格尔,把那个原本是万有物质性的无限,转移到思想方面来,使得\n思想本身也复杂化、纷繁化和晦暗化起来,思想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明”起来的,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也是一种玄思一一spekulativ,在拉丁文字源中有窥视、探视这类的意思,的确有点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意味。我们看到,在某个方面来看,把纯有的无限转移到思想方面来,使思想有了这个无限的内容,一方面固然克服了把思想限制于形式的毛病,但却未曾在根本上克服形而上学,反而加深了形而上学,使思想的病更沉重起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使思想浓厚起来,自己也成了一个黑暗的深渊。((思想的疾病,似乎就出在那个无限、大全上,或者把“有”想成无限、大全,或者把“思”想成无限、大全,都是这个疾病的征兆。思想要健康起来,就得从天上回到地上,也从地下回到地上,回到这个我们现实生活的、我们工作劳动、我们日常谈论和我们经常思考的世界中来。“我”不是纯思,“世界”也不是纯有,我在世界中,世界和我都是具体的、实在的,在一种联结的关系之中。“我”是“DasEin”,“世界”也是“DasEIn”。((海德格提出从“Dasein”来理解“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贡献,但他以为“Dasein”就可以使“Sein”“明”起来,则未必能如所愿。单纯的“Sein”是不能“明”(起来的,这一点,后来法国的勒维纳斯((指出来了,他说得很有理,也很有真情实感。光“Sein”还不是“人”生活的世界,人的生活的世界要比“Sein”“多”(出点什么来,要增加点\n什么,纯有才能转化为世界。增加的什么就是那个“Da”。有了“Da”,“Sein”才成了“Dasein”。所以,我们并不能说,人是“Dasein”,而世界是“Sein”;我们只能说,人是“Dasein”,世界也是“Dasein”。舍去那个“Da”,谈不到人及其世界。人是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人,而世界就正是生活。人是具体的,世界也是具体的,世界使人成为人,人也使世界成为世界。如果说,哲学为关于那个包括了人及其世界的“Dasein”的思想的话,那么哲学就不是本体论,而是具体论——对这个希腊字可稍加改动,成为“ontaology”,因为(onta(为(on(之复数形式。((从“Dasein”方面来考虑人,海氏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但从“Dasein”方面来看世界则比较弱一点。实际上,世界作为“Dasein”来看,使人想起胡塞尔的生活的世界,那个很是重要的“什么”。世界由“什么”组成,而不是由那个单纯的“是”组成。“说”要说点什么,“是”也要是个什么((人的生活的世界是说得出来的世界,是有名的世界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将质料改造为“器”。并不是“人”像神那样从“无”中生“有”,而是因为“朴”在人的世界里,本就是“器”。就连那人迹未到的大漠荒原、原始森林、星河太空……仍可是人的世界的一个部份。((世界作为“DasEin”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人的世界,首先是他人的世界。“我”是“DasEIn”,“你”是“Dasein”,“他”也可是“Dasein”。“我”并不孤独地在世上,相反,人使世界成为世界,首先是指他人使世界成为世界,他人使\n“Sein”成为“Dasein”;他人使纯有成为“什么”。世界的意义是他人向“我”指示出来的。即使是“我”的“Dasein”,也是他人给与的。“我”是接受者、受惠者。他人使“我”成为“我”。((“Da”对“Sein”而言是多出的,超越的,也是限制的,所以,不是无限超越有限,而是有限超越无限。人的超越性,在他的有限性、具体性。限制是否定,也是肯定;限制使世界成为什么,使人成为我、你、他,使人成为“什么”。“Sein”并不能限制“我”,但另一个“Dasein”却必定限制着“我”,规范着“我”,使“我”和谐地、合适地、健康地生活在他人之中;只有“你”,才能使“我”避免发疯,只有由他人组成的社会才能确定“我”不曾在发疯。“我”不能使“Sein”“明”,“Sein”也不能使“我”“明”;疯是孤独、离群、隔离的产物和结果。有时,一群人也会发疯甚至更容易发疯,那是这群人已不是具体的(Dasein,而是一个孤独的大我。“我”不论大小、多少,只要先有“我”,就有可能发疯。你和他是使“我”健全的保障。哲学作为健全的学问,首先是他人的学问,是“你”的学问,不是首先是“我”的学问;“我”必须向“你”学,接受“你”的教育。((哲学要授人以智慧,要使人清楚、明白,而不要使人胡涂,则要引导人去“思”那现实的、有限的、具体的世界,而不要诱导人去“思”那深不可测、说不清楚的无限。哲学要按照世界向人显示的那个实在的样子来思考、理解世界,哲学按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n((这样,哲学要给思想以一种限制和规范,不使它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不能被吸收到那个无底的深渊中去。幻想不是思想。所以哲学限制思想,同时也使思想成为思想。哲学把思想限制于产生它的现实生活和实际世界之中。不受限制的思想是一切思想疾病的根源。人可以没有上帝而生活得更好,但没有哲学的思想,只能使人发疯。从这个意义说,不要哲学则确是一种很坏的哲学。((如果我们暂时允许把“思”和“在”分开来说,那么哲学使“思”超越自力,而回到“在”中来,哲学使“Da”与“Sein”结合起来,使“Dasein”真正成为“Dasein”。((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可以认真考虑至少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批评理性的僭越和语言的滥用这些意思对促进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里,当然还包括了维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那句名言“对不可言说者须保持沉默”。这样,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非常普通的道理:哲学为思想之训练。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