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7 发布 |
- 37.5 KB |
- 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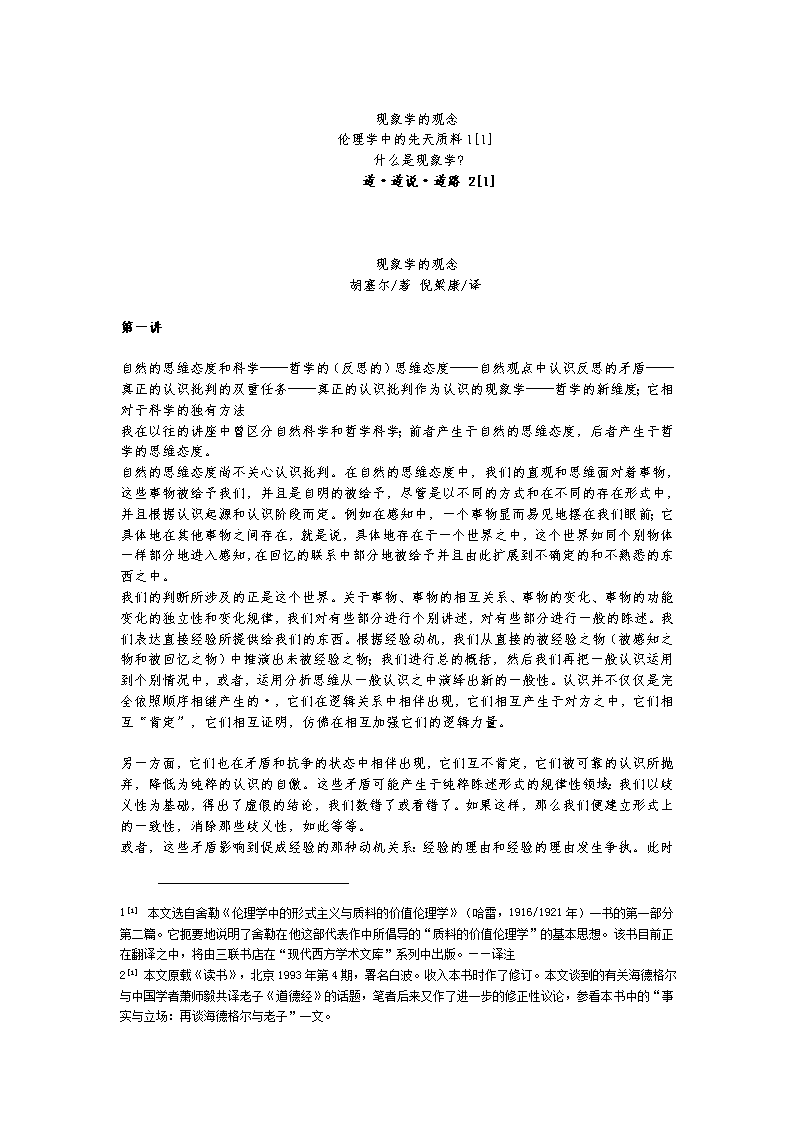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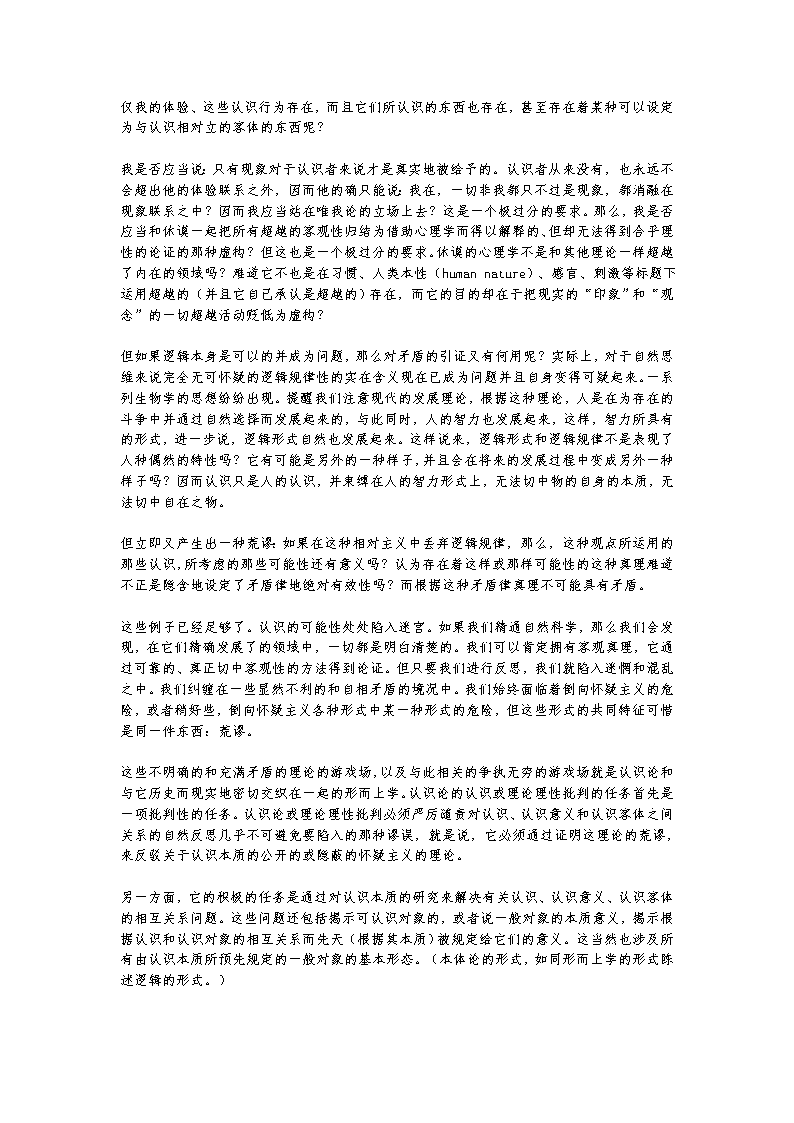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哲学经典论文精选
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现象学的观念伦理学中的先天质料[1]本文选自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哈雷,1916/1921年)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篇。它扼要地说明了舍勒在他这部代表作中所倡导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该书目前正在翻译之中,将由三联书店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中出版。——译注[1]什么是现象学?道·道说·道路[1]本文原载《读书》,北京1993年第4期,署名白波。收入本书时作了修订。本文谈到的有关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共译老子《道德经》的话题,笔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性议论,参看本书中的“事实与立场: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一文。[1]现象学的观念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第一讲自然的思维态度和科学——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态度——自然观点中认识反思的矛盾——真正的认识批判的双重任务——真正的认识批判作为认识的现象学——哲学的新维度;它相对于科学的独有方法我在以往的讲座中曾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科学;前者产生于自然的思维态度,后者产生于哲学的思维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和思维面对着事物,这些事物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的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形式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例如在感知中,一个事物显而易见地摆在我们眼前;它具体地在其他事物之间存在,就是说,具体地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如同个别物体一样部分地进入感知,在回忆的联系中部分地被给予并且由此扩展到不确定的和不熟悉的东西之中。我们的判断所涉及的正是这个世界。关于事物、事物的相互关系、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功能变化的独立性和变化规律,我们对有些部分进行个别讲述,对有些部分进行一般的陈述。我们表达直接经验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根据经验动机,我们从直接的被经验之物(被感知之物和被回忆之物)中推演出未被经验之物;我们进行总的概括,然后我们再把一般认识运用到个别情况中,或者,运用分析思维从一般认识之中演绎出新的一般性。认识并不仅仅是完全依照顺序相继产生的·,它们在逻辑关系中相伴出现,它们相互产生于对方之中,它们相互“肯定”\n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现象学的观念伦理学中的先天质料[1]本文选自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哈雷,1916/1921年)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篇。它扼要地说明了舍勒在他这部代表作中所倡导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该书目前正在翻译之中,将由三联书店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中出版。——译注[1]什么是现象学?道·道说·道路[1]本文原载《读书》,北京1993年第4期,署名白波。收入本书时作了修订。本文谈到的有关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共译老子《道德经》的话题,笔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性议论,参看本书中的“事实与立场: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一文。[1]现象学的观念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第一讲自然的思维态度和科学——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态度——自然观点中认识反思的矛盾——真正的认识批判的双重任务——真正的认识批判作为认识的现象学——哲学的新维度;它相对于科学的独有方法我在以往的讲座中曾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科学;前者产生于自然的思维态度,后者产生于哲学的思维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和思维面对着事物,这些事物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的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形式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例如在感知中,一个事物显而易见地摆在我们眼前;它具体地在其他事物之间存在,就是说,具体地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如同个别物体一样部分地进入感知,在回忆的联系中部分地被给予并且由此扩展到不确定的和不熟悉的东西之中。我们的判断所涉及的正是这个世界。关于事物、事物的相互关系、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功能变化的独立性和变化规律,我们对有些部分进行个别讲述,对有些部分进行一般的陈述。我们表达直接经验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根据经验动机,我们从直接的被经验之物(被感知之物和被回忆之物)中推演出未被经验之物;我们进行总的概括,然后我们再把一般认识运用到个别情况中,或者,运用分析思维从一般认识之中演绎出新的一般性。认识并不仅仅是完全依照顺序相继产生的·,它们在逻辑关系中相伴出现,它们相互产生于对方之中,它们相互“肯定”\n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螃袆莃薂螃羈芆蒈螂肁蒁莄螁膃芄蚃螀袃肇蕿衿羅节蒅袈肇肅莁袇螇芀芆袇罿肃蚅袆肂荿薁袅膄膂蒇袄袄莇莃袃羆膀蚂羂肈莅薈羂膀膈蒄羁袀莄莀薇肂膆莆薆膅蒂蚄薅袄芅薀薅羇蒀蒆薄聿芃莂蚃膁肆蚁蚂袁芁薇蚁羃肄薃蚀膆芀葿虿袅膂莅虿羈莈蚃蚈肀膁蕿蚇膂莆蒅螆袂腿莁螅羄莄芇螄肆膇蚆现象学的观念伦理学中的先天质料[1]本文选自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哈雷,1916/1921年)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篇。它扼要地说明了舍勒在他这部代表作中所倡导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该书目前正在翻译之中,将由三联书店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中出版。——译注[1]什么是现象学?道·道说·道路[1]本文原载《读书》,北京1993年第4期,署名白波。收入本书时作了修订。本文谈到的有关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共译老子《道德经》的话题,笔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性议论,参看本书中的“事实与立场: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一文。[1]现象学的观念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第一讲自然的思维态度和科学——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态度——自然观点中认识反思的矛盾——真正的认识批判的双重任务——真正的认识批判作为认识的现象学——哲学的新维度;它相对于科学的独有方法我在以往的讲座中曾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科学;前者产生于自然的思维态度,后者产生于哲学的思维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和思维面对着事物,这些事物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的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形式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例如在感知中,一个事物显而易见地摆在我们眼前;它具体地在其他事物之间存在,就是说,具体地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如同个别物体一样部分地进入感知,在回忆的联系中部分地被给予并且由此扩展到不确定的和不熟悉的东西之中。我们的判断所涉及的正是这个世界。关于事物、事物的相互关系、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功能变化的独立性和变化规律,我们对有些部分进行个别讲述,对有些部分进行一般的陈述。我们表达直接经验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根据经验动机,我们从直接的被经验之物(被感知之物和被回忆之物)中推演出未被经验之物;我们进行总的概括,然后我们再把一般认识运用到个别情况中,或者,运用分析思维从一般认识之中演绎出新的一般性。认识并不仅仅是完全依照顺序相继产生的·,它们在逻辑关系中相伴出现,它们相互产生于对方之中,它们相互“肯定”\n,它们相互证明,仿佛在相互加强它们的逻辑力量。另一方面,它们也在矛盾和抗争的状态中相伴出现,它们互不肯定,它们被可靠的认识所抛弃,降低为纯粹的认识的自傲。这些矛盾可能产生于纯粹陈述形式的规律性领域:我们以歧义性为基础,得出了虚假的结论,我们数错了或看错了。如果这样,那么我们便建立形式上的一致性,消除那些歧义性,如此等等。或者,这些矛盾影响到促成经验的那种动机关系:经验的理由和经验的理由发生争执。此时我们如何自助呢?这时我们就权衡各种可能的规定或解释的理由,弱的理由必须向强的理由让步,这些强的理由现在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将保持下去,直到它们不能再继续维持原状时为止,就是说,直到它们为反对新的、提供了更广泛认识领域的认识动机所进行的类似的逻辑战斗进行不下去时为止。自然的认识就是这样前进着。它在不断扩展的范围中获得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地存在着的被给予的、并只根据范围和内容、根据诸要素、关系、规律进一步研究的现实性。于是这样就形成和成长出各种自然科学,作为关于物理和心理自然的科学的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另一方面是数学科学,关于数、多样性、关系的科学等等。后一类科学与实在的现实无关,而是与观念的、自在有效的、此外从一开始就无可怀疑的可能性有关。自然的科学认识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困难的产生和解决,这些困难或是纯逻辑方面的,或是质料方面的,它们根据事物中蕴有的动力或思维动机而产生和消除,这些动力和动机存在于事物之中,并像是从中出发,被给予性向认识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将自然的思维态度或者说自然的思维动机与哲学的思维动机进行对照。随着认识和对象之间关系的反思的苏醒,出现了深不可测的困难。认识,这个在自然思维中最显而易见的事物一下子变成了神秘的东西。但我必须更严格一些。认识的可能性对自然思维来说是自明的。自然思维的工作已结出了无限丰硕的成果,日新月异的科学是一个发现连着一个发现向前迈进,它根本就不会想到要提出关于认识可能性的问题。当然,对它来说,认识也像出现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以某种方式成为问题,认识成为自然研究的客体。认识是自然的一个事实,它是任何一个认识着的有机生物的体验,它是一个心理事实。人们可以根据它的种类和它的联系形式,像对待每一心理事实那样对它进行描述,并不在它的生物发生学的联系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认识根据其本质是关于对象的认识,它的内在意义使它与对象相联系,并决定了此种认识之所以为此种认识。自然的思维也是在这种联系中进行的。它在形式上一般将含义(2)和含义有效性的先天联系以及属于对象本身的先天规律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产生了一种纯粹的语法并在更高阶段上产生了一种纯粹逻辑(根据其各种可能的限制而形成的诸规则之总和),并且又形成一种作为思维艺术的学说、主要是作为思维科学的工艺学说的日常实用逻辑。至此我们仍然站在自然思维的基础上。但正是刚才为了对照认识心理学、纯粹逻辑和本体论而涉及的关于认识体验、含义和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最深刻和最困难的的问题的起源,一言以蔽之,是关于认识可能性问题的起源。认识在其所有展开的形态中都是一个心理的体验,即都是认识主体的的认识。它的对立面是被认识的客体。但是现在认识如何能够确定它与被认识的客体相一致,它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准确地切中它的客体?对于自然思维来说说自明的认识客体的被给予性在认识中进入迷宫。在感知中,被感知之物应当是直接被给予的。这时事物出现在我们对它进行感知的的眼睛面前,我看见它、抓住它。但知觉仅仅是我这个感知主体的体验。回忆、期待也是如此,一切以此为基础并导致对实在存在的间接设定以及对关于存在的任何真实性的确定的思维行为都是如此,它们是主观的体验。我这个认识者从何知道,并且如何能够准确地知道,不仅我的体验、这些认识行为存在,而且它们所认识的东西也存在,甚至存在着某种可以设定为与认识相对立的客体的东西呢?我是否应当说:只有现象对于认识者来说才是真实地被给予的。认识者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超出他的体验联系之外,因而他的确只能说:我在,一切非我都只不过是现象,都消融在现象联系之中?因而我应当站在唯我论的立场上去?这是一个极过分的要求。那么,我是否应当和休谟一起把所有超越的客观性归结为借助心理学而得以解释的、但却无法得到合乎理性的论证的那种虚构?但这也是一个极过分的要求。休谟的心理学不是和其他理论一样超越了内在的领域吗?难道它不也是在习惯、人类本性(humannature)、感官、刺激等标题下运用超越的(并且它自己承认是超越的)存在,而它的目的却在于把现实的“印象”和“观念”\n的一切超越活动贬低为虚构?但如果逻辑本身是可以的并成为问题,那么对矛盾的引证又有何用呢?实际上,对于自然思维来说完全无可怀疑的逻辑规律性的实在含义现在已成为问题并且自身变得可疑起来。一系列生物学的思想纷纷出现。提醒我们注意现代的发展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人是在为存在的斗争中并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人的智力也发展起来,这样,智力所具有的形式,进一步说,逻辑形式自然也发展起来。这样说来,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表现了人种偶然的特性吗?它有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样子,并且会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吗?因而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物的自身的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但立即又产生出一种荒谬:如果在这种相对主义中丢弃逻辑规律,那么,这种观点所运用的那些认识,所考虑的那些可能性还有意义吗?认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可能性的这种真理难道不正是隐含地设定了矛盾律地绝对有效性吗?而根据这种矛盾律真理不可能具有矛盾。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认识的可能性处处陷入迷宫。如果我们精通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它们精确发展了的领域中,一切都是明白清楚的。我们可以肯定拥有客观真理,它通过可靠的、真正切中客观性的方法得到论证。但只要我们进行反思,我们就陷入迷惘和混乱之中。我们纠缠在一些显然不利的和自相矛盾的境况中。我们始终面临着倒向怀疑主义的危险,或者稍好些,倒向怀疑主义各种形式中某一种形式的危险,但这些形式的共同特征可惜是同一件东西:荒谬。这些不明确的和充满矛盾的理论的游戏场,以及与此相关的争执无穷的游戏场就是认识论和与它历史而现实地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认识或理论理性批判的任务首先是一项批判性的任务。认识论或理论理性批判必须严厉谴责对认识、认识意义和认识客体之间关系的自然反思几乎不可避免要陷入的那种谬误,就是说,它必须通过证明这理论的荒谬,来反驳关于认识本质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怀疑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的积极的任务是通过对认识本质的研究来解决有关认识、认识意义、认识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问题还包括揭示可认识对象的,或者说一般对象的本质意义,揭示根据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相互关系而先天(根据其本质)被规定给它们的意义。这当然也涉及所有由认识本质所预先规定的一般对象的基本形态。(本体论的形式,如同形而上学的形式陈述逻辑的形式。)正是通过完成这些任务,认识论才有能力进行认识批判,更明确地说,有能力对所有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认识进行批判。即:它使我们能够以正确的和彻底的方式解释自然科学关于存在之物的成果。因为关于认识可能性(关于认识可能的切合性)的自然的(前认识的)反思将我们置于认识论的混乱之中,这种认识论的混乱不仅产生关于认识的本质的错误见解,而且产生本末倒置的见解,这种见解使自然科学中对被认识的存在的解释自相矛盾。对同一个自然科学,从唯物论、唯灵论、二元论、心里一元论、实证论等等意义上解释都根据反思结果中各自认为是必要的解释而定。只有认识论的反思才对自然科学和哲学作了区分。只是通过认识论的反思才发现,自然的存在科学不是最终的存在科学。需要有一门绝对意义上的关于存在之物的科学。这门被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科学,是从对个别科学中的自然认识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其基础是在一般的认识批判中所获得的关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对象的及其各种基本形态的本质了解,这些基本形态是指认识和认识对象之间各种基本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认识批判的形而上学的目的,而是纯粹地坚持它的阐明认识和认识对象之本质的任务,那么它就是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现象学,这就构成现象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部分。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当代哲学,都认为一切科学,包括哲学,只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方法,这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这种信念完全符合十七世纪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信念认为,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确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与这种方法上的等同联系的还有对哲学与其他学科内容上的等同,当今人们还得把下列观点看作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哲学,确切些说,最高的存在——科学学说不仅与所有其他科学有关,而且也建立在它们的成果的基础上,就像科学是互为基础的一样,一些科学的成果可能作为另一些科学的前提。我想到了在认识心理学和生物学中所流行的对认识论的论证。在我们的时代,反对这种灾难性的先入之见的情形是大量存在的。这些确实是先入之见。在自然的研究领域中,一门科学完全可以把自己建立在另一门科学之上,并且一门科学可以作为另外一门科学方法上的楷模,尽管它们的楷模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各自研究领域性质的规定和限制。但哲学却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和任何“自然的”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由此得出,赋予自然科学以统一性的逻辑操作方式运用一切变通于各科学之间的特殊方法,因而具有一种统一性、原则性的特征,方法论的操作方式,作为一种原则上具有新统一性的哲学,把这种特征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再由此得出,在全部认识批判和“批判的”\n学科之中的纯粹哲学必须漠视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尚未科学地组织的自然智慧和知识中所进行的思维工作,并且不能对它作丝毫运作。我们先通过下列论述来进一步了解这门学说,在后面将对它进行更进一步的论证和阐述。在必然产生认识批判的反思(我指的是最初的、在科学认识批判之前的以及在自然思维方式中进行的那种反思)的怀疑主义的传播,任何自然科学和任何自然方法都不再作为一种可运用的财富。因为一般认识的客观切合性根据意义和可能性已完全变得神秘进而受到怀疑,而且,精确认识的神秘性并不比非精确认识的神秘性更少,科学认识的神秘性也并不比前科学认识的神秘性更少。认识的可能性,确切些说,认识如何能够切中在自身中存在的客观性本身的可能性成为疑问。而在这后面还隐含着:认识的功效,它的有效性的或合理要求的意义,对有效认识与纯虚妄认识之间区别的意义都成为疑问;同样,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对象就是它所存在的那个存在,无论这对象是被认识的还是未被认识的,它本身还是那样存在着并且它作为对象仍然是可能的认识对象,它的意义原则上是可认识的,并且即使它事实上永远不会被认识,和永远不能被认识,它的意义原则上还是可感知的、可想象的、并且在可能的判断思维中是可以通过谓词被规定的等等。但我们看不出,运用从自然认识中产生的、并在这些认识中被如此“精确论证了”前提会对解除我们认识批判的顾虑,回答认识批判的问题有何帮组。如果自然认识的意义和价值成为问题,完全是由于它所有方法的措施和所有精神论证的话,那么任何被规定为自然认识领域的出发点的公理和任何所谓精确论证的方法也就成为问题。最严密的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在这里都不比日常经验的某种真实的或所谓的认识具有丝毫优越性。因而很明显,根本谈不上哲学(它从认识批判开始并且它的一切都植根于认识批判之中)在方法上(甚或在内容上)要向精密科学看齐,根本谈不上哲学必须把精密科学的方法当作楷模,也根本谈不上哲学因当根据一种原则上在所有科学中同一的方法论继续进行在精密科学中所进行的工作,并且完成这些工作。我重申,哲学出于一种相对于所有自然科学来说的新尺度中,虽然这种新尺度(如这个词所形象地说明的)与旧尺度可能有着本质的联系,但它符合于一种从根本上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和“自然的”方法是对立的。谁否认这点,谁就没有理解认识批判所特有的全部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理解,哲学究竟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及相对于所有自然认识和科学,赋予哲学怎样的特性和合理性。第二讲认识批判的开端:对所有知识的置疑——根据笛卡儿的怀疑考察获得绝对确定的基地——绝对被给予性领域——重复和补充;对否定认识批判可能性的论据的反驳——自然认识之谜:超越——对内在和超越两个概念的区分——认识批判的第一个问题: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认识论还原的法则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现在的问题在于,认识批判如何能够确立自己?如果认识批判是在正确理解之中的认识,那么它就要以科学的自明性科学认识的,并由此客观化地确定,认识按其本质是什么,认识与被规定给它地对象之间关系地意义是什么,对象的有效性或切合性的意义又是什么。认识批判所必须进行的中止判断(εποχη\n)不可能具有如下意义,即:它不仅在开始时,而且自始至终在对任何认识,也包括它自己的认识进行置疑,并使任何被给予性,也包括它自己所确定的被给予性无效。既然它不能把任何东西作为预定力为前提,那么它就必须提出某种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它不加考察地从别处取来地,而是它自己给予的,它自己把这种认识设定为第一性的认识。这种第一性的认识绝对不能包含任何认识具有神秘、疑问的性质,这最终会使我们陷于窘境,以至于我们只好说,一般认识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需要澄清的、根据它的要求来说令人怀疑的东西。用相关的方式表达:如果我们不能把存在作为预定的,因为,我们不理解,自在的、但却在认识中被认识的存在具有什么意义,那么就必须证明一种我们所必须承认的绝对被给予的和无疑的存在,这种被给予是指:它具有使任何问题都必然迎刃而解的那种明确性。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笛卡儿的怀疑考察。由于考虑到错误和假象的多种可能性,我也许会陷于这样一种怀疑主义的绝望中,以至于我最后只能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一切都是可疑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显然并不可能一切都可疑,因为在我做出一切对我都可疑这个判断的同时,我如此判断,是无疑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想坚持普遍怀疑就会导致背谬。而在任何一个怀疑的情况中,确定无疑的是,我在这样怀疑着。任何思维过程也是如此。无论我感知、想象、判断、推理,无论这些行为具有可靠性还是不具有可靠性,无论这些行为具有对象还是不具有对象,就知觉来说,我知觉这些或那些,这一点是绝对明晰和肯定的:就判断来说,我对这和对那作判断,这一点是绝对明晰和肯定的,如此等等。笛卡儿把这些考虑用于其他目的;但我们在这里可以通过适当改造来利用它们。如果我们提出关于认识本质的疑问,那么就会牵涉到对认识的切合性的怀疑和认识本身的状况,首先认识是一个杂多的存在领域的称号,这个领域可以绝对被给予我们并且必须以个别的方式绝对被给予。这样,我们真实进行着的思维的形态是被给予我们的,只要我们对它进行反思,纯直观地接受它和设定它。我可以以模糊的方式谈论认识、感知、想象、经验、判断、推理等等,如果我进行反思,那么这种模糊的“关于认识、经验、判断等等的谈论和意指”的现象当然只是被给予,并且也是绝对地被给予。这种模糊的现象就已经是那些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称为认识的那些东西中的一个。但我也可以现实地进行感知并且观察感知,我此后还可以在想象和回忆中使一个感知在我面前再现出来,并且在这种想象的被给予性中观察这感知。这样,我的谈论就不再是空泛的,我的意指和关于感知的想象的被给予性彷佛就在我眼前。对于任何智性的体验,对于任何思维形态和认识形态来说,都是如此。在这里我把直观反思的感知和想象并列在一起。按照笛卡儿的考察顺序则应当首先说明感知:与传统认识论的所谓内心感知在某种程度上相符合,感知显然是一个变动不定的概念。在进行任何智性的体验和任何一般体验的同时,它们可以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直观和把握的对象,并且在这种直观之中,它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它是作为一种存在之物,作为一个此物(Diesda)被给予的,而对这个此物的存在进行怀疑是根本无意义的。尽管我能够考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被给予性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并且我能够在继续反思的同时,使直观本身对我来说成为这样一种直观,在它之中,上述被给予性,或者说,上述存在方式构造着自身。但是,我此刻仍然在绝对的基础上,就是说:这个感知使,并且只要它持续着,就始终是一个绝对之物,一个此物,某个在自身之中存在的东西,它就是某种我能够把它作为最终标准进行测量的东西,它可以表示,并且在这里必然表示存在和被给予,当然至少表示那种通过“此物”来说明的存在方式和被给予方式。并且一切特殊的思维形态,只要它们是被给予的,就都是如此。但是所有这些特殊的思维形态在想象中也都能够是被给予性,它们能够“仿佛”\n在眼前一般出发,但却不是作为现实的现在性,作为现实进行着的感知、判断等等而出现的。即使这样,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被给予性,它们直观地出现在这里,它们不仅仅是在模糊的暗示中、在空泛的意指中谈论它们,我们还直观它们并且在直观它们的过程中能够直观到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构造、它们的内在特征,并且在纯粹的测量中将我们的谈论紧靠直观到的丰富的明晰性上去。但这里必须立即补充对本质概念和本质认识的探讨。我们暂且确定,可以从一开始就描述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并且,如果建立一门认识论的打算是可能的,那么这个领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事实上,关于认识的意义方面和本质方面的模糊性正需要一门关于认识的科学,这门关于认识的科学的意图就仅仅在于使认识获得本质的明晰性。它不想解释作为作为心理事实的认识,它不想研究认识产生和消失的自由条件以及认识在其生成和变化过程中所必然依据的自然规律:研究这些问题是自然科学的任务,即关于心理事实、关于进行体验的心理个体的体验的自然科学的任务。相反,认识批判是想揭示、澄清、阐明认识的本质和这本质所属的关于有效性的合理要求:换言之,使它们成为直接的自身被给予性。重复和补充。自然的认识在各门科学中获得始终富有成效的进展,这使它对自己的切合性确信不疑,它没有理由对认识可能性和被认识的对象的意义感到不安。然而,一旦针对认识与对象的相互关系进行反思(一方面在认识和认识行为;另一方面在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中也可能对认识的思想含义进行反思),那么困难,不利的情况,矛盾的、但却被误认为已得到论证的理论就出现了,它们迫使人们承认,认识的可能性就其切合性而言是一个谜。一门新的科学要在此产生:这就是认识批判,它要整顿这种混乱并且向我们揭示认识的本质。显然,形而上学这门绝对的和最终意义上的存在科学的可能性依赖于认识批判这门科学的成功。但这样一门关于认识的科学究竟如何才能完全确立起来呢?凡是使一门科学受到怀疑的东西,它都不可当作已经给予的基础来利用。但是,由于认识批判把一般认识的可能性,即就认识的切合性而言的可能性,设定为问题,因此一切认识就都是可疑的。只要认识批判开始进行,对它来说,任何认识就不能再作为被给予的认识。因而它不能从任何前科学的认识领域中接受任何东西,任何认识都具有可疑性的标记。没有被给予的认识作为开端,也就没有认识的发展。就是说认识批判根本就无从开始。这样一门科学根本就不可能有。我认为,这里有一点是正确的:在开端上任何认识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被当作已确定的认识。但如果认识批判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任何认识,那么它开始时可以自己给自己以认识,并且自然是认识批判不能进行论证和逻辑推导的认识,因为论证和推导需要有事先就必须被给予的直接认识;相反,它直接指出这些认识,这些认识具有以下性质:它绝对明晰无疑地排除任何对其可能性的怀疑,并且绝对不包含任何导致一切怀疑主义混乱的难解之谜。现在我指出笛卡儿的怀疑考察和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或者说绝对认识的范围,这种绝对认识是在思维的明证性的概念下被把握的。现在还应当进一步指出,这种认识的内在使它能够作为认识批判的第一出发点;此外,它借助这种内在摆脱了那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是产生所有怀疑主义窘境的根源;最后,内在是所有认识论的认识必不可少的特征,不仅仅是在开端上,而且任何时候向超越的领域的借贷,换言之,即任何把认识论建立在心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做法都是一种背谬(nonsens)。我还要做一补充:有如下表面的论证:由于认识论将一般认识看作是可疑的,因此认识论如何得以开始呢——任何开端的认识作为认识都是可疑的;并且如果所有认识对于认识论来说都是一个谜,那么认识论自己用以开端的第一个认识也是一个谜。我认为,这种表面的论证当然是一种虚假论证。这种虚假起因于此话模糊的一般性。一般认识是“可疑的”,这并不表明否定一般认识的存在(这会导致悖谬),而是说,认识包含着某种问题,例如:某个被归于它的切合性方面的成就是如何可能的,甚至我也许还会怀疑,它是否可能。即使我自己在怀疑,但是,由于能够指出使怀疑没有对象的那些认识,怀疑随即也就消失了,因此,我就有可能迈出第一步。其次,如果我以对一般认识的不理解作为开端,那么这种不理解在其模糊的一般性中当然也包括每一个认识。但这并不是说,我将来遇到的每一个认识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对我使不可理解的。在一个最初普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认识层次上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大谜,并且当我陷入一般性的窘境时,我会说:一般认识是一个谜,然而很快便表明,这个谜并不寓于某些其他的认识之中。我们将得知,情况确实如此。我说过,认识批判必须与之相连接的那些认识不能含有丝毫可疑性,不能含有任何使我们陷于认识论的混乱之中的东西和任何超越整个认识批判的东西。我们必须指出,这是符合思维领域的情况的。但为此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会给我们带来根本性的推动。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观察一下,什么东西如此神秘、什么东西使我们在关于认识可能性地最先的反思中陷于窘境,那么这便是认识的超越。所有自然的认识、前科学的、特别是科学的认识,都是超越的、客观化的认识;它将客体设定为存在着的,它要求在认识上切中事态,而这种事态在认识之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被给予的,并不“内在”于认识。如果进一步考察一下,那么超越显然具有双重意义。它或者可能是意指在认识行为中对认识对象的非实项含有,以至于“在真正意义上被给予”或者是“内在地被给予”\n被理解为实项地含有;认识行为、思维具有实项的因素,具有实项的构造性的因素,但思维所意指的、所感知的、所回忆的事物却只能作为体验,而不是实项地作为一个部分,作为真实地在其中存在着地东西在思维自身之中被发现。因而问题在于:体验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在这里,内在是指在认识体验中实项地内在。但还有另一种超越,它的对立面是完全另一种内在,即绝对的、明晰的被给予性,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这种排除任何有意义的怀疑的被给予的存在是指对被意指的对象本身的一种绝对直接的直观和把握,并且它构成明证性的确切概念,即被理解为直接的明证性。所有非明证的,虽然指向或设定对象,却不自身直观的认识都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超越。在这种认识中,我们超越了真实意义上的被给予之物,超越了可直接直观的把握的东西。这里的问题是:认识如何能够把某种在它之中不直接的和不真实地被给予的东西设定为存在着的?在进行更深刻的认识批判的考虑之前,这两种内在和超越是混杂在一起的。很明显,提出第一个关于实项的超越的可能性问题的人实际上把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对明证的被给予性领域的超越的可能性问题也掺杂在里面了。就是说他默默地假定:惟一真正可理解的、无疑的、绝对明证的被给予性是在认识行为中实项含有的因素的被给予性,因此对它来说被认识的对象中任何未被实项地包含的东西都是神秘的、成问题的。我们很快将得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无论人们现在是在这种、那种还是首先在多种意义上理解超越,它都是认识批判的起初的和主导的问题,它是一个谜,这个谜对自然认识来说是一块拦路石,而对于新的研究则是一种推动。开始时,人们可能会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是认识批判的任务,并借此给这门新学科划定第一个暂时的界限,而不是更普遍地将一般认识的本质问题看作认识批判的主题。如果在最初确立这门科学时这个谜都存在于此,那么就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哪些东西不能当作预先被给予的东西。就是说,超越之物不能作为预先被给予的东西来运作。如果我不理解认识切中其超越之物是如何可能的,那么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现在,科学地论证超越的存在对我丝毫没有帮助。因为所有间接论证都回归到直接论证上去,而直接的东西已经包含着谜。但也许有人会说: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一样,都包含着谜,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如何可能的”是可疑的,而“这是可能的”却是绝对肯定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世界的存在,怀疑论者的谎言受到他的实践的惩罚。那么好吧,我们用一个更有力、并且更广泛的论证来回答他。因为这不仅证明,人们在认识论的开端不能依赖自然的和超越地客观化的一般科学,而且也证明在认识论的整个进程中也不能依赖这种科学。因而它证明了一个基本的命题;认识论从来不能并且永远不能建立在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于是我们要问:我们的对手想用他的超越的知识来做什么呢?我们把客观科学所储存的所有的超越的真理都交给他自由使用,并且推测这些真理的真实性价值并不因为以产生的超越科学如何可能这个谜而受到改变。他想用这些包罗万象的知识来做什么呢?他想怎样从“这是可能的”过渡到“如何可能的”上去呢?他的知识作为事实——这一事实即:超越的认识是真实的——向他保证,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在逻辑上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谜是:超越的认识如何可能。他能够在所有科学假设的基础上,在所有的认识、甚至包括超越的认识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考虑一下:他还缺少什么?对他来说,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只是以分析的方式显而易见,于是他说,我具有关于超越之物的知识。他缺少什么是很明显的。他不明白与超越之物的关系,他不明白人们归功于认识和知识的那种“超越的切中”。他的明晰性在哪里,是怎样的?但愿这种关系的本质在某处被给予他,这样他就能够直观到这些,认识和认识客体的统一性(切合性一词正暗示着这种统一性)就在他自己眼前,因而他不仅具有关于这种统一性的可能性的知识,而且在这统一性的明晰被给予性中把握这种可能性。可能性本身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超越之物,是一种被知道的、但却不是自身被给予的、被直观到的可能性。他的想法显然是:认识是一种不同于认识客体的东西;认识是被给予的,而认识客体不是被给予的;但认识却应当与客体有关,应当去认识客体。我如何才能理解这种可能性呢?回答显然是:只有关系本身作为一种可直观的东西被给予,我才能够理解这种可能性。如果客体是并且始终是一种超越之物,而且如果认识和客体确实不一致,那么他在这里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并且他以某种方式、完全通过对超越隐含的假设的推论使自己得以明白的这种希望,显然也是一件愚蠢之举。有了这些想法,他就必须理所当然地坚决放弃他的出发点:他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超越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他有关的所谓知识只是先入之见。这样,问题就不再是超越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而把超越的效力归于认识的这种先入之见如何解释自己:这恰恰是休谟的道路。但我们不考虑这些,我们对如下这个基本思想做补充说明,这一基本思想就是:“如何可能”\n的问题(超越的认识如何可能,甚至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一般认识如何可能)永远不可能根据关于超越之物的预先被给予的知识以及对此预先被给予的公理得以解决,哪怕它是产生于精密科学之中的公理;对这个思想,我们的补充说明如下:一个天生的聋子知道,有声音存在,并且声音形成和谐,并且在这种和谐中建立了一门神圣的艺术;但他不能够理解,声音如何做这件事,声音的艺术作品如何可能。他也不能想象同一类东西,即:他不能直观它们,并且不能在直观中把握“如何可能”。他的关于存在的知识对他毫无帮助,并且如果他想根据他的知识对声音艺术的“如何可能”进行演绎,通过对他的知识的推理弄清声音艺术的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对只是被知道,而不是被直观到的存在进行演绎,这是行不通的。直观不能论证或演绎。企图通过对一种非直觉知识的逻辑推理来阐明可能性(而是直接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一种背谬。我完全可以肯定,有超越的世界存在,可以把所有自然科学的全部内容看作有效的;但我不能借用它们。我永远不能奢望借助超越的假设和科学的结论达到我在认识批判中想达到的目的:即观察到超越认识的客观性的可能性。并且这显然不仅对知识批判的开端,而且对认识批判的所有进程都有效,只要它还停留在对认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阐述上。并且,这显然不仅对超越的客观性问题有效,而且对任何可能性的阐述都有效。每当人们进行超越的思维,并且在这种思维的基础上确立一种判断时,人们总是极其强烈的倾向于在超越的意义上作判断并因此陷入“向另一个人类的超越”之中,如果我们把上述结论与这种强烈的倾向性相联系,那么,对认识论法则的全面而又充分的演绎就形成了:在任何认识论的研究过程中,对各种认识类型都必须进行认识论的还原,即:将所有有关的超越都贴上排除的标记,或贴上无关紧要的标记、认识论上的无效性的标记,贴上这样一个标记,这个标记表明:所有这些超越的存在,无论我是否相信它,都与我无关,这里不是对超越的存在做判断的地方,它根本不被涉及。认识论所有的基本错误——一方面是心理主义的,另一方面是人本主义和生物主义的——都与所说的超越有关。它的影响极其危险,因为它使问题的本来意义永远都不得明白并且在超越中消失,一方面也是由于,连阐明这一点的人要想始终有效地保持这种明晰性也十分困难,而他却非常容易在漫思遥想中重新受到自然的思维和判断方式的诱惑,陷入到所有以这种思维和判断方式为基础而形成的错误的和诱人的问题之中。第三讲认识论还原的实行:排除一切超越之物——研究课题:纯粹的现象——绝对的现象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不可能局限于个别的被给予性;现象学的认识作为本质认识——“先验”\n概念的两种含义。根据以上阐述已经仔细地、可靠地证实了,哪些东西可以供认识批判利用,哪些东西不能利用。尽管只是根据认识批判地可能性,它的谜是超越,但是超越之物的现实仍然永远不能列入考虑的范围。显然,可利用的对象的领域,或者说,可利用的认识、可作为有效认识的出现,并且能够仍然不受认识论的无效性符号制约的认识的领域,并不能缩限为零。我们已经确定了诸思维的全部领域。思维的在,确切些说,认识现象本身,是无疑的,并且它不具有超越之谜。这些存在在认识问题的开端已经被设定了,如果不仅超越之物、而且认识本身也被放弃的话,那么超越之物如何能进入认识这个问题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同样明白的是,诸思维表现着一个绝对内在的被给予性领域,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明内在。在对纯粹现象的直观中,对象不在认识之外,不在“意识”之外并且同时是在一个纯粹被直观之物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意义上被给予。但这里需要通过认识论的还原来保证,在这里,我们想首先具体地(inconcreto)探讨这个还原方法上的本质。在这里我们需要还原,为的是使思维的在的明证性不至于和我的思维是存在的那种明证性,我思维地存在着地(sumcogitans)那种明证性等等相混淆。必须防止把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现象与心理学现象,即自然科学心理学的客体相混淆。如果我作为一个自然思维的人观察我正在体验的感知,那么我立即会、并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这是事实)会将它统摄于与我的自我的关系中,它在这里是作为这个体验着的人的体验,作为他的状态,作为他的行为,而感觉内容则作为对它来说在内容上的被给予之物,被感觉之物,被意识之物,并且和他一同排列在客观时间之中。感知,甚至思维就是这样被统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事实。作为日期被统摄在客观时间中,这属于体验着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时间之中并且延续着它的时间(一种通过经验的时间测量学方法得以测量时间)。这就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心理学。这种意义上的现象不受我们在认识批判中所必须遵循的那种规矩、那种就有所超越之物中止判断的规律的制约。作为人、作为世界之物的自我,以及作为这个人的体验的体验被列入客观时间中——尽管这是完全不确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超越并且在认识论来说是零。只有通过还原,我们也想把她叫做现象学的还原,我才能获得一种绝对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给予性。如果我对自我、世界和自我体验本身提出怀疑的,那么在有关体验的统摄中对被给予之物、对我的自我的简单直观的反思,就产生了这个统摄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被理解为我的感知的感知”。当然,我可以用自然的考察方式将这个现象重新与我的自我相联系,把它设定为经验意义上的自我,这时我又要说:我具有这种现象,它是我的现象。这样,为了获得纯粹现象我就不得不重新对自我以及时间、世界提出怀疑,并且列出一个纯粹的现象——纯粹思维。但是我也可以在我感知的同时纯直观的观察感知,观察它本身如何存在,并且不考虑与自我的关系,或者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那么这个被直观地把握的和限定的感知就是一种绝对的、摆脱了任何超越的感知,它就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被给予。任何心理体验在现象学还原的道路上都与一个纯粹现象相符合,这个现象指出,这个体验的内在本质(个别地看)是绝对的被给予性。所有关于一种“非内在的现实”\n,即尽管在现象中被意指,但没有被包含在现象中的,同时又不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被给予的现实的设定都是被排除的,就是说,被悬置的。如果存在着把诸纯粹现象变成研究客体的可能性,那么很明显,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处于心理学这门自然的、超越地客观化的科学之中了。这时我们便不研究,并且不谈论心理学的现象,不谈论所谓实体现实的某些确定的事件(实体现实的存在始终是可能的),而是谈论那些存在着的和起效用的东西,而不管有没有诸如客观现实的东西,不管对这种超越的设定是否合力。我们谈论的正是这样一些绝对被给予性;尽管这些被给予性也意向地关系到客观现实,这种反身关系也只是这些被给予性中地某一个特征,而对现实的存在和非存在却不会作出任何预先的判断。这样我们就已经在现象学之滨抛了锚,它的对象被设定为存在着的,正如科学设定它的研究客体一样,但现象学的对象并不被设定为一个自我之中,一个时间性的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被设定为在纯粹内在的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予性:纯粹的内在之物在这里首先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而得到描述:我意指的是此物,不是某东西超越地意指它,而是某东西在自身之中地它,它是作为某东西被给予地。当然,这些说明仅仅是迂回地辅助方法,借以说明超越的客体的虚假被给予性与现象学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区别,从而看到这里可以看到的最主要的东西。现在,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这块新大陆上站稳脚跟,不至于在它的岸边绊倒,我们必须迈出新的步伐,进行新的思考。因为在这段海岸边藏着暗礁,暗礁上阴霾云集,它以怀疑主义的风暴威胁着我们。我们至此为止所说的话,涉及到所有现象,当然为了理性批判的目的我们只是对认识现象发生兴趣。但是我们现在将要阐明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针对所有现象的,如果对这句话做些必要的修正,那么就是说,无论什么变化,无论何种层次,它对所有现象都是有效的。我们建立一门认识批判的意图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开端,走向一个我们可以支配的被给予性的坚实陆地,并且我们好像首先需要它们:为了阐明认识的本质,我当然必须把所有可疑形态中的认识作为被给予性来拥有,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拥有,即:这种被给予性自身丝毫不带有别的认识(尽管这认识似乎提供了被给予性)所带有的那些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纯粹认识的地盘,现在我们可以研究它并且确立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现象学。这门现象学难道不是自明地必定成为解决那些使我们动摇的问题的基础吗?但是很明显,只有当我自己观察到了认识,并且只有当它在直观中把本来的面目给予我,我才能使认识的本质得以明晰。我必须内在地并且纯直观地在纯粹现象中、在纯粹“意识”\n中研究它:它的超越是可疑的;只要它是超越的,那么它与之发生联系的对象的在对我来说就不是被给予的,令人可疑的正在于:它如何能够尽管如此仍然被设定呢,并且,如果这种设定是可能的话,那么它还有、以及它还能够有什么意义呢!另一方面,尽管我根据其切合性而将超越之物的存在看作可疑的,但这种与超越之物的联系在纯粹现象中却仍具有某种可把握的东西。这种与超越之物的关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它的意指仍然是现象的内在特征。甚至问题似乎仅取决于一门关于绝对的诸思维的科学。我必须接触到被意指的超越之物的已确定性,因此我不仅研究这种超越自身的意指的意义,而且在研究它的意义的同时,研究它的可能的有效性,或有效性的意义,并且这个研究只能在这个意义绝对被给予时,只能在有效性的意义在关系、证明、证实的纯粹现象中成为绝对被给予性时进行,除此之外在什么时候我还能进行这种研究呢?当然,我们在这里立即会不知不觉地萌生怀疑:难道在行动中不是必然会有更多的东西出现吗?难道有效性的被给予性不正带有客体的被给予性吗?如果确实存在着某种有效性的超越,那么这种被给予性就不可能时思维的被给予性。但是,无论如何,一门被理解为思维的纯粹现象的科学始终是第一性的,这是必定的,并且它至少能够解决主要的问题。因而这里的目的在于现象学,这里是指作为纯粹认识现象的本质论的认识现象学。前景是美好的。但现象学应当如何开始呢?它是如何可能的呢?我应当判断,但应当客观有效地判断,科学地认识纯粹现象。所有科学不都是导致对自在存在着地客观性以及对超越之物地确定吗?科学地被确定之物存在着,自在地存在着,无论我在对它地认识过程中是否把它设定为存在着地,它都绝对被视为存在着的。在科学中被认识之物,科学地被论证之物地客观性难道不正是作为相关物而属于科学的本质吗?并且,科学地被论证之物难道不是普遍有效地吗?但这里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纯粹现象的领域中活动。但我为何说地盘,毋宁说它是现象汇成的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的河流。我在这里能作些什么陈述?我可以直观地说:这里的这个!这个在,是无疑的。我甚至可以说,这个现象作为部分包含着那个现象,或者与那个现象相联系,这个现象渗透到那个现象中等等。显然,这里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无关,这种判断没有“客观意义”,这种判断只具有“主观”真实性。我们在这里不想研究这种判断(就其“主观”真实的要求而言)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客观性。然而这里可以一目了然,由前科学的自然的判断所安排并由精密科学的有效判断进一步完善的那种客观性的威仪,这里更本没有。我们不会给这些由我们纯直观地做出的判断——此物在等等,附以特殊的价值。此外,你们在这里会想到康德对感知判断和经验判断的著名区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德缺乏现象学的和现象学还原等概念,他不能完全摆脱心理主义和人本主义,因此,他没有达到进行这种必要区分的最终目的。当然,被我们排除了,而先验统觉,一般意识对于我们来说将很快获得完全另一种意义,一种根本不神秘的意义。但我们仍要回到我们考察的主要方面去。现象学的判断作为特殊判断不会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但如何才能获得判断,即科学有效的判断呢?而“科学的”这个词立刻又使我们陷入窘境,我们要问,超越不正是随着客观性而出现的吗?并且随着超越还出现了如下的怀疑:这种客观性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否可能并且如何可能?通过认识论的还原我们排除了超越的前提,因为超越根据它可能的有效性和它的意义来看是可疑的。那么科学的确定,对认识论本身的超越的确还可能吗?在对超越的可能性进行论证之前,任何对认识论本身的超越的确定都是不允许的,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但如果认识论的中止判断要求——如它所表现的那样——,在我们论证超越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不能把任何超越看作有效的,并且如果对超越的可能性的论证本身以客观论证的形式要求超越的设定,那么这里似乎就出现了循环,它使现象学和认识论成为不可能;而迄今为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不会利科就对现象学,包括认识论批判在内的可能性感到绝望。我们现在需要前进一步,这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循环。从根本上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因为我们区分了双重的超越和内在。你们还记得,笛卡儿在确定了思维的明证性之后(或者毋宁说在确定了我们还没有引用过的“我思故我在”之后)问道:是什么在向我们保证这种根本的被给予性?是明白清楚的感知(claraetdistinctaperceptio)。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我不须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比笛卡儿更纯粹、更深刻地把握了这个事物,因此我们在更纯粹地意义上把握和理解了明证性和明白清楚的感知。我们可以随着笛卡儿再向前迈一步(经过必要的修正):所有像个别思维一样通过明白清楚的感知而被给予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利用。但我们不能再继续进行第三个沉思和第四个沉思,即:对上帝的证明以及向真实可信的东西(veracitas\ndei)等等的回复,否则显然会带来恶果。你们始终要保持怀疑的态度,或者毋宁说,批判的态度。我们承认纯粹思维的被给予性是绝对的,然而外部的感知中的外在事物的被给予性不是绝对的,尽管这种外部的感知认为事物本身具有再。事物的超越使我们对事物产生怀疑。我们不理解感知如何能切中超越之物;但是理解感知如何切中内在之物,即以反思的和纯粹内在的感知、被还原的感知的方式切中内在之物。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理解呢?我们直接地直观和直接地把握我们在直观和把握时所意指的东西。观察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所意指的是某种不在它自身中被给予的东西,并且怀疑这东西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它是存在着的,这是有意义的。但是,直观,并且仅仅意指在直观时把握到的东西,这是仍然对此提出疑问和怀疑,就无意义了。从根本上这无非是说:如果直观、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真实的直观和真实的自身被给予性,而不是另一种实际上是指一个非给予之物的被给予性,那么直观和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就是最后的根据。这是绝对的自明性;非自明的东西、有问题的东西、甚至神秘的东西存在于超越的意指过程中,即存在于意指、信仰之中,甚至可能存在于对一种未被给予之物的烦琐论证中;虽然在此可以发现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即意指、信仰本身的被给予,但这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只须进行反思就可以发现它。但这个被给予之物并不是被意指之物。然而,难道绝对的自明性,直观的自身被给予性只存在于个别体验中和它的特殊因素部分中,就是说只是对“此物”\n的直观设定?难道不应当把另一些被给予性直观地设定为绝对的被给予性?例如把一般性设定为绝对被给予性,以至于一个一般之物直观地成为自明的被给予性,对这种被给予性的怀疑会在此导致背谬。我们以笛卡儿为依据所进行的全部明证性考察(这个考察肯定具有绝对的明晰性和自明性)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对现象学个别的思维被给予性的限制是多么奇怪。就是说,对于思维和我们正在体验的感觉的个别情况,我们也许能够说:这是被给予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贸然说出如下这个最一般的公理:一个被还原的一般现象的被给予性是一个绝对无疑的被给予性。但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你们引路。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明显的,即:认识批判的可能性除了依赖还原了的诸思维之外,还依赖于对其他绝对被给予性的指明。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在对诸思维进行预先规定的判断时已经逾越了诸思维,当我们说,这个判断现象以这个和那个想象现象为基础,这个感知现象包括这个和那个因素、颜色内容等等,这时我们已经超越了它们。并且,即是我们设定性地在对思维被给予性地最纯粹测量中做出这些陈述,我们已经带着反映在语言表达中地逻辑形式超越了纯粹思维。并且,尽管随着谓词地思维会有新思维加入到我们所陈述地那些思维中去,但这些新思维仍然不会构成谓词的事态,不会构成陈述的对象。至少对于那些能够站在纯粹直观的角度并拒斥所有自然成见的人来说,这样一种认识是较容易把握的,即:不仅个别性,而且一般性、一般对象和一般事态都能够达到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这个认识对于现象学的可能性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象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在纯粹直观的考察范围内、在绝对被给予性的范围内的本质分析和本质研究。这必然是它的特征:它想成为一门科学和一种方法,目的是阐明可能性,认识的可能性,评价的可能性,从它们的本质根据出发来阐明它们;因为存在着普遍怀疑的可能性,所以现象学的研究是普遍的本质研究。本质分析是具有源初根据的总分析,本质认识是针对本质、针对实质(Essenz),针对一般对象的认识。现在也可以合法地谈论先天了。至少,假如我们排除了关于被经验歪曲了的先天概念,那么,先天认识的含义无非是指一种纯粹针对总的实质的、纯粹从本质中汲取其有效性的认识,此外它还能有什么别的含义呢?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合理的先天概念。如果我们把先天理解为所有那些作为范畴具有一定意义上原则性含义的概念,并进一步理解为建立在这些概念中的本质规律,那么就产生了关于先天的另一种概念。如果我们在这里坚持关于先天的第一种概念,那么现象学就在原初的、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内与先天有关,与在总的直观中把握的种类、与先天的事态有关,这些事态在这些绝对被给予性的基础上可直接直观地构造自身。对理性(不仅理论理性,而且实践理性,以及任何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显然都在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先天,在于确定自身给予的那种原则形式和事态及借助这种自身被给予性实现、利用和评价随同对原则性含义的要求一起出现的逻辑学的、伦理学的、价值学说的概念和规律。第四讲通过意向性扩展研究范围——一般之物的自身被给予性;进行本质分析的哲学方法——对明证性的感觉论的批判;明证性作为自身被给予性——不局限于实项的内在范围;课题:所有的自身被给予性。如果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仅仅是认识的现象学,那么,我们所涉及的便是通过直接直观可指明的认识本质,即:一种直观的、在现象学还原的和现象学自身被给予的范围内进行的指明以及对“认识”这个广义的名称所班汉的杂多性质的现象做分析的区别。因而问题便是,本质地存在于和建立于这些现象之中的是什么,它们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哪些复合的可能性为它们奠定了本质的和纯粹内在的基础,哪些总的一般联系在这里喷涌而出。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实项的内在之物,而且也涉及在意向意义上的内在之物。认识体验具有一种意向(intentio),这属于认识体验的本质,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尽管对象不属于认识体验,但与对象发生的关系却属于认识体验。对象能显现出来,它能在显现种具有某种被给予性,但尽管如此它既不是实项地存在于认识现象之中,也不是作为思维(cogitatio)而存在。要澄清认识的本质并使属于认识的本质联系成为自身被给予性,就要从这两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属于认识本质的这个关系。这里确实存在着谜、奥秘和问题,这就是:认识对象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果认识是判断的认识,那么它的切合性或非切合性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果认识是明证的认识,那么它的相应性(Adaequation)的最终意义又是什么,等等。无论如何,全部这些本质研究事实上显然是总体的研究。在意识流中出现和消失的个别认识现象不是现象学确定的客体。这里的目的是在于“认识的来源”\n,在于可总体观察的起源,在于体现着一般基础尺度的总体的绝对的被给予性,按照这些尺度,可以衡量哪些混乱的思维的所有意义和公理,并且可以解答所有这思维置于它的对象之中的谜。但是一般性,一般本质和属于它们的一般事态果真能像思维那样在相同的意义上达到自身被给予性吗?难道一般本身不正超越了认识吗?作为绝对现象的一般认识当然是被给予的;但在认识之中,我们要想寻找一般之物是徒劳的,这种一般之物在对一样的内在内容的无数的、可能的认识中应当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之物。正如我们已经回答的那样,我们现在当然还要回答:这个超越当然具有一般之物。认识现象的和这种现象学个别性的任何实项部分,重又是一个个别性,这样,本身不是个别性的一般之物就不能实项地包含在一般性意识之中。但是,对这种超越的厌恶无非是一种先入之见,它产生的原因是没有从认识的起源本身来适当地考察认识。同样必须弄清楚的是,绝对现象和被还原的思维对我们来说之所以成为绝对的被给予性,不是因为它是个别性,而是因为它在现象学的还原之后在纯粹直观中仍然作为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表现出来。但我们能够纯粹直观地发现,一般性也不缺少这种绝对的被给予性。确实如此吗?我们看一下一般之物的被给予性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纯粹内在的一般性意识根据被观察的和自身被给予性的个别性构造自身。关于红,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我除去红此外还含有的、作为能够超越地被统摄的东西,如我的桌子上的一张吸墨纸的红等等;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红和种类的(in\nspecie)红的思想的意义,即从这个红或那个红中直观出的同一的一般之物;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一般的红。如果我们确实纯粹直观地这样做了,那么可以理解,我们那可能还会怀疑,什么是一般的红,它意指的是什么,按照它的本质它可能是什么?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红的性质。就是一种神性、一种无穷的智慧,除了总的直观这一切之外,能够得到更多的红的本质吗?如果我们给予两种红的种类,两种红的程度,那么我们难道不能判断,这种红和那种红是相似的,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红的现象,而是指红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不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吗?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在心理学主体中的抽象行为和进行这种抽象的心理学条件。这里谈的是红的总本质或红的意义以及在总的直观中红的被给予性。如果人们在对红的直观和在对红的特殊性质的把握过程中用红这个词恰恰是指被直观、被把握的东西的话,那么现在再追问和怀疑,什么是红的本质,或什么是红的意义就没有必要了;与此相同,如果人们在纯直观的和纯本质直观的考察中,在现象学还原的范围内看到了有关的典型现象并且给予了有关的性质,那么在涉及认识本质和认识的主要形态的过程中再怀疑它们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只是认识显然不是像红这样一种简单的事物,必须对认识的杂多形式和种类进行区分,不仅如此,还必须在它们之间的相互本质联系中对它们进行研究。因为,理解认识,这就是说,要总的澄清认识的目的论关系,这些关系的结果便是智慧形式的各种本质类型的某种本质关系。同时,对认识的理解还包括对原则的最终阐明,这些法则作为科学客观性的可能性的观念条件支配着所有作为规范的经验科学的过程。对阐明法则的全部研究完全是在本质领域中进行的,这个本质领域又以现象学还原的单一现象为基础而构造起来。分析在每一步上都是对构造于直接直观中的总事态的本质分析和研究。因而全部的研究都是先天性的;当然它不是一种在数学演绎意义上的先天性研究。讲它与客观化的先天科学区分开来,是它的方法和它的目的。现象学的操作方法是直观阐明的、确定着意义和区分着意义的。它比较,它区别,它连接,它进行联系,分割为部分,或者去除一些因素。但一切都在直观中进行。它不会理论化和数学化;就是说,在演绎理论的意义上它不作解释。一旦它对作为统治着客观化科学可能性的哪些原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理进行阐明(但最终也把它自己的基本概念和法则作为反思的阐明的对象),那么它就结束了,客观化的科学便从这里开始。因而它是完全另一种意义上的科学并且具有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完全不同的方法。在现象学最严格的还原之中的直观和本质直观是它的惟一所有的东西,这种方法本质上属于认识批判的意义,因而也属于所有的理性批判(即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就这点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但是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批判之外还有被称为哲学的东西,这种哲学所涉及的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因而是最广义理解的一般形而上学。在直观的这些情况中,人们谈及明证性,并且,实际上唯独知道确切的明证性概念并根据其本质来确定它的哪些人才看到这类情况。根本性的东西在于,不要忽视,明证性实际上就是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相应地自身把握的意识,它无非意味着相应的自身被给予性。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者谈了许多研究起源的价值,而同时却和最极端的理性主义一样远离真正的起源,他们想让我们相信,明证的判断和不明证的判断的全部区别在于某种感觉,通过这种感觉,明证的判断便显示出来。但是在这里,感觉能说明什么呢?它应当做什么呢?难道它应当向我们呼唤:停住!这里在这里吗?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相信它呢?为什么这种相信重又必须具有一种感觉的标记呢?而为什么对二乘二等于五的意义判断即从不具有这种感觉的标记呢?为什么它就不能具有这种标记呢?究竟怎样才能理解这种感觉的标志呢?现在人们对自己说:从逻辑上说,同一个判断,如二乘二等于四的判断对我来说可以有时明证,有时不明证,四这个数的同一概念对我来说这次可以是直觉地在明证性中被给予,而另一次只是在符号地想象中被给予。因而从内容上来说,两方面是同一现象,但其中一方面具有价值上地优越,具有赋予价值的特征,具有突出的感觉。难道我实际上在两方面具有同一个东西,只是这一次附加了一种感觉,而另一次则没有?如果人们观察一下现象,那么很快就发现,实际上同一现象并不会两次出现,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现象,它们只是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我看到二乘二等于四,并且我在模糊的符号判断中说出来,那么我意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并不是说:具有同一现象。从两方面来看,内容是不同的,这一次我直观,并且事态本身在直观中被给予,另一次我具有符号性的意指。这一次我具有直观,而另一次我具有空洞的意向。因而区别是否在于,存在着一种两方面共同的东西,存在着相同的“意义”\n,一次是附有感觉标记,另一次却没有呢?但人们只是观察现象本身,以取代自上而下地去谈论它们和构造它们。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有一次在生动的直观中具有红,并且另一次在符号性的空洞意向中想到红,那么是否这两次同一个红的现象都是实项当下的,只是一次附有红的感觉而另一次没有这种感觉呢?人们只须观察一下这些现象就会认识到,它们完全不是这样,它们那只有通过两方面被视为同一的东西(我们叫做意义)才得到统一。但是,区分是否存在于现象本身之中呢?是否还需要用一种感觉来进行呢?并且,区别难道不正在于,在一种情况中,存在着红的自身被给予性,存在着数的和总数相等性的自身被给予性,或者,存在着在主观表达中相应直观的把握和对这些事物的自身具有,而另一次只存在着对这些事物的意指吗?因而我们对这种充满感觉的明证性并不能满意。只有当它在纯粹直观中指明自己,并且这种纯粹直观的含义是指我们所期望的直观以及和这种明证性本身相矛盾的直观时,这种明证性本身才是合理的。利用明证性的概念,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关于思维在我们具有明证性,并且,因为我们具有明证性,所以它不包含谜,也不包含超越的谜,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我们可以支配的无疑的东西。关于一般之物我们的明证性也不更少,一般对象和事态对我们来说成为自身被给予性,并且它们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无疑地被给予的;同样在严格意义上相应地自身被给予。据此,现象学还原的含义并不是指将研究限制于实项的内在领域内,限制于在绝对思维的这个(Dies)之中实项地包含之物的领域内,它的含义根本不是指限制在思维领域内,而是指限制在纯粹自身被给予性的领域内,限制在那些不仅被讨论、不仅被意指之物的领域内;它的含义也不是指限制在那些被感知之物的领域,而是指限制在那些完全在其被意指的意义上被给予之物和在最严格意义上自身被给予之物的领域内,以至于被在意指之物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被给予的。一言以蔽之,限制在纯粹明证性的领域内,但明证性这个词要在某种严格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意义排除任何“间接的明证性”,尤其排除所有不严格意义上的明证性。绝对被给予性是最终的东西。当然人们可以轻易地声称他具有某些绝对被给予之物,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绝对的被给予性也可能被模糊地讨论并且也可能在绝对被给予性中被给予。正如我能够直观红的现象,并且仅仅无直观地谈论它一样,我也可以谈论对红的直观并直观红的直观本身,借此把握对红的直观本身。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自身被给予性,这意味着否定所有最终的规范,否定所有给认识以意义的基本标准。然后人们就不得不把一切都宣布为假象,并且以背谬的方式将假象本身也宣布为假象,因而完全陷入怀疑主义的背谬性之中。但是不言而喻,只有那些看到了原因,保留了看、直观、明证性的意义的人才能以这种方式提出反怀疑主义者的论据。对那些没看或者不愿看的人,对那些谈论着并且自己提出论据,但始终处于接受所有矛盾,同时又否认所有矛盾的人,我们毫无办法。我们不能回答:“显然”是这样,他否认有诸如“显然”这样的东西;就像一个不在看的人想否认看的行为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一个在看的人想否认他自己在看和否认有看的行为一样。假如他不具有另一种感官,我们怎么能使他信服呢?关于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我们已经知道,它并不是表示实项的单一性,即思维的绝对个别性的自身被给予性。如果我们把握住这种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那么问题就在于,它能够达到多远,它在什么程度上或在什么意义上与诸思维的领域和对诸思维进行概括的一般性领域相联接。如果人们抛弃了最初明显的先入之见,即认为在个别的思维中和在实项内在的领域中包含着唯一绝对的被给予之物,那么现在也必须抛弃后来的、并且同样是明显的先入之见,即认为只有在那些从实项内在的领域中产生的总直观中才能生长出新的自身被给予的对象。“我们在反思的知觉中绝对被给予地具有诸思维,同时我们有意识地体验它们。”人们想这样开始,然后我们能够去直观在诸思维中和在诸思维的实项因素中个别化的一般之物,在直观抽象中把握一般性,并且把纯粹建立在这些一般性中的本质联系在直观联系的思维中构造为自身被给予的事态。这便是一切。然而,对于原初的、绝对被给予性的直观认识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倾向更危险了,即:过多地产生思想,并且从这些思维反思中提取出被误认的自明性。自明性大多根本不能被明确地表述,因此它们不受任何直观的批判,自明性更易暗下规定并擅自限定了研究的方向。直观的认识是这样一种理性,它打算将知性也变成理性。知性在这里不容置喙,不能将它未兑现的空头支票混入已兑现的支票中。而在这里我们对知性以纯粹国库券为根据的兑换和换算方法并不提出疑问。因此,知性要尽可能少,但直观要尽可能纯[无知性的直观(intuitiosine\ncomprehensione)];实际上我们想起了神秘主义者的话,他们描述了智慧直观,这种直观不是知性知识。而全部艺术在于,把直观的眼睛纯粹盯住这个词,并且排除这些与直观混杂在一起的超越的意指,排除这些被误认的共同被给予之物、共同被思维之物,以及有可能的话排除由附加的反思强加于其中的解释。固定不变的问题是:这种被意指之物是否在真正的意义上被给予,是否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被直观和被把握,或者,这种意指是否超出了被意指之物?假定了这一点,我们便很快认识到,以为直观的研究在一种所谓内心感知的领域内以及一种以此内心感知为基础的纯粹内在的、对它的现象和现象-因素进行本质直观抽象的领域内进行,这实是一种臆想。有各种各样的对象的方式(Modi),以及所谓被给予性的方式,也许在所谓“内心感知”意义上的存在之物的被给予性以及自然的和客观化的科学的存在之物的被给予性只是这许多被给予性的一种,而其他的被给予性尽管被标志为非存在之物,但仍然也是被给予性,只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它们才是被给予性,即:它们与其他那些被给予性相对立并且在明证性中能够与前者区别开来。第五讲时间意识的构造——本质把握作为实质的明证被给予性;个别实质和一般意识的构造——范畴的被给予性——符号性地被想象之物作为本身——研究领域的最广范围:认识中对象的各种构造方式;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我们确定了思维的明证性,而后进一步承认了一般之物的明证的被给予性,那么这个步骤会立即导致下一个步骤。在感知颜色并同时进行还原时,我获得颜色这个纯粹现象。如果我现在进行纯粹的抽象,那么我就获得现象学的一般颜色这个本质。但如果我具有明晰的想象,那么我也不完全获得这种本质吗?而谈到回忆,它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它提供了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所以人们能够指出所谓原初的回忆,指出与任何感知必然交织在一起的保留。我们现在正在体验着的体验,在直接的反思中成为我们的对象,并且在这种体验中所展现的始终是同一个对象之物:同一声音刚才还是作为真实的现在(Jetzt),眼下仍是这一声音,但它回到了过去并同时构造着同一个观点的时间点。如果声音不停止,而是持续着,并且在它的持续过程中从内容上展示为同一的或者从内容上展示为变化的,那么这里不正是可以证明地(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它在持续或在变化吗?并且这不有说明,直观超出了纯粹的现在点,即:它能够意向地在新的现在中确定已经不是现在存在着的东西,并且以明证的被给予性的方式确认一截过去吗?并且,这里重又区分出:一方面是当时地对象之物,它现在存在并且过去存在,它持续着和变化着;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当下现象和过去现象,持续现象和变化现象,这现象在当时是一个现在,并且,在它包含着的细微差别中,在它自身经历着的不断变化中,它显然并展示了时间性的存在。对象之物不是现象的一个实在部分,在它的时间性中它具有某些在现象中根本找不到并且根本无法解释的东西,但它在现象中构造自身。它在其中展现出来并且在其中作为“存在着的”\n明证地被给予。再往下,至于本质被给予性,它不仅仅根据感知和交织在感知中的保留来构造自身,也即它的构造不仅是从现象本身获得一种一般之物;而且是将显现的对象一般化。根据显现的对象去设定一般性:例如,一般时间性内容,一般持续,一般变化。此外,它还可以将想象和回忆作为基础,它自己给予可纯粹把握的可能性;在同一意义上它也从这些行为中取得一般性,另一方面这种一般性却并非实项地包含在这些行为中。显然,一种完全明证的本质把握尽管回指到它必须在其基础上构造自身的个别直观,但并不因此回指到单一感知,这种单一感知所给予的典型的个别是一种实项的现在当下之物。无论本质直观的抽象是在一种感知的基础上进行还是在将想象当下化的基础上进行,关于现象学的音质、音度,关于色调,关于亮度等等的本质都是自身被给予的,并且,真实的和已修正了的存在的设定从两方面来说都无关紧要。这种情况也适合于那种与心理材料的真实意义上的种类有关的本质把握,如判断、肯定、否定、感知、推理等等。当然,此外它也适合于总的事态,这种事态属于这种一般性。在两种声音中,一种较低,一种较高,并且这种关系不可颠倒。对此的了解,是在直观中构成的。我们必定可以看到一些例子,但决非以感知的事态的方式看到这些例子。对于本质考察来说,感知和想象所处的地位是完全相同的,从两者中可以同样很好地直观出同一本质,抽象出同一本质,并且在其中织入的存在设定是无关紧要的;至于被感知的声音以及它的强度、它的质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存在,而想象的声音,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构的声音不存在;前者是明证地实项地当下,后者则不是;声音在重复回忆的情况中毋宁说是被设定为曾经存在并且在现在中被当下化了,而不是被设定为现在的;这些都属于另一种考察,对于本质考察来说,这些不是问题,除非它的意图在于揭示这种具有其被给予性的区别并且确定对这些区别的总的看法。此外很清楚,即使感知中的基本的例子是被给予的,这里也不考虑显示出感知被给予性的那种东西,即:存在。想象不仅对于本质考察来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感知,而且它似乎在自身之中也包含着单一的被给予性,并且是作为真实明证的被给予性。我们来看一下纯粹想象,把它看作不具有回忆设定的想象。一种想象的颜色并不是感觉颜色(Empfindungsfarbe)意义上的被给予性。我们将想象的颜色与对这颜色的想象体验区分开来。这颜色在我眼前的浮现(这是粗糙的表述)是一种现在,是一种现在存在的思维,颜色本身却不是现在存在的颜色,它并没有被感觉。另一方面,它却是在某种程度上被给予,它出现在我眼前。它也可以像感觉颜色那样通过排除所有超越的含义而被还原,因而对我来说它的含义并不是指纸张的颜色、房屋的颜色等等。所有经验的存在设定都能够被去除;尔后我根据我对它的“直观”,也可以说“体验”来看待它。但尽管如此,它仍然不是想象体验的一个实项的部分,它不是当下的,而是被当下化了的颜色,它仿佛就在眼前,却不是作为实项的当下。但归根结蒂,它是被直观的,并且,作为被直观之物,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给予的。因此我不能将它设定为物理的或心理的存在,我也不将它设定为一种真正思维意义上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是一种实项的现在,一种被给予性它具有明证性地被描述为现在被给予性。想象的颜色在这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不是被给予的,这并不表明,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被给予的。它显现并且自身显现,它自身显现出来,我在其当下化中对它自身进行直观的同时能够对它作出判断,对构造它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联系作出判断。当然,它们也是在同一意义上被给予的,并且,在不“真实”存在着的总的想象体验中,它们不是实项当下的,只是“被想象的”\n。纯粹的想象判断仅仅表达内容,表达显现之物的单一本质,它可以说:这个(3)是如此形成的,它包含着这些因素,它如此这般地改变自己,但想象判断对作为在真实时间中真实存在的存在,对真实的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和未来存在不作丝毫判断。因而我们能够说,对个体的实质而不是对存在作出的判断。正因为此,总的本质判断(我们习惯直接将它称为本质判断)就是不依赖于感知和想象之间的区别。感知设定存在,但也具有实质被设定为存在着的内容在当下化中可能是同一个内容。但是,存在和实质的对立并不表明:在这里,两种存在方式在两种自身被给予性的样式中表现出来并能够得以区分。在对一种颜色的纯粹想象中,将颜色设定为实践中的现实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判断,并且对于在想象的内容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被给予。但颜色显现出来,它在此,它是一个这个,它能成为一个判断的主体,并且是一个明证的判断主体。因而被给予性的一种样式在想象的直观中和在以其为基础的明证的判断中显现出来。当然我们仍然停留在个体单个的领域中,所以这类判断作用不大。只有我们构造总的本质判断时,我们才获得牢靠的、科学所要求的那种客观性。但现在问题不在于此。这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洪大的激流之中。开端曾经是思维的明证性。在这里我们首先觉得我们好像有了坚实的基地,即纯而又纯的存在。人们在这里似乎只须着手去做,去直观。根据这种被给予性,人们可以去比较和区别,人们可以展示特殊的一般性并且因此获得本质判断,以上这些,人们很轻易地就承认了。但做进一步仔细的考察便可看出,思维的纯粹存在根本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现在表明,在笛卡尔的领域中,各种对象就已经在“构造”自身,而构造活动说明,内在的被给予性并不像它最初所显示的那样简单地在意识之中,就像在一个盒子中一样,相反,它们在“现象”中显示自己,这些现象本身不是对象,并且不实项地包含对象;如果在这里为了使被称为“被给予性”的东西(4)得以出现而需要这种形成和构造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就在其变化的和非常奇特的构造中,在某种意义上为自我创造对象。在感知以及它的保留中,原初的时间客体构造着自身,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中时间才能被给予。所以在建立于感知或想象之上的一般性意识之中,一般之物构造着自身;在想象中,并且也在感知中,在单一实质意义上的直观内容构造着自身,这时不考虑存在的设定。此外,我们回想一下,还有种种行为,它们在这里始终是明证的陈述的前提。在这里出现、并且在是与否、同与异、一与多、并且与或者等等词中以谓词判断和属性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指明了思维的形式,但如果这些思维形式构造恰当,那么借助于它们,被给予性就可在综合联结基本行为的基础上成为意识,这便是这些或那些本体论形式的事态。这里也“发生了”(“geschieht”)当时对象在如此形成的思维行为中的自身“构造”;而被给予,或者说,对事物的纯直观在其中进行的意识更不仅仅是一种盒子式的东西(在这盒子中被给予性是简单的),而是直观的意识,它是——对关注忽略不计——\n这样和那样已形成的思维行为,事物不是思维行为,但却在这思维行为中被构造,在它们之中成为被给予性;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只是以被构造的方式表现它们自身为何物。但这难道不是纯粹的奇迹吗?而这种对象的构造是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停止的呢?有没有真实的界限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任何现象和判断中不都形成一种被给予性吗?任何对象在这样或那样被直观、被想象、被思维时,难道不是一种被给予性、一种明证的被给予性吗?在感知一个外部事物时,这事物,例如一个出现在眼前的房屋,可以说被感知。这个房屋是一超越,它融入根据存在现象学还原的存在中。真实明证地被给予的是这房屋的显现,是在意识流中出现并流逝的这个思维。在这个房屋现象中我们找到红的现象、广延的现象等等。这是明证的被给予性。但是,在这个房屋现象中显现出一个房屋,为此它也叫作对房屋的感知;而这不是一般的房屋,恰恰就是这一座房屋,这些难道不也是明证的吗?我难道不能明证地判断说:根据现象,或者,在这感知的意义上,房屋是这样或那样的,是砖屋,屋顶是石板的等等?而如果我在想象中进行虚构,例如我眼前浮现出骑士圣.乔治在杀一条龙,那么这想象现象所展现的圣.乔治,“这个”“被”描述得如此这般的骑士,并不是明证的,即是一种“超越”。难道我在这里不能明证地进行判断,不能对想象现象的实项内容进行判断,而只能对显现的事物对象进行判断吗?显然,只有对象的一个方面,时而这方面,时而另一方面出现在真正的当下化的框架中,但是与以往一样,这一点却是明证的,即:这个对象、骑士圣.乔治等等具有现象的意义并且在现象中符合现象地表明为“被给予性”。最后是所谓符号思维。我不带任何直观去思维二乘二等于四。我是否可以怀疑,我在思维这个算术式,并且这个被思维之物与今天的天气无关?这样我也具有明证性,即类似被给予性的东西吗?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一切于事无助,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方式上背谬的东西,完全愚蠢的东西也是“被给予的”。一个圆的四角形不会像屠龙者出现在我面前一样,显然在想象中,也不会像一个通常的外部事物那样出现在感知中。但一个意向客体却明证地存在于此。我能够根据其实项内容描述一个“圆的四角形的思想”这个现象,但圆的四角形却不在其中,而这一点却是明证的,即:它在这个思维中被思维,并且这个被思维之物本身在思维过程中被加上了圆形和四角形的特征,或者,这个思维的客体是一个圆形的并且同时又是四角形的客体。现在绝对不应说,这些在最后被阐述的被给予性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被给予性,因此最终所有被感知之物、被想象之物、被虚构之物、符号性地被想象之物,所有构造和荒谬都是“明证地被给予的”;而是只应指出,这里有着巨大的困难。原则上看,在澄清它们之前,它们不能阻止我们说,真实的明证性伸展得有多远,被给予性伸展得有多远。但当然,到处都存在着的大问题是,在完成明证性的过程中纯粹地确定,但明证性中什么是真实地被给予的,什么不是的;并且确定,在这同时,非真正的思维在其中塞入了些什么,并无被给予性根据地解释于其中。而这里问题不在于将随便什么现象都确定为被给予的,而是了解被给予性的本质和各种对象样式的自身构造活动。诚然,任何思维现象都具有其对象性关系,并且任何思维现象——这是第一个本质的了解——都有其作为诸因素的总和的实项内容,这些因素在实项的意义上构成这思维现象;另一方面,它具有其意向对象,这对象根据其本质形成的不同被意指为是这样或那样被构造的对象。如果这个具体情况确实能够成为明证性,那么这个明证性必然会给我们所有必要的教益;在它之中必须表明,这种“意向的非存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并且它与思维现象本身的实项内容的关系如何。我们必须看到,它在何种联系中作为真实和真正的明证性出现,并且在这种关系中真实和真正的明证性是什么。而后问题就在于展示真正的被给予性的各种样式,换言之,对象的各种样式的构造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如:思维的被给予性,在新鲜的回忆中犹存的思维被给予性,在现象的河流中持续的现象统一性的被给予性,这个统一性变化的被给予性,在“外部”\n感知中的事物的被给予性,幻想和重复回忆以及在相应的联系中杂多综合地统一在一起的感知和其他想象的各种形式的被给予性。当然还有逻辑的被给予性,一般性的被给予性,谓词的、事态的被给予性等等,还有背谬的、矛盾的、非在的被给予性等等。被给予性,尽管在它之中表现出纯想象之物或真实存在之物,实在的或观念的、可能或不可能之物,但它无论在哪里都是一种在认识现象之中的被给予性,在最广义的思维现象中的被给予性,并且,在本质考察中处处都在探究这个起初是如此奇特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认识中才能完全根据对象所有的基本形态来研究这对象的本质,只有在认识中它才是被给予的,它才能被明证地直观。这种明证的直观本身就是最确切意义上的认识;而对象不是一个像藏在口袋里一样的藏在认识中的东西,好像认识是一个到处都同样空洞的形式,是一个空口袋,在里面这次装进这个,下次装进那个。相反我们认为被给予性就是: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对象有如此之多的基本形态须予以区分,给予的认识行为和认识行为的集合、联系也有如此之多的基本形态须予以区分。而认识行为,进一步说,即思维行为,它们完全不是无联系的个别性,它们并非无联系地在意识流中来来去去。它们在本质上相互联系,显示出目的论的相互依存性,实现、确证、证明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对应物。这种展示出合乎知性统一性的联系,便是问题所在。它们本身是构造对象的;它们在逻辑上联结非真正给予行的行为和真正给予行的行为,纯想象行为或者毋宁说纯信仰行为和了解行为,并且联结杂多的与对象有关的行为,无论它是直观的思维或是非直观的思维。而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客观科学的对象,首先是实在的时空现实的对象才构造自身,但这一构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进行的。对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进行研究并且是在纯粹明证性的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阐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的大问题。原初的问题是主体的心理学的体验和在这体验中被把握的自在现实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实在的现实,尔后也包括数学的和其他观念的现实。首先需要了解,根本问题必然在于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在已被还原的意义上,根据这意义,这里谈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一般认识,不附带任何存在的设定关系,无论它是与经验的自我的关系,还是与实在的世界的关系。需要了解,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认识的最终意义给予问题以及一般对象问题,一般对象本身只存在于它与有可能认识的相互关系中。此外还需要了解,这个问题只在纯粹被给予性的领域中,只在绝对的、因而作为最终标准的被给予性领域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在直观过程中一个一个地探究认识的所有基本形态和在认识中全部或部分地成为被给予性的对象的所有基本形态,以便规定所有须阐明的相互关系的意义。伦理学中的先天质料[1]本文选自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哈雷,1916/1921年)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篇。它扼要地说明了舍勒在他这部代表作中所倡导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该书目前正在翻译之中,将由三联书店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中出版。——译注[1]【德】马克斯·舍勒著倪梁康译现在我想在下面的论述中表明,即使在一般价值先天(Wertapriori)以内,形式的东西也绝不会与先天的东西相等同,在这里存在着先天本质关系的基本种类\n。但我在此并不想把所有包含在这些基本种类中的东西都加以阐释。这种做法将意味着展开这门实证的伦理学本身,而这里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第1章.形式的本质联系 在各个先天联系中,可以被称作(纯粹)“形式的(formal)”联系,是那些不依赖于任何价值种类和价值质性以及不依赖于“价值载体”之观念、并且建基于作为价值的价值之本质中的联系。它们共同展示着一门纯粹的价值论,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纯粹的逻辑学相符合。而在它之中重又区分出一门关于价值本身的纯粹学说以及一门关于价值认定(与逻辑学的“对象理论”和“思维理论”相符合)的纯粹学说。在这里首先存在着一个本质事实,即:所有价值(无论它们是伦理学的还是美学的等等)都分为(为简便起见我们要说)肯定的价值和否定的价值。这一点包含在价值的本质之中,并且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刚好能够感受到这些特殊的价值对立(即肯定的和否定的价值),如美-丑、善-恶、适意-不适意等等。与此相对的是那些已经部分地为弗兰茨·布伦塔诺所发现的“公理”,它们先天地确立了存在与肯定的价值和否定的价值的关系。这些公理就是: 一个肯定的价值的实存本身就是一个肯定的价值。一个否定的价值的实存本身就是一个否定的价值。一个肯定的价值的非实存本身就是一个否定的价值。一个否定的价值的非实存本身就是一个肯定的价值。 在这里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在价值和(观念)应然之间的本质联系。首先是这样一个定律:所有应然都必须奠基于价值之中,即:惟有价值才应当存在和不应当存在;以及这样的定律:肯定的价值应当存在,否定的价值不应当存在。而后是那些本质联系,它们对存在与观念应然的关系来说是先天有效的,并且规整着合理存在(Rechtsein)与不合理存在(Unrechtsein)的关联。因而,一个(肯定的)应然之物(Gesollte)的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一个非存在应然的所有存在都是不合理的;一个应然之物的所有非存在都是不合理的;但一个非应然之物的所有非存在都是合理的[2]正如观念的应然与义务和规范无关一样,合理(dasRechte)也与“正确”(dasRichtige)无关,后者仅仅涉及一个为规范所如此要求的行为举止。[2]。接下来在这里还包括这样的联系:同一个价值不可能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但每一个不是否定的价值都是肯定的价值,每一个不是肯定的价值都是否定的价值。这些定律例如也不是对矛盾律、排中律的运用,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定律所涉及的不是定律关系,而是本质联系。但它们并不是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存有的本质联系,仿佛在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价值的存在与不存在。毋宁说,这些联系是在价值本身之间的联系,无论这些价值存在还是不存在[3]上述联系论证了一门纯粹形式的价值学,它与作为关于对象一般的科学的纯粹(形式的)逻辑学相并列。[3]。而与它们相符合的是这样一个价值认定原则:不可能将同一个价值认定为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此等等。我在这里要强调:由康德所发现的那些原则只是部分地展示着这个形式的价值认定原则的一个特例;这种展示仅仅在于,它们(错误地)只与伦常\n领域相关联,并且(同样错误地)不与价值认定相关联,而只是直接与愿欲相关联,但它们实际上却只对愿欲(甚至是追求一般)有效,因为它们对那个作为愿欲(和追求)之基础的价值认定有效。因为,康德以各种方式所表述的“伦常法则”就意味着:或者是要求避免在目的设定中的矛盾(主观地和合规范地说:“协助制作一个由这些目的组成的王国,在其中任何一个目的都可以与任何其他的目的无矛盾地共存”);或者就是要求保证愿欲的一致性(即:对自己保持“忠实”),在同样的条件下(即同样的“经验特征”条件和“环境”条件下)愿欲同样的东西,等等[4]Th.利普斯新近已经确切地强调,康德的“伦常法则”在根本上只是对愿欲领域而言的同一原理与矛盾原理。[4]。但康德恰恰在此有着多重的误解:1.完全不可能从这些“形式”法则中获得善的观念;毋宁说,“善”的价值只是这些形式的价值法则(它们对所有价值有效)的一个运用领域,但在这些运用过程中预设了“善”与“恶”。2.这些法则建基于直观的本质联系之中(就像逻辑法则也是如此)。3.它们在价值之间、同样也在价值认定之间原初地起效用。4.它们是价值把握的法则(只要它们是行为法则),但原初并不是意愿法则。相反,在我们看来,康德原则上已经获得这样一个正确的否定性认识:这些法则并不是对逻辑(理论)法则的单纯运用,即是说,是一些只有当对象是判断对象时才运用在伦常行为举止上的法则,而且无论如何也是伦常行为举止本身的直接法则,即便——如他所以为的那样——它们首先是愿欲的而非价值认定的直接法则。这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意味着,“理性”在它们之中“直接成为实践的”。但他也完全误解了(此外也在理论的领域中)这些“法则”的意义。例如,并非是因为矛盾律对“存在的思维”有效,它才对存在有效;而是因为那个充实着它本质联系在所有存在(甚至包括实际的思维)中都被充实,矛盾律才对存在的思维有效。就是说它意味着,在这些定理的领域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A是B”与“A不是B”都是真实定理:因为这个存在根据其本质排斥了这个可能。惟有通过这些定理中的一个定理(A是B并且A不是B)与存在的争执,这两者才能够是在判断中被意指的定理。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定理,那么在一个定理的A与另一个定理的A之间(A与A')或在B(B与B')之间或在它们的联结之间便必定存在着一个差异。但对判断来说有效的是:只要在判断中所意指的是同一个A和同一个B以及它们的同一种存在联结,那么就不可能实际地做出“A是B并且A不是B”的判断。每当我们看到似乎有这种判断做出时,在同一些表述中总是隐含着不同判断的事实。因为,“判断A是B”和“判断A不是B”这两个定理是先天不可能(“在不损害真理的情况下”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