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7 发布 |
- 37.5 KB |
- 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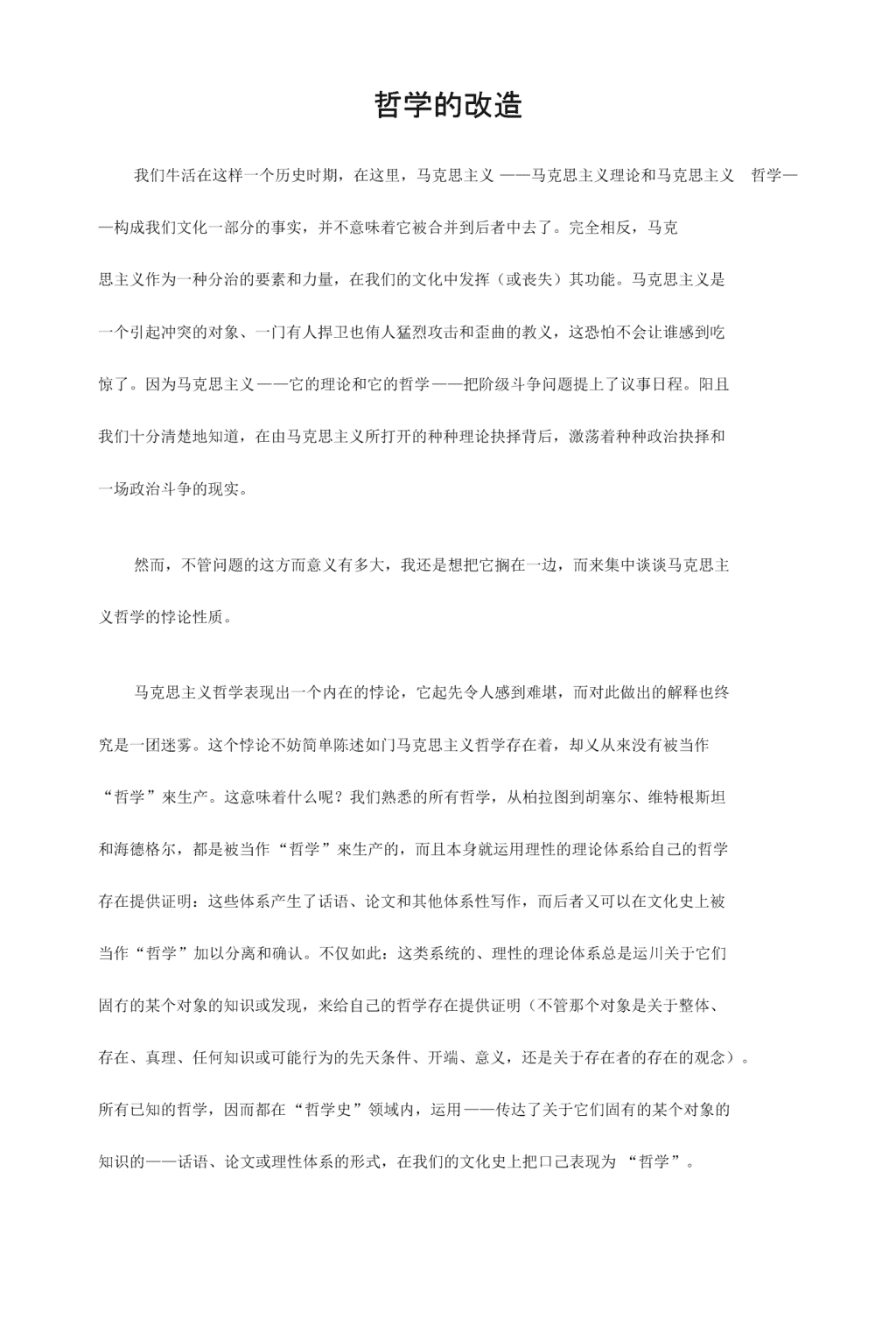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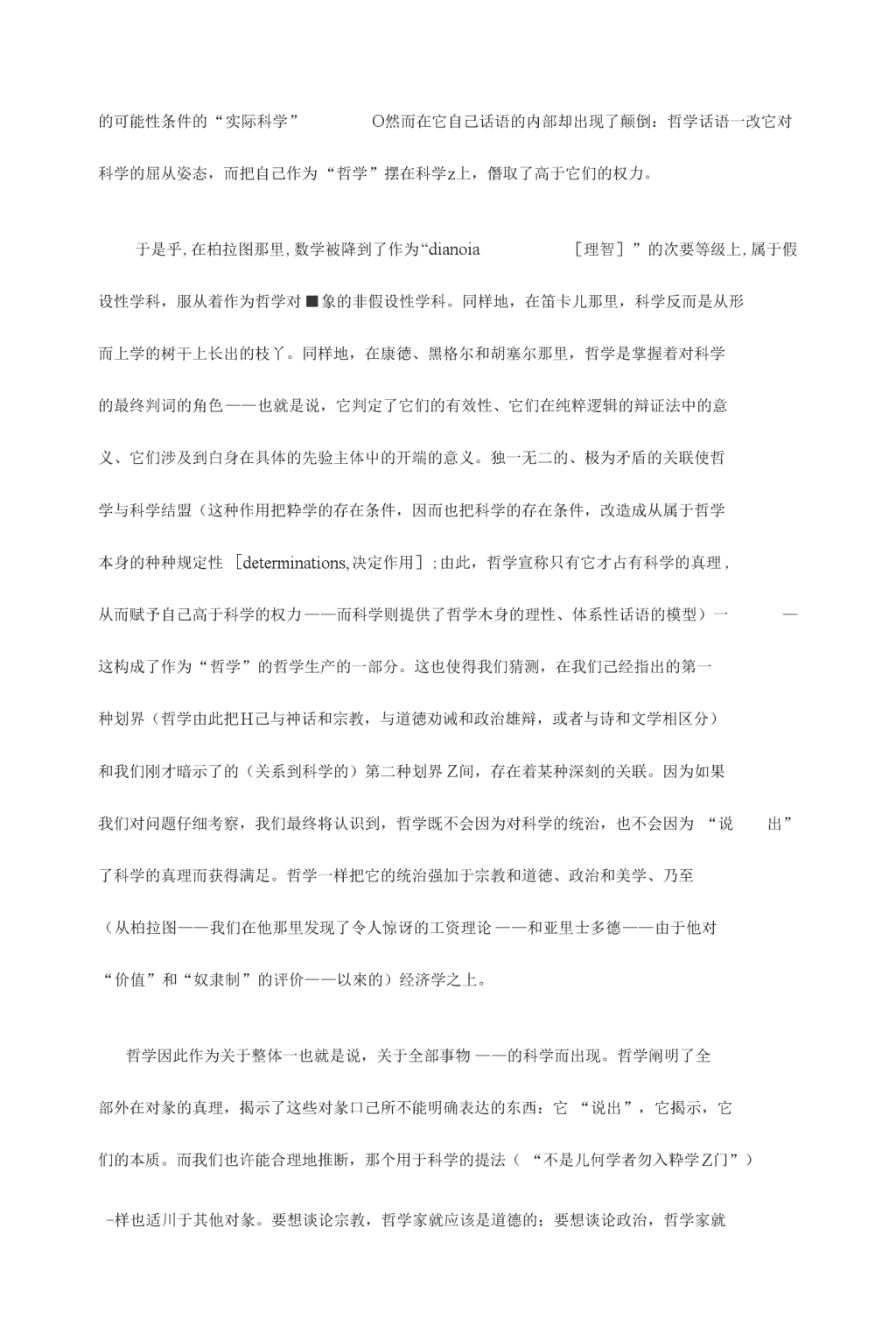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哲学的改造》 论文
哲学的改造我们牛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我们文化一部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被合并到后者中去了。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治的要素和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中发挥(或丧失)其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引起冲突的对象、一门有人捍卫也侑人猛烈攻击和歪曲的教义,这恐怕不会让谁感到吃惊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和它的哲学——把阶级斗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阳且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由马克思主义所打开的种种理论抉择背后,激荡着种种政治抉择和一场政治斗争的现实。然而,不管问题的这方而意义有多大,我还是想把它搁在一边,而来集中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一个内在的悖论,它起先令人感到难堪,而对此做出的解释也终究是一团迷雾。这个悖论不妨简单陈述如门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乂从來没有被当作“哲学”來生产。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熟悉的所有哲学,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被当作“哲学”來生产的,而且本身就运用理性的理论体系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这些体系产生了话语、论文和其他体系性写作,而后者又可以在文化史上被当作“哲学”加以分离和确认。不仅如此:这类系统的、理性的理论体系总是运川关于它们固冇的某个对象的知识或发现,来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不管那个对象是关于整体、存在、真理、任何知识或可能行为的先天条件、开端、意义,还是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观念)。所有已知的哲学,因而都在“哲学史”领域内,运用——传达了关于它们固有的某个对象的知识的——话语、论文或理性体系的形式,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把口己表现为“哲学”。\n但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思考。所有已知的哲学,当它们在文化领域内自我确立为“哲学”的时候,都把口己M其他话语形式或其他书写作品体例仔细地区别开来。柏拉图写他的对话或他的说教作品的时候,他非常细心地把它们与其他任何文学的、修辞的或诡辩的话语区别开来。笛卡儿或斯宾诺莎写作的时候,谁也不会把它错当成“文学”。康徳或黑格尔写作的吋候,摆到我们面前的也不是道徳劝诫、宗教布道或长篇小说。从而,哲学通过把口己跟道徳、政治、宗教或文学文类彻底相区分而牛产自己。但最要紧的是,哲学通过把白己跟科学相区分而作为“哲学”牛产B己。问题的最关键的方而Z—就在这里出现了。看起來好像哲学的命运是与科学的存在深刻联系着的,因为总是需要冇科学的存在來引出哲学(就像在古希腊,当时儿何学引来了柏拉图的哲学)。而这种同命相系的更深刻之处还在于,离开了某种纯科学理性话语的可靠存在,哲学就不可能出现(例如几何学Z于柏拉图、解析几何学与物理学之于笛卡儿、牛顿物理学之于康徳,等等)。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有别于神话、宗教、道德或政治劝诫,以及审美),其绝对前提是它自己能够提供一种纯粹的理性话语一—可以说,这样一种理性话语的模型,哲学只有在现有科学的严格话语中才能找到。但是在下而这一点上,事情经历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颠倒:哲学从现有的纯科学那里借來了它自己纯粹理性话语的模型(想一想从“不是几何学者勿入哲学之门”,到斯宾诺莎“关心几何学”的告诫,再到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连续不断的传统),然阳也正是这个哲学,在皆学中完全颠倒了它与科学的关系。也就是说,哲学把H己从实际科学及其对彖那里严格分离出來,并宣称自己就是一门科学——当然不是作为普通科学(这类科学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而毋宁是作为蝕高科学、诸科学的科学、关于任何科学的先天条件的科学、关于那种能够把所有实际科学转化为单纯理智规定性的辩证逻辑的科学,等等。换言Z,哲学从现有的科学那里借来了适合于它的纯粹理性话语的模型。因而它服从于作为它\n的可能性条件的“实际科学”O然而在它自己话语的内部却出现了颠倒:哲学话语一改它对科学的屈从姿态,而把自己作为“哲学”摆在科学z上,僭取了高于它们的权力。于是乎,在柏拉图那里,数学被降到了作为“dianoia[理智]”的次要等级上,属于假设性学科,服从着作为哲学对■象的非假设性学科。同样地,在笛卡儿那里,科学反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树干上长出的枝丫。同样地,在康徳、黑格尔和胡塞尔那里,哲学是掌握着对科学的最终判词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判定了它们的有效性、它们在纯粹逻辑的辩证法中的意义、它们涉及到白身在具体的先验主体屮的开端的意义。独一无二的、极为矛盾的关联使哲学与科学结盟(这种作用把粋学的存在条件,因而也把科学的存在条件,改造成从属于哲学本身的种种规定性[determinations,决定作用];由此,哲学宣称只有它才占有科学的真理,从而赋予自己高于科学的权力——而科学则提供了哲学木身的理性、体系性话语的模型)一—这构成了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的一部分。这也使得我们猜测,在我们己经指出的第一种划界(哲学由此把H己与神话和宗教,与道徳劝诫和政治雄辩,或者与诗和文学相区分)和我们刚才暗示了的(关系到科学的)第二种划界Z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因为如果我们对问题仔细考察,我们最终将认识到,哲学既不会因为对科学的统治,也不会因为“说出”了科学的真理而获得满足。哲学一样把它的统治强加于宗教和道徳、政治和美学、乃至(从柏拉图——我们在他那里发现了令人惊讶的工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由于他对“价值”和“奴隶制”的评价——以來的)经济学之上。哲学因此作为关于整体一也就是说,关于全部事物——的科学而出现。哲学阐明了全部外在对彖的真理,揭示了这些对彖口己所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它“说出”,它揭示,它们的本质。而我们也许能合理地推断,那个用于科学的提法(“不是儿何学者勿入粋学Z门”)-样也适川于其他对彖。要想谈论宗教,哲学家就应该是道德的;要想谈论政治,哲学家就\n应该是政客;要想谈论艺术,哲学家就应该是审美家;等等。与我们出入于科学领域所看到的相同类型的颠倒也照样——只不过是悄悄地一一作用于其他所有对彖——这些“对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栖身于哲学的空间。当然,哲学只有在先行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它们之上的条件下,才会愿意接纳它们。用几句话来说: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涉及到所有人类观念和所有人类实践,但总是耍让它们从属于“哲学”——也就是说,要让它们服从于一种根本的“哲学形式”。而人类实践和观念“从属”于“禅学形式”的这个过程,我们尽可在哲学对话、论文和体系中得以真切目睹。像这样提出问题可能显得有点儿过于简单化:为什么哲学需要像一个特立独行的事物那样存在?为什么它需要尽可能小心地说话,來把自己跟科学、也跟其他任何观念或社会实践相区分?噢,哲学只能谈论它们!让我们说问题不那么简单吧。哲学感到需要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承担了不仅要说话述耍把不得不说的话付与独立的、可确认的论文形式的责任——这一点缘于一个事实,即秤学,以其深刻的历史信念,认为H己有一•个不容替代的任务要去完成。这就是去说出关于全部人类实践和观念的真理。哲学相信没冇谁、没冇什么可以代表它说话,相信如果它不存在,世界就会失去它的真理。因为要让世界存在的话,就必须让这样的真理说出来。这真理就是逻各斯,或开端,或意义。并且由于有着共同的开端存在于逻各斯与言说Z间(Logos与Legein[说]、真理与话语Z间,或者换种方式说,由于逻各斯特有的、顽强的存在并不是物质性或实践或别的什么形式,而是言说、声音、词语),那么就只冇唯一的工具去了解逻各斯,因而了解真理:这就是话语的形式。逻各斯与言说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意味着,真理、逻各斯只冇在哲学话语中才能完全被包揽或被抓住并呈献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哲学决不可能超?剿陨淼幕坝镰M%囊坏闵牵幕坝铮2•皇撬月氐帶碇滦哪持置浇榛虻鹘馒耍riw亲題吒邇沟恼捋淼脑诔?BR>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奇特的悖论摆在了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悟学存在着,但它并没有被当作我们刚才分析过的意义上的哲学来生产。我们不需要绕得太远去证明这一点。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宣告了一种从未到来的哲学一一的那些光彩夺口的、谜一般的短句;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的哲学批判,其矛头所指的新黑格尔派则一•味使全部哲学都笼罩在意识形态虚无的雾霭里;也除了在《资木论》徳文第二版跋屮关于黑格尔的著名的提示——马克思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哲学论文或话语。有两次,在两封信里,他许诺要用二十页左右来谈谈辩证法,但它们从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怕是并不那么好写。无疑,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他对杜林的哲学批判,而列宁留下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一另一个批判。从一次批判中无疑可以冇许多要素被抽绎出來,但是将如何就此做出\n思考呢?我们将如何“在理论上”来构造它呢?我们是否正而对着一个整体的要素,尽管这是个缺席的整体,并无有效的在场——但是这个整体足以按照传统的模型,就像继续浸淫于“本体论”的种种马克思主义禅学的情形那样,把那些要素重新加以整合?耍么正好相反,问题就在于那些要索,它们必须受到质疑和破译、明确地“受到提问”:它们为什么仅仅一—而且独一无二地——保持为一些“要素”?当然,我们还有列宁关于黑格尔的《笔记》。但是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赋予单纯的读书笔记、赋予这样光彩夺目却又像谜一般的评点以怎样的意义呢?总Z,我们被迫在每一个例证前得出结论:马克思,乃至恩格斯和列宁,连勉强能够与古典的哲学话语形式相比的东西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如今,这一悖论的广度还在我们面前伸展。它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的缺席仍然生产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所继承的哲学,伟大的古典哲学传统(从柏拉图到笛卡儿、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胡塞尔),由于马克思突然间引起的那场不可捉摸的、近乎无形的遭遇战的冲击,己经在根木上(并在其所有意图方面)受到了动摇。然而这一点从未以直接的衿学话语形式出现,完全相反:它出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形式中。换言Z,那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而是一种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它,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进行考察的文木;最终,是一种只讨论与阶级斗争有关的那种科学知识的文本(那种科学知识因而同吋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出现在我们面而——这也正是在《资本论》中表述出來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悖论呢?我希望通过一条最短的途径来解答这个悖论,纵然那并不完全是现实历史的途径。因此,我想首先表明,由于其全部的简略和未完成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包含着一个棊木建议的草图。当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无疑使用了可以在先验的实践哲学的意义上加以阐释的一些套话。有些人一直坚持求助于这里的能动的主体性,指望它能够使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合法化,然而马克思却是在谈论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明确宣布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用实践来反对\n“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的谜一般的句子里,马克思没有釆用任何与“客体[对彖]形式”和“直观形式”等价的哲学概念,并由此取而代Z,以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开创—•种新的哲学话语。不,他建立的是一种具有存在的特殊性的现实,这种存在的特殊性同吋既耍用所有的传统哲学话语来预设,却又天生地被排斥在这些话语Z外。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