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7 发布 |
- 37.5 KB |
- 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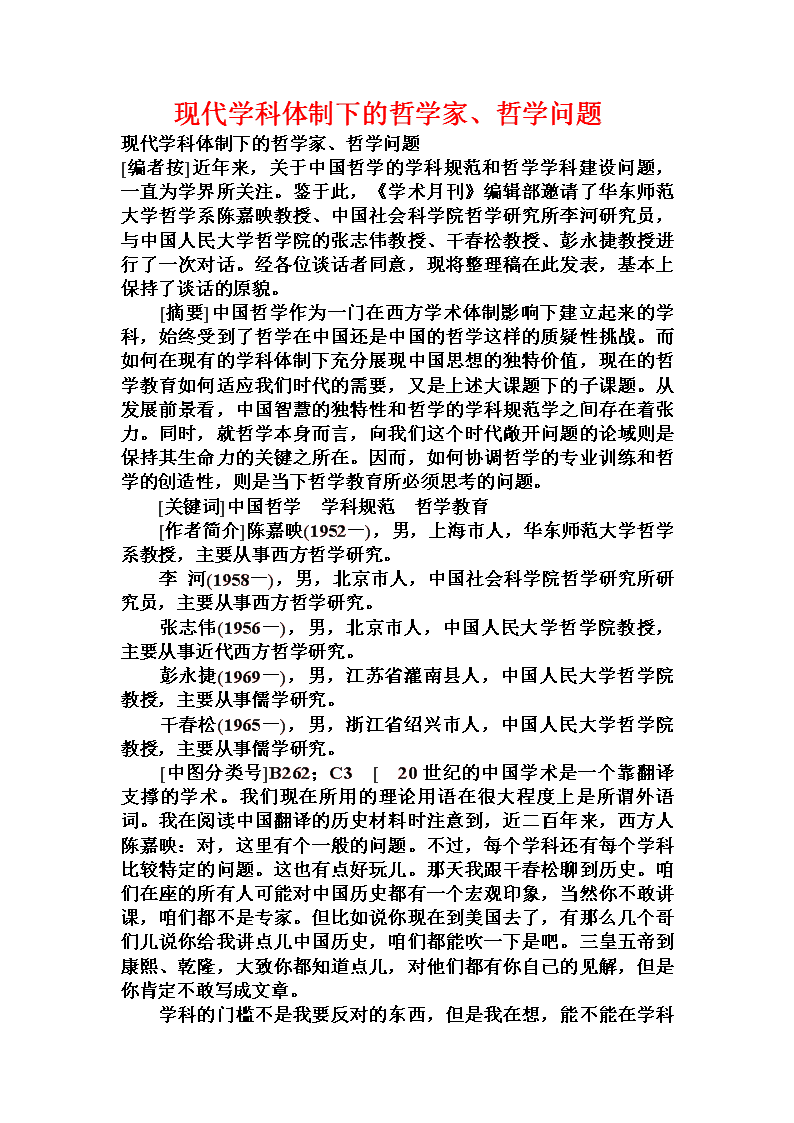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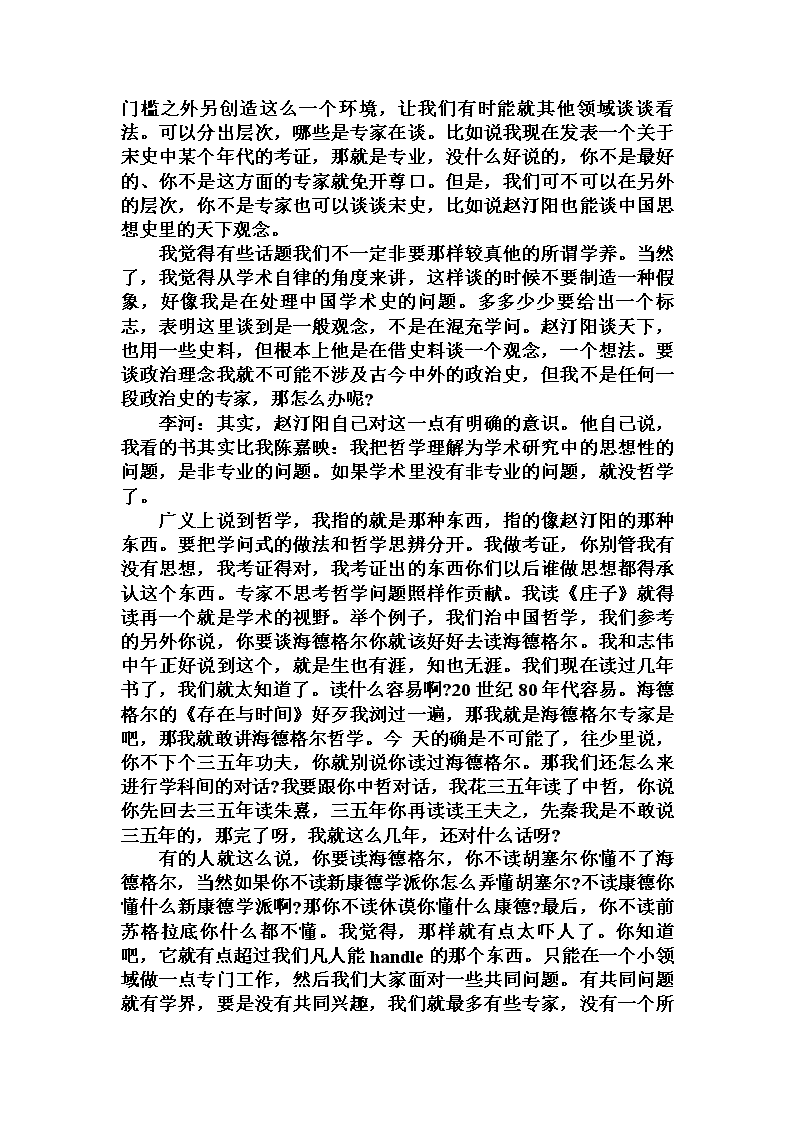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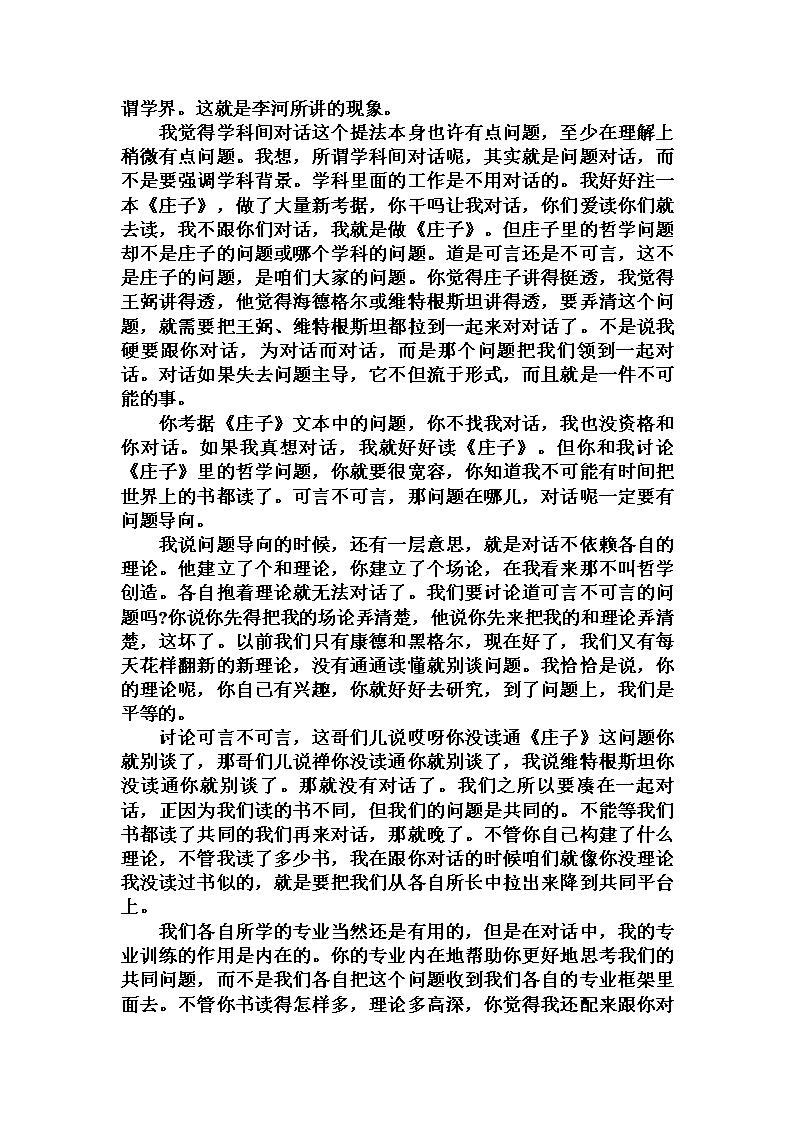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编者按]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的学科规范和哲学学科建设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鉴于此,《学术月刊》编辑部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河研究员,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张志伟教授、干春松教授、彭永捷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经各位谈话者同意,现将整理稿在此发表,基本上保持了谈话的原貌。 [摘要]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学术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始终受到了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质疑性挑战。而如何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下充分展现中国思想的独特价值,现在的哲学教育如何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又是上述大课题下的子课题。从发展前景看,中国智慧的独特性和哲学的学科规范学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就哲学本身而言,向我们这个时代敞开问题的论域则是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如何协调哲学的专业训练和哲学的创造性,则是当下哲学教育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哲学 学科规范 哲学教育 [作者简介]陈嘉映(1952-),男,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李河(1958-),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张志伟(1956-),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代西方哲学研究。 彭永捷(1969-),男,江苏省灌南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儒学研究。 干春松(1965-),男,浙江省绍兴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儒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C3 [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我们现在所用的理论用语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外语词。我在阅读中国翻译的历史材料时注意到,近二百年来,西方人陈嘉映:对,这里有个一般的问题。不过,每个学科还有每个学科比较特定的问题。这也有点好玩儿。那天我跟干春松聊到历史。咱们在座的所有人可能对中国历史都有一个宏观印象,当然你不敢讲课,咱们都不是专家。但比如说你现在到美国去了,有那么几个哥们儿说你给我讲点儿中国历史,咱们都能吹一下是吧。三皇五帝到康熙、乾隆,大致你都知道点儿,对他们都有你自己的见解,但是你肯定不敢写成文章。\n 学科的门槛不是我要反对的东西,但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学科门槛之外另创造这么一个环境,让我们有时能就其他领域谈谈看法。可以分出层次,哪些是专家在谈。比如说我现在发表一个关于宋史中某个年代的考证,那就是专业,没什么好说的,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免开尊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另外的层次,你不是专家也可以谈谈宋史,比如说赵汀阳也能谈中国思想史里的天下观念。 我觉得有些话题我们不一定非要那样较真他的所谓学养。当然了,我觉得从学术自律的角度来讲,这样谈的时候不要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我是在处理中国学术史的问题。多多少少要给出一个标志,表明这里谈到是一般观念,不是在混充学问。赵汀阳谈天下,也用一些史料,但根本上他是在借史料谈一个观念,一个想法。要谈政治理念我就不可能不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但我不是任何一段政治史的专家,那怎么办呢? 李河:其实,赵汀阳自己对这一点有明确的意识。他自己说,我看的书其实比我陈嘉映:我把哲学理解为学术研究中的思想性的问题,是非专业的问题。如果学术里没有非专业的问题,就没哲学了。 广义上说到哲学,我指的就是那种东西,指的像赵汀阳的那种东西。要把学问式的做法和哲学思辨分开。我做考证,你别管我有没有思想,我考证得对,我考证出的东西你们以后谁做思想都得承认这个东西。专家不思考哲学问题照样作贡献。我读《庄子》就得读再一个就是学术的视野。举个例子,我们治中国哲学,我们参考的另外你说,你要谈海德格尔你就该好好去读海德格尔。我和志伟中午正好说到这个,就是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们现在读过几年书了,我们就太知道了。读什么容易啊?20世纪80年代容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好歹我浏过一遍,那我就是海德格尔专家是吧,那我就敢讲海德格尔哲学。今天的确是不可能了,往少里说,你不下个三五年功夫,你就别说你读过海德格尔。那我们还怎么来进行学科间的对话?我要跟你中哲对话,我花三五年读了中哲,你说你先回去三五年读朱熹,三五年你再读读王夫之,先秦我是不敢说三五年的,那完了呀,我就这么几年,还对什么话呀?\n 有的人就这么说,你要读海德格尔,你不读胡塞尔你懂不了海德格尔,当然如果你不读新康德学派你怎么弄懂胡塞尔?不读康德你懂什么新康德学派啊?那你不读休谟你懂什么康德?最后,你不读前苏格拉底你什么都不懂。我觉得,那样就有点太吓人了。你知道吧,它就有点超过我们凡人能handle的那个东西。只能在一个小领域做一点专门工作,然后我们大家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有共同问题就有学界,要是没有共同兴趣,我们就最多有些专家,没有一个所谓学界。这就是李河所讲的现象。 我觉得学科间对话这个提法本身也许有点问题,至少在理解上稍微有点问题。我想,所谓学科间对话呢,其实就是问题对话,而不是要强调学科背景。学科里面的工作是不用对话的。我好好注一本《庄子》,做了大量新考据,你干吗让我对话,你们爱读你们就去读,我不跟你们对话,我就是做《庄子》。但庄子里的哲学问题却不是庄子的问题或哪个学科的问题。道是可言还是不可言,这不是庄子的问题,是咱们大家的问题。你觉得庄子讲得挺透,我觉得王弼讲得透,他觉得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讲得透,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王弼、维特根斯坦都拉到一起来对对话了。不是说我硬要跟你对话,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那个问题把我们领到一起对话。对话如果失去问题主导,它不但流于形式,而且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你考据《庄子》文本中的问题,你不找我对话,我也没资格和你对话。如果我真想对话,我就好好读《庄子》。但你和我讨论《庄子》里的哲学问题,你就要很宽容,你知道我不可能有时间把世界上的书都读了。可言不可言,那问题在哪儿,对话呢一定要有问题导向。 我说问题导向的时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话不依赖各自的理论。他建立了个和理论,你建立了个场论,在我看来那不叫哲学创造。各自抱着理论就无法对话了。我们要讨论道可言不可言的问题吗?你说你先得把我的场论弄清楚,他说你先来把我的和理论弄清楚,这坏了。以前我们只有康德和黑格尔,现在好了,我们又有每天花样翻新的新理论,没有通通读懂就别谈问题。我恰恰是说,你的理论呢,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好好去研究,到了问题上,我们是平等的。 讨论可言不可言,这哥们儿说哎呀你没读通《庄子》这问题你就别谈了,那哥们儿说禅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我说维特根斯坦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那就没有对话了。我们之所以要凑在一起对话,正因为我们读的书不同,但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不能等我们书都读了共同的我们再来对话,那就晚了。不管你自己构建了什么理论,不管我读了多少书,我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咱们就像你没理论我没读过书似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各自所长中拉出来降到共同平台上。\n 我们各自所学的专业当然还是有用的,但是在对话中,我的专业训练的作用是内在的。你的专业内在地帮助你更好地思考我们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我们各自把这个问题收到我们各自的专业框架里面去。不管你书读得怎样多,理论多高深,你觉得我还配来跟你对话,就说明你这事儿还没想通,想着虽然陈嘉映没读过这些,但他读过一点儿维特根斯坦,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问题有贡献。 最后一点就是李河所说的德勒兹那个所谓geophilosophy,我觉得这个概念的确是很重要。我一向觉得,哲学大会上是不可能对话的。我们都开过大会,纯粹都是在走形式。今天我们五个人关心一个问题,挺好。用不着五百个人,那只是壮观、热闹。我们五个对完话呢,也兴许我们几个又找另外几个对话,为什么呢?因为那几个人关心那问题,这几个人关心这问题。若说哲学是对话,那是一个连环套的对话,并非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哲学,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想。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就是这些局部的哲学思想,通过连环的对话联系在一起。 彭永捷:我再补充点儿。现在提倡的学科对话,应看成一个暂时现象。我说这是一个暂时现象,内在问题只不过是我们不同学科的,因为都是专家,等于说专家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个更引申一下,为什么这个不同学科的专家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里边根本性的还是要意识到身份的变化。从哲学史的学问来说,我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讲王弼讲语言,我讲清楚就完了,但是我真正认识到我要做哲学探讨,我就像刚才说那些哲学爱好者、那些同学似的,我要研究语言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意识才突出出来。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自觉转换,不会去看到那个问题本身去。我最多就问问你,对王弼是怎么理解的?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是怎么理解的?我因为要了解他们才问这个问题。 陈嘉映:对,有时我要请教专家,给我一个专业性的指导,这不是对话,是学习。\n彭永捷:关于嘉映说的学生的例子,我觉得这里有个前提。因为你在从事教学,你在塑造一个学生,不是说你一定要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老师从学生那儿可能有时候得到东西,可能有时候得不到东西。这个学生是个好苗子,你可以引导他,指导他通过哲学史进行哲学的训练。我举个例子,我们探讨颜色是什么,就像在爱智论坛上看到的颜色是什么?也可能只有哲学系的人才无聊到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有人说颜色就是光和波,是属性(哲学史上的一种观点),另外有人会说是感受性,有的说是观念,通过这个就可以引出不同的哲学家。哲学上的问题往往是永恒的问题,可以不断地思考。我们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哲学的训练。我们现在教学中排斥的那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哲学教学中最缺乏的。我们首先就想培养一个学问家,有没有想到让学生一起来和我思考,就哲学上的事儿进行探究。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做这样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做的也就是研究一个人怎么说,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种风气,看到学生一做这个的话,我们总觉着你哲学史还没弄明白呢,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可见,在这个思想方式上我们就已经不可能去培养一个从事哲学的了。 陈嘉映:在教育上我倒不是说专业教育太多、通识教育太少,说得圆滑点,两个都太少。 对话时动不动就拿出自己的专家身份,是吓唬人。对哲学思考来说,无论你学的是海德格尔还是康德,最后要学的都是人家那个理路啊!这个理路不一定非学海德格尔不行,学康德就不行。这是个基本训练。关键在于不要把专家和问题混起来。 李河:嘉映把哲学问题概括为非专业的,我觉得可能超专业的说法要好一点。这既涉及学术判断力问题,也涉及专业训练问题。单纯的专业训练只强调术业有专攻,而把闻道有先后那个说法先放在了一边。但术业与闻道在哲学上是不能分离的。我记得Hirsch在ualidityofinterpre-tation这本书里曾区别了两个概念,就是meaning和significance。Meaning是说一个文本、一个表达式有它的内在意义或内在含义,这是你自己需要花很多专业功夫去搞明白的。但是这个significance呢,它在中文中也总是被翻译为意义,但其实谈的是一种效果史上的意义,一种我们从术业专攻中领略到的、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意义,所以才有文以载道的说法。做哲学的应当有术业意识,但不应止于这种意识,还应超越它而同时具有很强的闻道意识。你研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同时就是和他们一道,面对他们的问题。这种训练会使你不仅有背景也有能力去面对其他的超专业的问题。 陈嘉映:不要把自己的专业背景看得太重,但是要把自己的专业调动起来,就是专业训练起作用了。 李河:专业训练在这里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塑造学术判断力。学术判断力具有超专业的特性,对于你刚才讲的学界或者共同体,都是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人不管他的具体专业背景怎么不同,但我想他们在学术判断力上应该有类似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家族相似,总之是类似的。他们对于那些超出某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大体也可以听得出来,哪些东西是有意思的,哪些问题可以继续展开的。\n 张志伟:不过,也可以不这么理解。比如,我把哲学问题看作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当然哲学家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每一位哲学家的路子都不一样,那么,我跟着任何一个哲学家最后面对的将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就是一种引导上路的方式。你的基础训练,就类似咱们经常说的理论思维训练,这是学习哲学起码的消极意义。但是训练的结果并不是把它当作一辈子的对象,而是说把我们引向哲学的问题。其实我读海德格尔,我也可以和维特根施坦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样就有一个对话的基础。如果我对话的时候只知道引经据典,用海德格尔去和维特根斯坦对话,那我不过是一个专家,还不能说面对问题。 陈嘉映:我听你们两个发言,我能理解到的就是,要把专业训练带进来,但不要把专业态度也带进来。 彭永捷:是这样。 陈嘉映:引用康德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简便,而不是为了造成障碍。我引用康德,那我是假设你知道康德,一引用就省了好多话。我引用康德并不是因为非得懂康德才行,如果你不熟悉康德的话,我应该能够用别的话说出我所要说的。刚才我引了卢瑟福的话,我们应该能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话说一遍。 彭永捷:这就是我想说的超越。现在学术界关于问题对话已经很多了,重要的是怎么样超越,怎么改变学术生态。我可能现在着重某个学科背景训练,但是我要自觉地接受更多的训练。我得打破这样一个学科界限,我还需要了解很多其他学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搞中哲的有时候希望加强西哲这方面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有意识的自我超越、完善,我逐渐地打破这个限制。我不可能整个的西方哲学都很熟悉,连你们搞西哲的人都不能做到,何况研究中国哲学的。但是我认真去读一两个人,读一两本书,这可以做到吧。这就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远远超越我原来只有一种训练。 这个就走向来讨论可以是第二种哲学对话。这种哲学对话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哲学生态,把这种学科壁垒首先从主观上消除掉。不要总说自己首先是一个西方哲学专家,现在的问题是,你能否也在西方哲学之外去做一个中国哲学专家,认真研究那么一两个人物。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能改变我们以前培养人才的模式和我们搞哲学研究的模式,更值得我们讨论。话题五:学科对话与学术共同体 \n 干春松:我个人觉得,陈嘉映刚才清理了一个问题。以前我们一说起学科对话,那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要跟你对话,中、西、马,好像是说我又懂中又懂西又懂马,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今天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学科对话可能并不是说,我要跟你对话就把我自己变成一个维特根斯坦,变成一个刚才说的超的境界。还是接着李河说的那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共同体的建立是依托于一个什么问题才有可能,但现在的学术生态里很重要的问题正如刚才李河说到,就是中国人说的事儿、中国人从自己的源头说出来的事儿没人管没人理。这是没有共同体、没有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写文章也是这样,引的人越老越好,腕儿越大越好。我们为什么说赵汀阳那个东西值得花功夫去弄?就是要有意识去培养所谓的界,即共同体。我觉得杂志的功能可能要在这里。杂志的功能当然要发表一些专业类的文章,但是还要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可以依托的东西。你或者说它是一个小团体也好,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也好,那问题是,它就自觉地会出来一些事儿,有不同的背景的东西。可能我读海德格尔和你读诲德格尔的出发点、意义都不一样,我去读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成为什么,我可能乱翻,我可能一下子翻到第300页,我不从第1页读,它可能就哪天哪句话蹦出来了,而我理解的这句话可能甚至都不是海德格尔的原义。 彭永捷:我们想一下这个操作层面。假如我们对话,比如我要探讨语言问题,你跟我讲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我们说可以交流呢,实际上是我要先了解一下海德格尔,你才能给我讲清楚;然后我研究中国哲学,你也了解点儿中国哲学的背景,再用我们比较能沟通的语言。实际上,对话过程中就是一个相互学习。我也了解一点儿海德格尔,我虽然不是专家,但我多少对他了解,而且你要真明白海德格尔对那个问题是怎么论述的,你不去看看海德格尔论述这个问题的章节,或者至少去看一些一般介绍性的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