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7 发布 |
- 37.5 KB |
- 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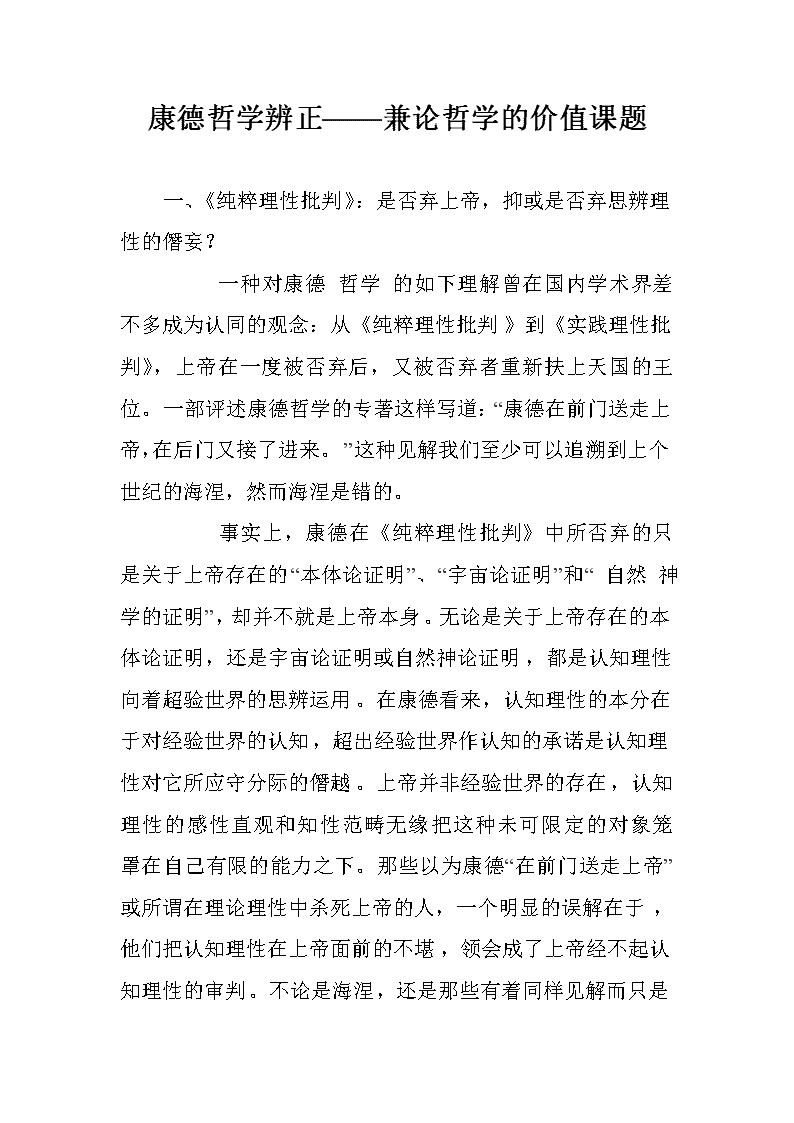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康德哲学辨正——兼论哲学的价值课题
康德哲学辨正——兼论哲学的价值课题一、《纯粹理性批判》:是否弃上帝,抑或是否弃思辨理性的僭妄?一种对康德哲学的如下理解曾在国内学术界差不多成为认同的观念: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上帝在一度被否弃后,又被否弃者重新扶上天国的王位。一部评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这样写道:“康德在前门送走上帝,在后门又接了进来。”这种见解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海涅,然而海涅是错的。事实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否弃的只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n神学的证明”,却并不就是上帝本身。无论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还是宇宙论证明或自然神论证明,都是认知理性向着超验世界的思辨运用。在康德看来,认知理性的本分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认知,超出经验世界作认知的承诺是认知理性对它所应守分际的僭越。上帝并非经验世界的存在,认知理性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无缘把这种未可限定的对象笼罩在自己有限的能力之下。那些以为康德“在前门送走上帝”或所谓在理论理性中杀死上帝的人,一个明显的误解在于,他们把认知理性在上帝面前的不堪,领会成了上帝经不起认知理性的审判。不论是海涅,还是那些有着同样见解而只是变了一种说法的人,至少在他们把《纯粹理性批判》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自然神论证明的否弃看作是对上帝本身的否弃时,他们认可了认知理性效准的无限性,或者也可以说,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这时所执著的正是所谓认知理性一元论。在康德那里,上帝确然是不可“知”的,但不可“知”并不就是不可“达”或不可“致”。不可“知”只是对认知理性效准的有限性的申达,并不意味着对理性——包括理性的实践运用或所谓实践理性——的信念不足。依康德的意思,认知理性只须去认知,这是以经验世界为对象的活动,非感性的领域则非认知的能力所能为。比如价值判断,原是依据意志或情趣所作的“好”与不“好”的分辨,这分辨决不能为认知的“是”与“不是”的分辨所取代。既然在理性的认知向度上,永远不会发生“好”与不“好”的问题\n,那末不论它如何运作和发挥,也决然不会进到价值判断的领域。单就这一点而言,认知理性的效准便不能被认为是无所不在的。换句话说,价值领域对于以“知”为职分的认知理性说来便是不可“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价值判断在实践地对象化到经验世界后,认知理性不能对既成的事实作“知”的条理。康德不曾明确对价值进路和认知进路作如上的划分,但事实上,他对纯粹理性的可能及其界限的探究,亦即所谓纯粹认知理性批判、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判断力批判,却是以这种划分为前提的。一般地说,上帝作为“一切可能的存在中之最完善者”,其“最完善”的规定是价值规定;价值规定必是在价值的向度上,而不是在认知的向度上。因此,依康德《批判》的题中之义,作如下断言是极自然的:任何趋向上帝的努力都只能是价值向度上的事,而不会是认知向度上的事。康德是在”纯粹理性之理想”一章中批判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的;如果我们把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等的驳斥看作是他对他心目中的上帝的消极认可,那末下面这段谈论“神人”理想的话正可以看作是他在上帝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康德说:“德及其所伴随之人类智慧皆为理念。顾哲人则为理想,盖仅思想中所有,完全与‘智慧之理念’相一致之人物。此犹理念授与吾人以规律,理想在此种事例中,则用为模拟人物之完善规定之原型;吾人之行动,除吾人心中所有此种‘神人’之行谊以外,并无其他标准可言,吾人惟与此种‘神人’之行谊相比较,以之判断吾人自身,因而改进吾人自身,——吾人虽绝不能到达其所命定之完全程度。吾人虽不能容认此等理想具有客观的实在,但并不因而视为脑中之空想;此等理想实以理性所不可或缺之标准授之理性,以‘在其种类中乃十分完全事物’之概念提供于理性,因而使理性能评衡其不完全事物之程度乃其所有之缺陷。”\n诚然,这是就作为“完人”或“神人”的那种理想的哲人发论的,但其就“理念”和“理想”所说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作为可能的“最高存在者”的上帝。人性的理念是完满状态的“德及其所伴随之人类智慧”,人性理念的实体化则是作为最完善的人或人的“原型”的“神人”。“神人”为现实的人提供“行谊”的价值标准,它不必是诉诸感性而引起认知活动的“客观的实在”,但也“并不因而视为脑中之空想”。就是说,它不必是感性的真实,却也还是一种真实,这真实是相对于感性真实的“虚灵的真实”。“虚灵的真实”是价值意义上的真实,它不能从只同感性真实发生关系的认知理性那里得到确证,却能从德性修养、境界提升等关乎实践理性的活动中获得认可。在与“神人”同样的理路上,康德也确信作为“元始存在者”或“最高存在者”的“神”,因此,即使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也已经提出了一种所谓“道德的神学”。并且,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神学与试图以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的方式证明上帝存在的“思辨的神学”的不同。他说:“此种道德的神学,具有优于思辨的神学之特点,即道德的神学势必引达‘唯一的一切具足的理性的元始存在者’之概念,而思辨的神学则在客观根据上甚至指示其途径之程度亦无之,至关于其存在,则更不能与人以确信矣。”\n显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并不存在把上帝“送走”的问题,他送走的只是不能引达上帝的“思辨的神学”;此后的《实践理性批判》也不存在对上帝“又接了进来”的问题,因为从价值的进路上引达上帝的“道德的神学”在第一个《批判》那里已经相当真切。康德从一开始阐发“道德的神学”,就不曾抛开上帝在“思辨的神学”那里被赋予的“全能”、“全知”、“遍在”、“永恒”的属性,只是这些属性既然都在价值的向度上,由“道德”的实践契接它们就更顺理成章些。康德指出:“吾人若自所视为世界之必然的法则之‘道德的统一’之观点以考虑‘所唯一能以其适切的结果授之于此种必然的法则,使此种法则因而对于吾人具有强迫力’之原因,必须为何种原因,则吾人自必断言必须有一唯一的最高意志,此种最高意志乃包括一切此等法则在其自身中者。盖若在种种不同意志之下,吾人如何能发见目的之完全统一。以自然全体及其与世界中道德之关系,从属彼之意志,故此‘神’必为全能;以彼可知吾人内部最深远之情绪及其道德的价值,故必为全知;以彼可立即满足最高善所要求之一切要求,故必遍在;以此种自然与自由之和谐,永不失错,故必永恒,以及等等。”不可否认,“批判”是一把双刃的剑,它在否弃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证明的同时,也对运用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等证明方式的人心目中的上帝有所匡正,但这正如上面的引文所表明的那样,并未影响\n康德对上帝的“全能”、“全知”、“遍在”、“永恒”等品质的肯认。上帝并不是可诉诸经验的感性存在,就这一点而言,那些对上帝存在作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证明的人们的观念与康德并无二致,而康德的理性批判的彻底在于,他不像他所批评的人们那样,用认知理性去把握认知理性把握不了的作为超验存在的上帝。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确曾说过“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知识”,但这里的“否定知识”,并不是指否定认知理性在自己的限度内所能达到的知识,而只是如康德所谓在于“剥夺‘思辨理性自以为能到达超经验的洞察’之僭妄主张”。倘在纯粹的认知理性所可达知的范围内,康德不仅不否定知识,反倒对知识有着比信仰更高的评价。但在价值领域,在认知理性不能达知的实践理性的范围内,“知识”是不存在的,对并非感性真实的那种“虚灵的真实”唯有“信仰”。因此康德声明,对于上帝,“我之确信,非逻辑的确实,乃道德的确实”他特别强调说:“因此种确信依据主观的根据,甚至我不可谓‘神之存在等等,在道德上确实’,仅能谓我在道德上确信有‘神之存在等等’耳。易言之,有神及另一世界之信仰,与我之道德情绪,参伍交织,故决无能自我夺去信仰之恐惧,正与我无丝毫理由惧有失去道德情绪相同。”\n康德是审慎而缜密的,他紧紧地把握着价值向度上的“神之存在”,正因为这样,他从一开始就以上述方式把他的“道德的神学”同他所极力反对的“神学的道德”区别开了。二、《实践理性批判》:“至善”只是“矛盾”的“暴露”,抑或还有更深长的意味?如果说对思辨理性的僭妄的否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纯粹理性批判》在康德以伦理为中心的价值探求中不过是一部“消极的”导言,那末别具涵义的“至善”概念的确立,则可看作“积极的”《实践理性批判》的“终局目的”。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对“至善”作某种与这一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相称的探讨,前文提到的那部专著或可看作对“至善”评述较多的文字,但作者的结论性的说法却是这样:“‘至善’概念实质上是宗教性质的,它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在于突出地暴露了康德伦理学以及康德整个思想发展行程中的矛盾,即由超感性的纯粹理性逐渐进入感性现实的人类活动及其历史探求中所必然遇到的矛盾。”他对“效果仅为消极”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解也许“积极”了些,而对“积极”的“至善”概念的理解却不免有些“消极”了。这理解除开更多地强调了康德哲学思想中的“矛盾”的“暴露”外,也在指出“至善”的“宗教性质”的同时,为它下了“向当时的宗教势力屈从退让”的断语。“至善”原是一个古老话题的重新提起,它意味着把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终极性追问及其解答作为哲学的重心。“哲学在古人看来原是指教人什么才是‘至善’\n的概念,并指教人什么是求得它的行为的”,——康德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主张,——“我们最好还是维持这个名词的古义,而在理性努力经营使其成为一门学问的范围内,把它理解为求达至善之术。”从康德为哲学所作的这个界说看,我们或可以这样理解康德哲学:这个通过理性的批判开辟道路的哲学,是以人生价值的探索为使命、以对“至善”及其求取之道的指点为归摄的。康德哲学有其独到的认识论,但这认识论——它在《批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更多地只是用来烘托一种价值观的;康德哲学也有其独到的本体论,但那本体论上的境界不是经由认识的途径而是经由价值的途径获致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及“视为纯粹理性终极目的之决定根据之最高善理想”时写道:“我之理性所有之一切关心事项,皆总括在以下之三问题中:我所能知者为何?我所应为者为何?我所可期望者为何?\n第一个问题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第二个问题是《实践理性批判》的伦理学的主题,第三个问题是经由第二个问题引出的问题,即“至善”问题。这二、三两个问题的关联则诚如康德所作的推绎:“我如为我所应为者,则所可期望者为何?”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以“爱智”把第二个问题关联于第三个问题,又以“爱学”把第一个问题也关联于第三个问题。他解释“爱学”说:“爱学,即爱全部思辨理性知识的那个含义,而并不至于使人忘却它所能唯一借以称为智慧的那个主要目的。”这即是说,认知理性原只是“学”,它只有在帮助实践理性求致“至善”因而借此把自己系于那种“至善”关切时,才可能被称为“智”。从康德对哲学所作的界说及他在理性范围内提出的三个问题看,我们有理由说,把握了康德的所谓“至善”,也就把握了康德哲学的最高问题,而“至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终极眷注或最圆满的“好”的价值问题。康德在他的生命进到最后一个十年时,亦即在完成了三大批判之后,接着上述三个问题提出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对此康德并没有径直作出回答。但就康德所提四个问题的内在关联看,这里似乎可以这样设想康德的答案:人是能通过“理性努力”自觉求达“至善”或“圆满的善”的生灵。在古希腊哲人那里,“至善”观念是基于对“德性”和“幸福”的同一性的认可的,但不同的出发点使他们在同样的思维方式的误导下各自走向一偏。伊壁鸠鲁派依据感性需要把人所应得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原则,在他们看来自觉到自己的准则可以获致幸福,那就是德性;斯多葛派则把独立于一切感性动机的德性作为自己的原则,在他们看来自觉到自己的德性就是幸福。分析\n的原则——从幸福中分析出德性,或从德性中分析出幸福——使他们在幻觉中走向“至善”,打掉逻辑的附会,真相却只是这些从“同一性”出发的人们终久盘桓在各自的原点上半步未进。康德也是在德性与幸福的联结上求取“至善”的,但他认为:“幸福和道德原是至善里面所包含着的两个完全种类不同的要素,因此,它们的结合是不能在分析方式下认识到的,而只是两个概念的综合。”不过德性和幸福作为至善的两个要素,在康德那里决不是秋色平分的,而“综合”也并不依从任何经验的原则。“通过意志自由来实现至善,乃是一种先天的必然”,对这一“必然”的肯认,使康德的至善追求走上一条独辟的蹊径。对于康德说来,道德作为至善的第一要素,是不受任何因素或条件制约的至上的善,它使至善具有一种至上性,幸福则只是在为道德制约并作为修德的必要结果的前提下才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它与道德修省状况的配称一致使至善成为善的无可添加的全体而赋有圆满性。因此,至善的实现首先意味着以至善为鹄的的意志同道德法则完全契合。但这圆满契合是任何有理性的存在者在其有限的生存期间都不可能达到的,它只虚灵地呈现在有理性的存在者无止境地趋向它的努力中。德性修省的无底止须得以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和人格无底止地延续为前提,这即是说,要使至善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只有悬设所谓灵魂不死。康德承认灵魂不死在理论\n上是无从证明的,但它却为先天而无制约地有效的实践法则所要求。然而灵魂不朽悬设下的无限的德性修省所能寄望的至上的善只是显示了至善的高卓,还不就是至善的圆融。至善不是把至上的善的德性孤峭地悬置在人的感性生活之外,它的圆成还有待与德性相配称的幸福。幸福,依康德的界说,“乃是尘世上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生中所遇事情都称心合意的那种状况”。作为人的生存境遇的一种尽可能好的改善,幸福把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希冀引向一个极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然同人的意志法则以及把这一法则立为最高的意志动机时的法则和谐一致。然而极善世界不过是最高的派生的善,对最高的派生的善的悬设意味着对最高的原始的善的悬设,亦即对上帝存在的悬设。如果说“灵魂不朽”的悬设,主要在于保证永无止境的德性修省以体现“至善”的至上性,那末,“上帝存在”的悬设则在于确保尽可能多的幸福对于处在不断提升中的德性的精确配称。“神学的道德”的根源处是神秘的,但主张“道德的神学”的康德却并不掩饰自己悬设上帝的初衷。他说:“依照世界中单纯自然过程来讲,与道德价值精确相应的幸福原是期望不到,并且应当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而从这方面说来,只有在一位道德的‘主宰’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承认至善的可能性”。“道德的‘主宰’”给予至善的是“决定终局的道德的关切”,康德在这里再一次道破了“道德的神学”中的上帝的秘密:“道德法则是借着作为纯粹实践理性对象的至善这个概念,才决定了作为最高实有的‘原始实有’\n这个概念的:这个结果是物理进程所不能达到的,因而是全部思辨理性进程所不能达到的。因此,‘神’的概念原非属于物理学,即不属于思辨理性,而是属于道德学的一个概念。”一般地说,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人文意识的主导祈向是由认可人的肉体感受性而必致的“幸福”。只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才成为批判哲学家的康德,悬设“上帝存在”以作为“至善”的托底的概念,与其说康德是“向当时的宗教势力屈从退让”,不如说是对本然意义上的基督教的正面价值与当时启蒙思潮所肯认的时代价值作一种历史的契接。这契接出于一种现实关切,而在“至善”的逻辑彻底处也正关联到人类的终极眷注。可以理解的是,“幸福”价值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那里的至上化,曾有效地冲击过“他律”的神学的道德,它使那些被中世纪教会贬斥为过恶的人的肉体感官欲望从桎梏中获得解放。但由此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却是道德的神圣感的黯淡和人在物欲、肉欲、权力欲中的可能的陷溺。“意大利在十六世纪初已经发现它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间,就是最好的人也逃脱不掉”。而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当“百科全书派”的人们还醉心于“幸福”价值而对科学和理性寄予过高的企望时,卢梭——一位对后来的康德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早就以他悲郁的文字为那明快的乐观色调投下了阴影。他戒告世人:“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n进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在时代的沧桑之变中,康德作为启蒙思想家从未忘记过他所把握的“启蒙”的主旨。在他看来,“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同时,他也从未轻觑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所一再宣示的满足人的肉体感受性的幸福的价值。但康德毕竟又是一位更深睿的哲学家,他要在肯定人的幸福价值的同时肯定人的道德价值,并把前者置于后者的制约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既对启蒙思潮有批判的继承,也对历史地存在着的基督教有批判的继承,而且,倘作一种更远的追溯,我们还可以从对他的“至善”观念有过重大影响的古代哲学家中举出柏拉图、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究元”意味上的“至善”是至高的道德与充量的幸福的极完满的配称一致,它在感性的人文世界中也许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它的虚灵之光却永远吸引着人的向善的心灵。人对幸福的眷注,人对德性境界的眷注,人对身心幸福与德性境\n界配称一致的眷注,并不限于某个时代或某个民族的特殊意向;它具有终极意义,因而它属于人类的终极眷注。“应然”的世界并不像“实然”的世界那样可以用认知理性作尽可能精确的量度,但“应然”只要是真正的“应然”,——例如“应当”德性高尚,“应当”配称于这高尚德性以相应的“幸福”,——那就应当被视为一种真实,不过这不是经验的或感性的真实,而是与人的真切意向同在的“虚灵的真实”。不论康德对“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悬设为人们留下了多少可批判或品评的话柄,他由这些悬设而确立的“至善”目标,却由一种永远当有的“应然”为可能出现于历史中的经验的“实然”世界提供了终极性的价值标准,——评判的标准和理想的标准。三、《判断力批判》:主题在于“美”,抑或在于“人”?“美”的问题与“人”的问题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不存在旨趣上的分异,但领悟的重心在二者间的或此或彼,对于《判断力批判》的总体理解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前文提及的那部“康德述评”的作者看来:“本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只讲美学。随后有了目的论判断,但整个只作为附录。”说“目的论判断”在《判断力批判》中“整个只作为附录”,显然不是事实,而发论者紧接下来所写的文字则不啻为一种自我矫正,他说“在第一版,目的论很大一部分,如第79节以后都还是《附录》。到第二版才去掉‘附录’\n的标题。”但即使从矫正后的说法也可以看出,发论者是把“美”的问题作为《判断力批判》的主旨所在的。在对《判断力批判》的“美学”把握后面,左右把握的实际是发论者的这样一个观点:“真、善、美,美是前二者的统一,是前二者的交互作用的历史成果。”这一观点是否允当是可以另作讨论的;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以“美学”为《判断力批判》的主旨乃至把“目的论判断”看作是该书的赘疣可能并不妥当。且不去说《判断力批判》下卷即使在第一版正文中也已经系统阐发了为“美学”所不能包容的“目的论判断力的分析论”和“目的论判断力的辩证论”,单是就全书的“导言”看,康德也是把“自然的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以对列的方式论说的。康德指出:“第一种合目的性的表象是建基于单纯对对象形式的反省中而直接感到的愉快上面。而第二种的合目的性的表象却和对于物的愉快情绪毫无关系,因为物体的形式不是和主体在对物的把握中的认识机能相联系,而是在给定概念下和对象的特定认识相联系,和对物判定的悟性相联系。”\n不论关于“审美判断力”的论说在《判断力批判》中占了怎样的篇幅因而怎样重要,它却只是被统摄在“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命意下的;而且,不论对“目的论判断力”的论说在一些批评者看来怎样地“不需要”,它却也同样地体现着原作者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的信念。“审美判断力”对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论证不能尽其致,因此“自然的合目的性”只把“审美判断力”归置为它所必要的论证的蹊径之一。就康德的本意看,他的“美学”原是由“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必得说明而带出来的,《判断力批判》的主旨并不落在“美”的问题上,而是落在由“自然的合目的性”所指向的“人”的问题上。不同理解引达的是问津康德哲学者对“美”在“人”的问题上的分际把握的各异。前一种理解把“人”的问题归结为“美”的问题,其观点诚如前文引述的所谓“真、善、美,美是前二者的统一”;后一种理解则把“美”的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因此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美”,如同“真”、“善”一样,只是“人”的问题的一个向度,一个并不能统一“真”、“善”,也不能被“真”、“善”所统一的向度。但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判断力批判》一书本身,回到“自然的合目的性”问题,因为“自然的合目的性”何以引达和怎样引达了“人”的问题,尚需要审慎地申论。三个《批判》中,“实践理性批判”比起“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来,其独特而最堪注重的意义在于,它经由道德价值的探讨把全部问题引向“人”,它对道德价值的神圣性的证可本身即是对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确定。“人格”和“人道”问题,人作为价值主体的问题,不是纯粹认知理性或纯粹判断力在自己限度内能够独立问津的,但实践理性即使完全不凭藉认知理性和判断力也对问题的解决足以胜任。康德指出:\n“人类诚然是够污浊的;不过他必须把寓托在他的人格中的人道看作是神圣的。在全部宇宙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一切东西都能够单纯用作手段;只有人类,以及一切有理性的被造物,才是一个自在目的。那就是说,他借着他的自由的自律,就是神圣道德法则的主体。”从康德的表述看,“人是目的”不过是人是价值主体的同义语,尽管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范围内“价值”主要是指赋予“人格”、“人道”概念以内涵的道德价值。纯粹认知理性的问题不是价值问题,作为认知理性对象的感性自然界也不存在价值问题,但一当它们同被那纯粹实践理性证可为价值主体的人关联起来,或者说,一当它们被引向“人是目的”的价值命题,它们对于人也就有了价值。“判断力批判”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认知理性,把自然概念的领域置于“人是目的”的价值之光的照耀下,使那自身不发生价值判断的东西由人赋予它们以价值。康德在批判地考察了纯粹思辨理性和纯粹实践理性之后发现:“在自然概念领域,作为感觉界,和自由概念领域,作为超感觉界之间虽然固定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致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有过渡,好像是那样分开的两个世界”,然而他认为,“前者对后者绝不能施加影响;但后者却应该对前者具有影响,这就是说,自由概念应该把它的规律\n所赋予的目的在感性世界里实现出来;因此,自然界必须能够这样地被思考着: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那些按照自由规律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互相协应的”。实际上,“自由概念的领域”对于“自然概念的领域”,在“应该”意义上的“影响”,在康德那里是经由“判断力”的两种途径揭示的:一是审美的方式,一是“目的论”的方式。审美带给人以“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但这表象中的“合目的性”却又是无目的的。就其无目的而言,它通着“自然概念的领域”,就其“合目的性”而言,它又通着“自由概念的领域”;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由此得以契接,相关于自然的认知和相关于自由的欲求也因着相关于审美判断力的愉快或不快而得以贯通。愉快与不愉快情绪是发自人这个审美主体的,而审美主体同时也是道德主体,所以审美主体对愉快的感受必然关涉到这主体所本具的道义观念和道德感情。在康德看来,“人的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因此他也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但康德决不曾简单地把审美判断归结为道德判断,他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种“止基于客观规律的兴趣”,而审美判断是一种“自由的兴趣”。同时,他又指出:“那对自然的惊赞,这自然在它的美丽的产品里表示为艺术\n品,不单是由于偶然,而好像是有意的,按照合规律的布置,并且作为合目的性而无目的;这目的,我们在外界是永不能碰到的,我们自自然然地在我自己内里寻找,并是在那里面,即在那构成我们生存的终极目的,道德的使命。”审美判断的“合目的性而无目的”,也是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的“无目的”而具“合目的性”。这“合目的性”既然只能“自自然然地在我自己内里寻找”,它便只是所谓“主观的合目的性”。而“主观的合目的性”的可能的基础,却须得在“目的论”里去寻求。康德鄙弃把自然看作是“偶然的体系”或“宿命论的体系”的“目的性的观念论”,也鄙弃主张“物活论”或“有神论”的“目的性的实在论”。他从有机物的生命机制推扩开,把问题的思考引向另一条途径。在他看来,有机自然物中,“所有一切部分都是交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在这样一个产物里面,没有东西是无用的,是没有目的的。”从有机自然物的这一内在机制推至整个自然界,他得到了“整个自然作为按照目的的规则的一个系统”的观念。但认可自然系统的内在目的性,必致问及自然的“最后目的”;这个“最后目的”是新目的论得以成立的一个“无条件的条件”,它显然处在物理目的论世界的研究范围之外。康德循着他的独特的逻辑线索寻找,找到了“人”——“作为本体看的人”。他说:\n“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只有一类的存在者,其因果作用是目的论的,那就是说向着目的的,而同时它们是这种性格的,就是它们按照着来为它们自己确定其目的的规律是它们想像为无条件的并且不依靠自然的任何东西的,而是在其本身就是必然的。这类的存在者就是人,可是是作为本体看的人。”“作为本体看的人”和作为现象看的人的区别在于,它不纠缠在因果必然的链条中,而在实践理性的意义上获得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在《判断力批判》中我们也读到这样一些文字:“在我们假定世界的东西,在其真正的存在看来都是有所依靠的,而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就需要一个按照目的而行动的最高目的,这个时候,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善的意志是人的生存所能唯一借以有其绝对的价值,而且与之有着关系,世界的存在才能有一个最后目的的。……只有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来说,人才能是世界的最后目的的。”这依然是“人是目的”的话题,不过已经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人是目的”的命题的扩展。《实践理性批判》所说的“人是目的”还仅限于所谓“自由概念的领域”,《判断力批判》说的“人是目的”是经由判断力——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把意义从“自由概念的领域”辐射到“自然概念的领域”的。所谓“目的”,总意味着一种价值取向,目的系统其实即是价值系统。从“现象”到“本体”即从“自然”到“自由”,“目的论判断”以人的双重地存在——作为现象或自然的存在和作为本体或自由的存在——而又终是一体的这一“反省”,终于完成了作为“知性”对象的“自然概念的领域”向作为“理性”对象的“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过渡。\n至此,审美判断从主观形式上所判定的“自然的合目的性”,才真正有了它的可能的基础,用康德的话说,这即是:“一经为有机体里面实际上对我们呈现出来的自然目的所支持的对自然的目的论鉴定,使我们能够形成关于自然目的的一个巨大的系统这个观念,那时我们就可以从这种观点来甚至看自然的美了,这种美乃是自然和我们从事于抓住并且鉴定自然所出现的东西的认识能力的自由活跃的一致。因为那时,我们就可以把自然的美看为自然在其整体作为一个系统的一种客观目的性了。”四、哲学不能没有它的价值命意康德哲学对人类心智的启迪也许是多方面的,他那用“灰色、枯燥乏味的包装纸一般的文体”写下的《批判》,是一份经心的人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遗产。这里只是想从“知性”、“理性”和“反省判断力”的错落处引发一种“价值”思考,让过分逻辑化了的哲学反省自己的逻辑。认知问题是“是”与不“是”的问题,价值问题是“好”与不“好”的问题;前者在于从感性对象求得知识,后者在于对实践中的人或事物作出评判或决断,对那些堪称虚灵的真实的东西确立相当的信念并诉诸自律的修为。哲学并不就是伦理学\n、美学或宗教学,但它应当为真、善、美、幸福、尊严、高尚、神圣……价值提供相应的哲理,这正像哲学并不就是科学但却有义务为科学提供认识论或方法论原则一样。康德哲学的特色或可归结于两点,一是它对认知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执著分辨,二是它从价值进路而不是认识进路把握“本体”。不论人们对这位批判哲学家否定认知理性直接逼近“本体”的可能性作怎样的诘难,他出自实践理性优于认知理性的论断对人生意义或价值作某种终极性的探询,却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块须得人们仰视才见的丰碑。价值生发目的,目的涵润理想,存在于人的价值祈向上而为实践的价值系统所指示的理想往往显现着人的生命的另一重真实。人的生命活动的第一个对象是自然\n界,就人有求于自然、有赖于自然因而受制于自然而言,人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但人的“受动”存在状况并不像动物那样是一个被自然界给定界限的常数,人能打破自然加于自己的界限而获得又在被打破中的新的界限,因而人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作为“受动—能动”的自然物是由于人自己,或者说,人在这种“受动—能动”的存在中自己是自己的根据、自己是自己的理由。这“自己是自己的理由”的意致用一个相宜的概念作表达,即是自由。因此,也可以说,人作为一种“受动—能动”的“自然”存在,同时即是一种“自由”——有别于动物的“他由”——的存在。“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它的客观表达在于对象世界依着人的目的、意向、情趣的改变。人在自己的对象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向、情趣是所谓“对象化”,这“对象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特征,既涵淹着人的生命活动的合目的性,也涵淹着人的生命活动的合规律性。人在他的“受动—能动”的自然存在亦即“自由”的自然存在中,创造着有别于自然世界的人文世界,这使它成为“受动—能动”的社会存在物和“受动—能动”的历史存在物。如果依人们通常易于接受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按照“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历史存在”的逐层丰富的云谓加以规定,那末人的“受动—能动”性或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性质,则意味着人对自己在自然、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的毫不含糊的肯认。即是说,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性质决定了人永远是自然、社会、历史的主体,自然、社会、历史永远是人的存在对象,是人在不断从“偶然的个人”上升为“有个性的个人”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着的价值、目的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是目的”,但康德的命题在这里有了怎样的转进是一目了然的。\n倘把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人的存在对象,人还可以被看作是“受动—能动”的精神存在物。人在精神领域的“受动—能动”性可以从人的心灵的“反思”和“反省”活动中得到理解。“反思”是指人对作为历史的既在的精神成果的再思考,也指人对经验中获得的认识的再思维,它关乎理智的知识在扬弃中的更新和感性直观认识向认识的知性构造形态的推进。“反省”一方面指人对自己心灵活动律则的省察,由此而有逻辑学和一定形态的心理学;一方面则指人在价值修为中的自衡和自律,由此而有所谓人的精神境界。“反省”的后一方面多在于道德的践履,它以对“人格”的成全相对独立地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性质。无论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见诸对象化的向度,还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省的向度,都既有关乎所谓规律性的认知理性问题,又有关乎所谓目的性的价值理性问题。而且,“价值”总是以“应该”或“值得”的判断为认知过程选择方向或为认知结果作出安排。人的审美活动的“无目的的目的”是以人为目的,它不无直观认知的功能,但它也同时把一种“美”的价值带给人的价值世界。诚然,离开“真”与“善”,“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即是“真”与“善”的统一。中国后世儒者在价值问题上的一种偏至在于以“善”统一“真”、“美”,西方最有成就的思辨哲学家黑格尔却在他的整个体系中把“美”、“善”统一于“真”;结果前者独钟于“善”反倒使“善”落于寡头化而成一泛道德主义的格局,后者执著于“真”以致使“真”囿于逻辑强制而成一泛逻辑主义的格局。“美”不必称羡“真”、善”曾被人给予的价值一尊的地位,“真”、“善”、“美”倘一定要求得某种统一,那也只能统一于人的“自由”而非“他由”的生命活动,统一于所谓“人是目的”,尽管这期间“善”直接贞定着人的“人格”而显得更具主导意义。\n作为哲学对象的价值范畴或者还有很多,康德在“人是目的”的意义上确立“至善”概念时说到了“德性”和“幸福”及其配称一致,而在比较古希腊几个学派和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时,他说到了“素朴”、“聪明”、“智慧”和“圣洁”。事实上,我们至少还可以举出相对于执著的“逍遥”或“洒脱”,相对于局守的“通达”或“通灵”,相对于牴牾的“协调”或“和谐”,相对于卑怯的“勇敢”或“无畏”,相对于偏颇的“完满”或“圆融”……。如此之多的价值观念关联于人的现实关切乃至终极眷注,会成为一种怎样的价值格局?这是哲学的“价值”课题。它很可能涵盖了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但既然用了“价值”的名义,它便不会为所涉及的学科的边界所封限。就这一点而言,康德哲学的魅力或者主要不在于它的“批判”的逻辑格度,而在于“批判”中的智慧启示。注释:、、、、、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313-314、315、407、407、407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12—413、555、556、19、19、560、564、564、549-550、550页。\n、、、、、、、、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1、111、115-116、116、127、147、147、142、89页。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23页。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6—147页。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13、145、201、146、146页。、、、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99-100、100、110、30页。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