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1 发布 |
- 37.5 KB |
- 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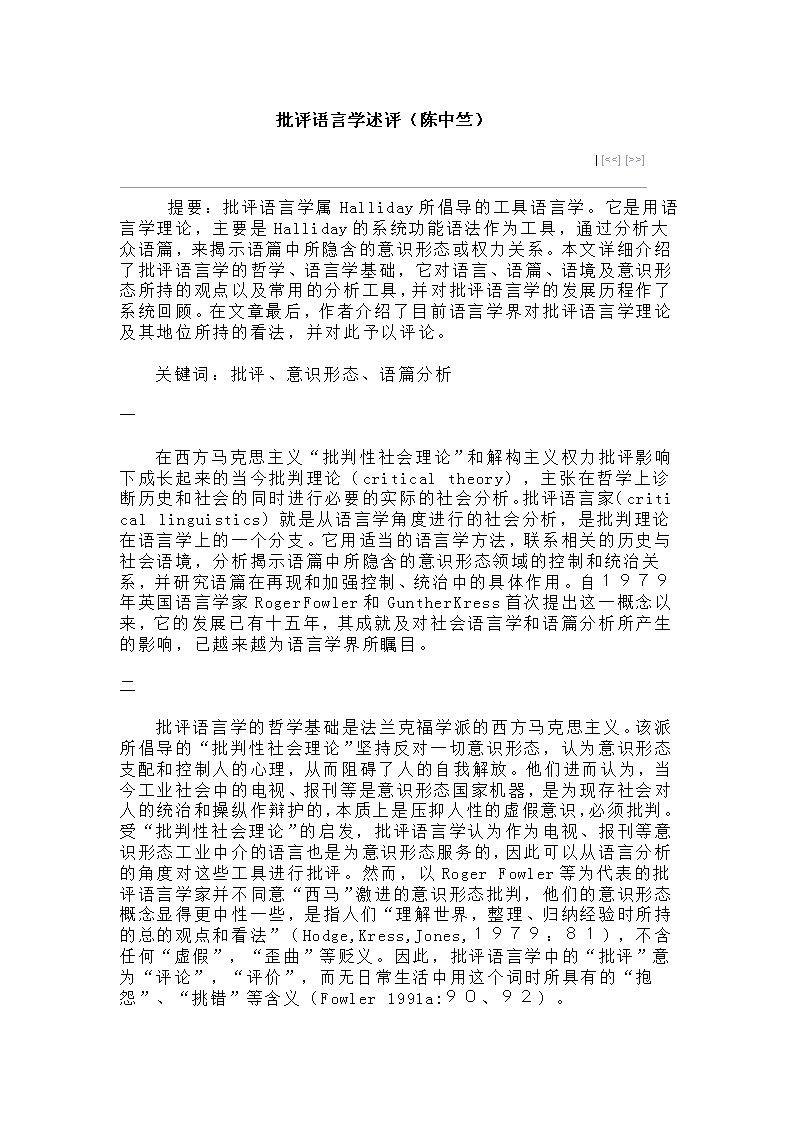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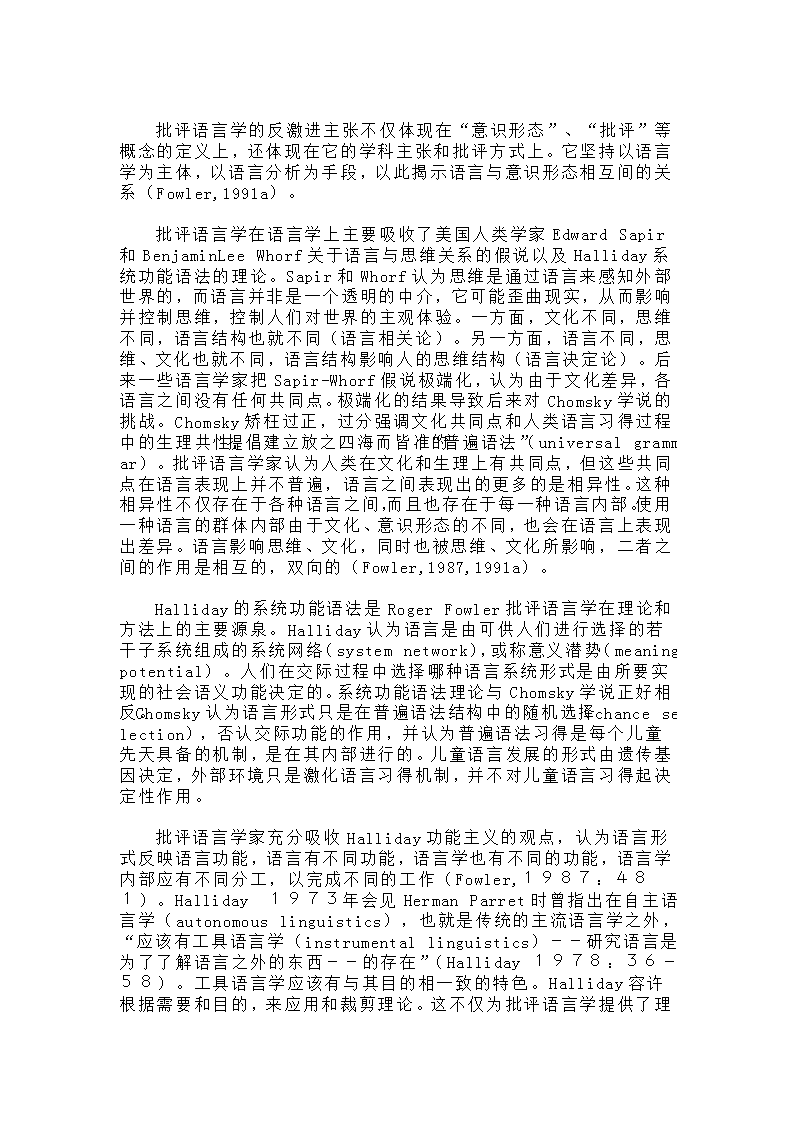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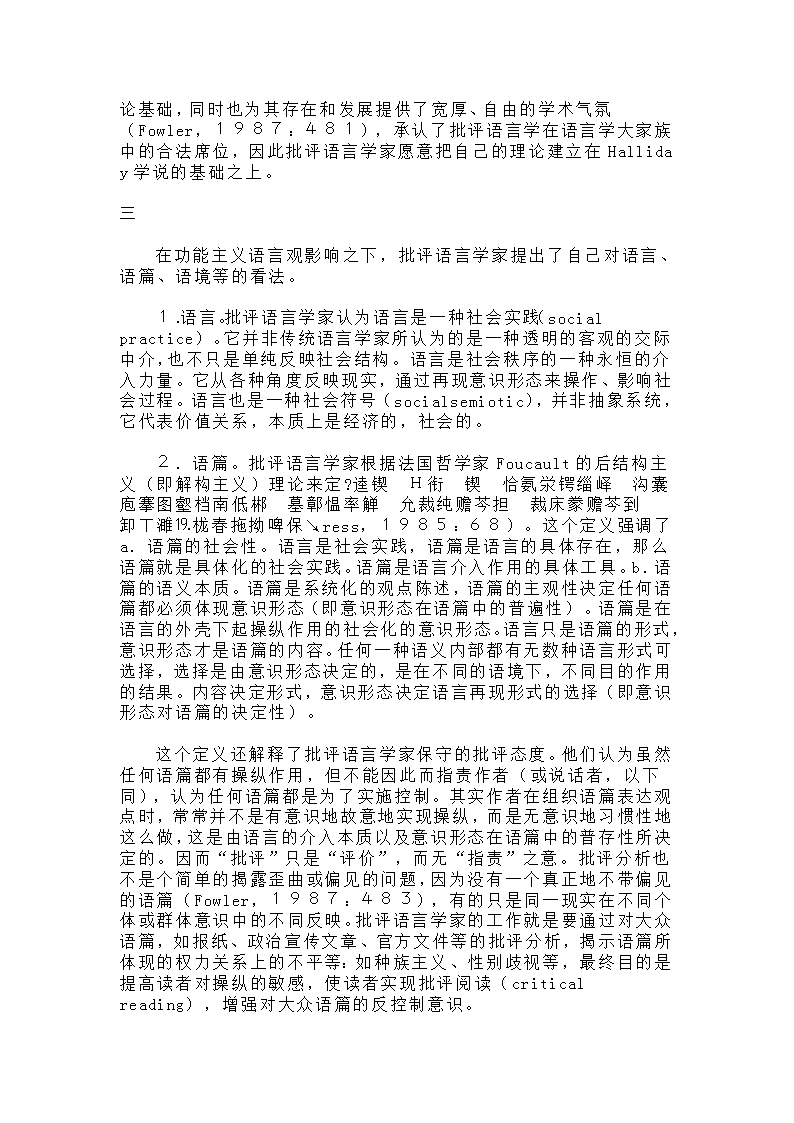
申明敬告: 本站不保证该用户上传的文档完整性,不预览、不比对内容而直接下载产生的反悔问题本站不予受理。
文档介绍
关于语言学批评
批评语言学述评(陈中竺)| [<<] [>>] 提要:批评语言学属Halliday所倡导的工具语言学。它是用语言学理论,主要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工具,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来揭示语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本文详细介绍了批评语言学的哲学、语言学基础,它对语言、语篇、语境及意识形态所持的观点以及常用的分析工具,并对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回顾。在文章最后,作者介绍了目前语言学界对批评语言学理论及其地位所持的看法,并对此予以评论。 关键词:批评、意识形态、语篇分析 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社会理论”和解构主义权力批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今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主张在哲学上诊断历史和社会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实际的社会分析。批评语言家(criticallinguistics)就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社会分析,是批判理论在语言学上的一个分支。它用适当的语言学方法,联系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语境,分析揭示语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统治关系,并研究语篇在再现和加强控制、统治中的具体作用。自1979年英国语言学家RogerFowler和GuntherKress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它的发展已有十五年,其成就及对社会语言学和语篇分析所产生的影响,已越来越为语言学界所瞩目。 二 批评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该派所倡导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坚持反对一切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支配和控制人的心理,从而阻碍了人的自我解放。他们进而认为,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电视、报刊等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为现存社会对人的统治和操纵作辩护的,本质上是压抑人性的虚假意识,必须批判。受“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启发,批评语言学认为作为电视、报刊等意识形态工业中介的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因此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对这些工具进行批评。然而,以RogerFowler等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并不同意“西马”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显得更中性一些,是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Hodge,Kress,Jones,1979:81),不含任何“虚假”,“歪曲”等贬义。因此,批评语言学中的“批评”意为“评论”,“评价”,而无日常生活中用这个词时所具有的“抱怨”、“挑错”等含义(Fowler1991a\n:90、92)。 批评语言学的反激进主张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批评”等概念的定义上,还体现在它的学科主张和批评方式上。它坚持以语言学为主体,以语言分析为手段,以此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相互间的关系(Fowler,1991a)。 批评语言学在语言学上主要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EdwardSapir和BenjaminLeeWhorf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以及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Sapir和Whorf认为思维是通过语言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而语言并非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它可能歪曲现实,从而影响并控制思维,控制人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一方面,文化不同,思维不同,语言结构也就不同(语言相关论)。另一方面,语言不同,思维、文化也就不同,语言结构影响人的思维结构(语言决定论)。后来一些语言学家把Sapir-Whorf假说极端化,认为由于文化差异,各语言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极端化的结果导致后来对Chomsky学说的挑战。Chomsky矫枉过正,过分强调文化共同点和人类语言习得过程中的生理共性,提倡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语法”(universalgrammar)。批评语言学家认为人类在文化和生理上有共同点,但这些共同点在语言表现上并不普遍,语言之间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相异性。这种相异性不仅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内部。使用一种语言的群体内部由于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会在语言上表现出差异。语言影响思维、文化,同时也被思维、文化所影响,二者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双向的(Fowler,1987,1991a)。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是RogerFowler批评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源泉。Halliday认为语言是由可供人们进行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network),或称意义潜势(meaningpotential)。人们在交际过程中选择哪种语言系统形式是由所要实现的社会语义功能决定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与Chomsky学说正好相反。Chomsky认为语言形式只是在普遍语法结构中的随机选择(chanceselection),否认交际功能的作用,并认为普遍语法习得是每个儿童先天具备的机制,是在其内部进行的。儿童语言发展的形式由遗传基因决定,外部环境只是激化语言习得机制,并不对儿童语言习得起决定性作用。 批评语言学家充分吸收Halliday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反映语言功能,语言有不同功能,语言学也有不同的功能,语言学内部应有不同分工,以完成不同的工作(Fowler,1987:481)。Halliday 1973年会见HermanParret时曾指出在自主语言学(autonomouslinguistics),也就是传统的主流语言学之外,“应该有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linguistics)--研究语言是为了了解语言之外的东西--的存在”(Halliday\n1978:36-58)。工具语言学应该有与其目的相一致的特色。Halliday容许根据需要和目的,来应用和裁剪理论。这不仅为批评语言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宽厚、自由的学术气氛(Fowler,1987:481),承认了批评语言学在语言学大家族中的合法席位,因此批评语言学家愿意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Halliday学说的基础之上。 三 在功能主义语言观影响之下,批评语言学家提出了自己对语言、语篇、语境等的看法。 1.语言。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practice)。它并非传统语言学家所认为的是一种透明的客观的交际中介,也不只是单纯反映社会结构。语言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它从各种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语言也是一种社会符号(socialsemiotic),并非抽象系统,它代表价值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社会的。 2.语篇。批评语言学家根据法国哲学家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理论来定?逵锲H衔锲恰氨泶锷缁峄沟囊庖搴图壑档南低郴墓鄣愠率觯允裁纯赡芩担裁床豢赡芩到卸ㄒ濉⒚栊春拖拗啤保↘ress,1985:68)。这个定义强调了a.语篇的社会性。语言是社会实践,语篇是语言的具体存在,那么语篇就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语篇是语言介入作用的具体工具。b.语篇的语义本质。语篇是系统化的观点陈述,语篇的主观性决定任何语篇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普遍性)。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语篇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语篇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部都有无数种语言形式可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目的作用的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即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决定性)。 这个定义还解释了批评语言学家保守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虽然任何语篇都有操纵作用,但不能因此而指责作者(或说话者,以下同),认为任何语篇都是为了实施控制。其实作者在组织语篇表达观点时,常常并不是有意识地故意地实现操纵,而是无意识地习惯性地这么做,这是由语言的介入本质以及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普存性所决定的。因而“批评”只是“评价”,而无“指责”之意。批评分析也不是个简单的揭露歪曲或偏见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地不带偏见的语篇(Fowler,1987:483),有的只是同一现实在不同个体或群体意识中的不同反映。批评语言学家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对大众语篇,如报纸、政治宣传文章、官方文件等的批评分析,揭示语篇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上的不平等: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最终目的是提高读者对操纵的敏感,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nreading),增强对大众语篇的反控制意识。 3.语境。批评语言学家强调批评分析离不开语境,认为语言结构与其语篇意义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语境中会有不同含义。例如被动语态在新闻报道暴力事件中的意义显然与科技文章中的被动语态含义不一样。因此,批评分析必须联系语境。 批评语言学家对大众语篇进行批评分析,揭示体现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主要分析工具是现代语言学,而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下面就是批评语言学家经常使用的几个主要的语言学分析工具。 1.及物系统(transitivitysystem)。Halliday把语言的元功能(metafunction)分为三种:概念功能(ideational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function)。及物系统就是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Halliday的及物性与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有着根本不同。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是指动词带不带宾语,如在“Thelioncaughtthetourist”和“Themayorresigned”两句话中,前者的动词是及物的,后者的动词是非及物的。这种区分显然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各种动词之间的语义区别,从而也忽略了各种小句的区别。如在“Hehatedthelion”这样一个句子中,“hated”与上例中的“caught”同属及物动词,但已不再是一个象“caught”一样的物质过程,而是一种心理过程。可见,动词之间远远不只有“及物”?和“不及物”之间的差别。Halliday认为及物系统是语言再现的基石,其作用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在句中表达成若干种过程,并指明各种过程的参加者和环境成分。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现实世界中的同一过程,在语言上却可用及物性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或者用同一种过程,但变换参与者的位置。选择哪一种过程,怎么安排参与者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给语篇中每一个小句的过程进行分类,并研究过程与其参加者和环境成分的关系,如该过程是否影响其它实体,物质过程的目标是否是动作者本身等,可以揭示语篇所隐含的意义与目的。 2.人际功能系统。人际功能表达作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以及他对事物的推断等功能。它直接与态度、观点等相连,是一条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 RogerFowler在LinguisticCriticqsm书中举出以下例子来说明英语中对人的称呼怎样典型地体现作者的态度。下面是三条新闻的标题,分别取自1976年12月12日的《观察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星期日电讯报》。 1)NUSregretsfuryoverJoseph. 2)StudentleaderscondemninsulttoKeith\nJoseph. 3)Studentchiefs‘regret’attackonSirKeith. 1976年12月10日,NUS(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开会时,保守党国会议员Keith Joseph爵士企图旁听,遭到学生攻击。学生代表当场投票一致同意把他赶出去。第二天NUS执委们发表了一个不太真诚的道歉声明。这三条新闻所报道的就是该事件。虽然是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但《观察家报》在提取KeithJoseph时只提及其姓,无其名,也无其称号,显得不够尊敬。而《星期日电讯报》则称KeithJoseph为SirKeith,用“爵士”称号表示尊敬,只有名无其姓显示亲密。两种报纸的两种不同称呼是与这两种报纸所执行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观察家报》宣称崇尚自由,不会同情KeithJoseph。而《星期日电讯报》是一份政治思想偏右的报纸,因而尊敬象KeithJoseph这样的政客。和这两报相比,《星期日泰晤士报》的“KeithJoseph”称呼要中性一些,情态色彩少一些。 在人际功能中,另一个对批评语言学很有帮助的分析工具是英国语言学家Austin和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speechact)理论。言语行为指的是一段言语(书面的或口头的),如果场合适当,并与有关规定相符,便构成一种行为。如开会时,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开始”,会议就开始了,主席的话就构成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强调场合的合适性,如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还强调言语行为的施动者身份的适当性,因此,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规范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又构成社会和政治体系。言语行为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又在新闻报道等大众语篇中极为常见,因而是批评语言学家揭示意识形态的常用工具。 3.转换。转换(transformation)是一种句法关系。批评语言学家不仅进行语义分析,而且分析句法,分析句子成分的不同位置和顺序所显示的不同语篇意义。有两种转换最为重要,一是语态,即被动与主动的转换,再一个就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 先看两个新闻标题(参阅Fowler,1991b): 1) PCshotboyfrom9inches. 2) Robber’sson,five,Killedinhisbed. 上面两个例子分别取自1986年6月1日英国《东部日报》和《太阳报》。报道一个警察被控在逮捕一名犯人时误杀犯人五岁的儿子。记述同一件事的这两个新闻标题,使用语态不一样,前者主动,后者被动,所表达的语篇含义也就不一样。与例2)相比较,例1)指明了施动者“PC”,说明《东部日报》将报道重心放在PC上,暗示PC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太阳报》的报道中,施动者没有出现,使得责任者不明。而动作目标“the\nboy”位置脱离其常规句尾位置,被放到了句首,从而被突出和强调。 英语中另外一个极为突出的转换现象是动词名词化,如investigation,completion,interview等。这些词形式是名词,语义却是动态的,是一个小句、过程的压缩形式。如果我们把investigation这个名词展开、补全:“X(must)haveinvestigatedY”,我们会发现比较整个句子,名词化形式没有指明过程的参与者,无时间(没有时态)和情态(说话者对自己所讲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个人意愿等)的显示。因而动词名词化帮助遮掩了许多可以揭示意识形态范畴的语言信息。在进行批评分析时,必要时应该展开这些动词性名词,显示隐含其中的权势关系。 及物性系统、人际功能系统和转换是批评语言学家常用的批评工具。当然,分析工具不只限于此。凡是有利于批评分析的理论、模式,分析者都可以借来,使其功能主义化,用于揭示意识形态。 四 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已近十五年,其发展过程可分下面几个阶段。 1.萌芽(1976-1979)。批评语言学的萌芽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大规模开展的传媒研究。1976年,英国著名的格拉斯哥大学传媒小组发表了他们对电视新闻中所谓“坏新闻”的研究成果。他们经过系统分析发现,有利于政府和工业资本家的带偏见的报道大量存在于工业新闻中。随后,伯明翰大学的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开始了对新闻的批评分析(参看vanDijk,1985)。这些大众传播研究导致了批评语言学的诞生,因为新闻、大众传播、意识形态等都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对新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也可通过对这个物质外壳的分析来进行。1979年,RogerFowler等主编LanguageandControl一书出版。在该书的最后一章,Fowler和Kress提出了“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并对其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来源以及分析工具进行了阐述。该书的编辑和作者当时都是Fowler在东英吉利亚大学的同事。他们把研究集中到新闻的语言结构上,并强调自己研究的语言学基础。LanguageandControl的出版,标志着批评语言学的正式破土。 2.停滞(1979-1985)。在Languageand\nControl出版的后期,Fowler在东英吉利亚大学的同事纷纷离开,到别的大学或别的大陆任职。同事的分散,使得在一起合作不再成为可能,完善批评语言学模式的工作因此被耽搁了下来。Fowler本人也专注于文学批评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其间虽有一些批评语言学论文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出现(如1984年在荷兰乌得勒支举办的批判理论夏季学校),但总的来讲,没有专著出版,影响也不大。因此,1979年批评语言学登台以后,随即进入了停滞时期。 3.反思(1985-1987)。1985年,当时已迁居澳大利亚的GuntherKress在“Discourse,texts,readersandthepro-nucleararguments”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批评语言学向何处去的问题。LanguageandControl中收集的论文都是分析语言结构以证明语篇为意识形态所影响,其结论几乎都是批评分析证明了语篇并非意识形态真空。这样的分析和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和重复。正如Kress在该文中所说:“现在很多学者的工作都证明了意识形态在语言中的作用,并且至少部分地展示了他们对这种作用的理解。但是,一些问题,一些主要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在证明了语言和语篇是和语篇所由来的社会结构和过程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联之后,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对此,Kress提出了自己发展批评语言学的方案。他认为应该运用批评语言学的现有研究成果和模式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通过武装读者进行批评阅读,来使读者实现社会和政治上的自我解放,从而合理地改造社会。在Kress看来,批评语言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运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将重心转向读者,实现其社会意识形态批评的功能。此后不久,Fowler在1986年出版了LinguisticCriticism一书,1987年又发表了“Notesoncriticallinguistics”一文,重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回批评语言学。他认为Kress把批评语言学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读者的观点为批评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因而值得肯定,但他本人更强调批评语言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完善,以及对现有成果的巩固。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进行批评分析仍十分困难。就发表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不够多,而且分析所涉及的语篇种类也十分有限。除了1985年Chilton主编LanguageandtheNuclearArmsDebate:NukespeakToday一书之外,还无其它对同一体裁或同一题材作系统研究的专著,研究显得并不完整。论文中研究者对语言学方法和语篇的具体语境一带而过,很难让读者看懂。因此,在Fowler看来,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一个完整易学的标准工具体系,让更多的分析者掌握。 4.新发展(1988- )。两位批评语言学的创始人对现状和未来思索的不同结果,导致批评语言学两个方向的同时发展。Fowler积极巩固现有的理论和方法,于1991年出版了批评语言学对同一体裁的语篇进行研究的专著:LanguageintheNews:Discourse&IdeologyinthePress。Kress拓展外围,研究批评语言学的应用,与其它澳大利亚语言符号学家,如Threadgold等一起,把语言提高到社会符号的高度来研究,以发展批评阅读理论。自1988年起先后发表了SocialSemiotics(与Hodge合著),ReadingImages(1990,与vanLeeuwen合著)等书和“Structuresofvisualrepresentation”(1992,与vanLeeuwen合著)等文章。批评语言学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不仅在Fowler所在的英国和Kress工作过的澳大利亚,欧洲大陆荷兰、奥地利等也逐渐出现了一批批评语言学家。1991年伦敦Routledge出版由Kirsten\nMalmkjaer主编的《语言学大百科全书》,Fowler应邀为该书撰写了“批评语言学”一节。批评语言学得到语言学界的正式认可。 五 随着批评语言学声誉的扩大和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传播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加入对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Kress,Threadgold等)希望批评语言学走出其狭窄的语言结构分析,从简单跨学科发展至高度跨学科。与此同时,语言学学者们开始讨论批评语言学在语言学内部的地位问题。就在上文所提及的《语言学大百科全书》“语篇分析”这一节中,批评语言学被认为是语篇分析的一种,与篇章分析、会话分析二者并列。1993年4月,荷兰语言学家vanDijk在其主编的Discourse&Society杂志的“批评性语篇分析专刊”上发表“Principlesof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一文,把批评语言学作为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个部分来评述。批评语言学应属与自主语言学相并列的工具语言学下的一个独立分支。它和语篇分析是不同的。当今语篇的概念,越来越广,已经不再限于须以语言为中介。语篇分析从社会科学中广泛抽取各种模式,显得杂而有失控制,让语篇分析的初学者难以把握。批评语言学家并不反对跨学科研究意识形态的语篇再现,但批评语言学并非是任何对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所进行的研究(Fowler,1987:492)。它强调语言学的主体地位,强调对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掌握,因而其分析工具显得紧凑而易把握。诚然,以语言学为主来解释语言与权力分布,语言与社会控制的关系的确有其局限,但它确实为揭示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和新的研究视角。 批评语言学刚刚起步,其理论与方法仍需完善,其涉及的“意识形态”、功能等基本概念还在激烈争论之中。它目前只能说明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普遍存在,但对语篇在再现和加强意识形态操纵中作用的研究尚属初级阶段。虽然如此,批评语言学在主流语言学的统治中为语言研究和应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丰富语言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 参考文献 Chilton,P.(ed.)1985.LanguageandtheNuclearArmsDebate:NukespeakToday.London&Dover,N.H:FrancesPinter. Fairclough,N.1985.Criticalanddelcriptivegoalsindiscourseanalysis.JournalofPragmatics9.739-763. --1993.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andthemarketizationofpublicdiscourse:theuniversities.Discourse&Society4(2).133-168. Fouccult,M.1980.Power/Knowledge.NewYork:Pantheon. Fowler,R.etal.(eds.)1979.LanguageandControl.London:Routkedge. Fowler,R.1986.LinguisticCriticism.Oxford:OxfordUniv.Press. --1987.Notesoncriticallinguistics,inSteeleand\nTreadgold(eds),LanguageTopics:essaysinHonorofMichaelHalliday.Amsterdamand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 --1991a.Criticallinguistics.InMalmkjaer(ed.).TheLingnisticEncyclopedia.London:Routledge. --1991b.LanguageintheNews:DiscourseandIdeologyinthePress.London:Routlege. Halliday,M.A.K.1978.LanguageasSocialSemiotic.London:EdwardArnold. --1985.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London:EdwardAronld. Hodge,B.Kress,GandJones,G.1979.Theideologyofmanagement.InFowleretal(eds.)1979. Honneth,A.1991.TheCritiqueofPower:ReflectiveStagesinaCriticalSocialTheory.Trans.byKennethBaynes.Cambridge,M&London:TheMITPress. Kress,G.1985.Discourse,texts,readersandthepro-nucleararguments,inChilton(ed.). --1993.Againstarbitrariness:thesocialproductionofthesignasafoundationalissuei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Discourse&Society4(2).169-191. Malmkjaer,K.(ed.)1991.TheLinguisticEncyclopedia.London:Routledge. vanDijk,T.A.ed.1985.DiscourseandCommunication.Berlin&NewYork:WalterdeGruyter. --1993.Principlesof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Discourse&Society4(2).249-283. Wodak,R.(ed.)1989.Language,PowerandIdeology.Amsterdam:Benjamins.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与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06-1809:50作者简介:肖翠云(1978-),女,安徽宁国人,闽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语言学与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福建福州350008\n内容提要: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是文艺学和语言学共同介入的学术活动,它的形成与确立得益于两者的合力推动:文艺学界通过“为文艺正名”的方式,解除政治对文艺的束缚,探讨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并通过引进西方语言学批评,反思语言的性质,确立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语言学界通过“为语言正名”的方式,解除政治对语言的钳制,使语言回归正常的工具性能,并通过引进西方文化语言学理论,思考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确立语言的文化性。两者的协力合作使本体论语言观得以确立,使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促成了文学语言学批评在中国形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学界的贡献要大于语言学界,但语言学界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6年02期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语言学批评研究”(10CZW013)的阶段性成果。文学语言学批评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道独特风景,它以文学审美论和语言本体论为基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批评武器,关注文学及其语言形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倡导精细的科学化分析,是一种面向文学本体的批评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的影响下,这一独特的批评方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从文艺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来探讨它的形成与确立,展示两者在其中的贡献和作用。一、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1977~1984)1.文艺学界“为文艺正名”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是从文艺学界的“为文艺正名”开始的。这一正名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通过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反思与论争,破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解除文艺与政治之间的绑定关系,将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反映社会生活的自由。二是思考文艺的本质,探讨文艺的特殊规律和自身特色。一方面是“破”“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方面是“立”文艺自身特色,有“破”有“立”,“破”“立”结合,达到“为文艺正名”的目的。(1)反思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破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1977年,刚从“文革”阶级斗争中挣扎出来的文学批评不可能立即表现出决绝的姿态,在方式上必然带有文革文学批评模式的印记:一方面文学批评类的文章不多,而为数不多的文章在分析时仍以阶级立场为基础,执行的是“政治标准第一”甚至“唯一”的批评原则。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很少涉及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即使偶有涉及也大都放在文章的末尾或者几笔轻轻带过。1978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文学批评开始打破阶级分析的立场,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以“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为标题关键词的文章不断出现,这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原先“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准则开始向“艺术标准”转换。\n1979年之后,“艺术标准”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常规手段,“政治标准”逐渐淡出文学批评的视野。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与文艺学界对“工具说”的批驳、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思考密切相关。1979年1月《戏剧艺术》在显要位置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首次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提出质疑,拉开了批驳“工具说”的序幕。《上海文学》紧随其后,于1979年第4期发表“本刊评论员”署名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旗帜鲜明地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进行驳斥。文章公开宣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不科学的口号,这一口号至少有三大罪状:一是造成了文艺创作公式化和概念化;二是歪曲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三是狭隘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可见,作者之所以要为文艺正名,就是因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将文艺与政治等同起来,忽视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为文艺正名》的发表引发了学界激烈的争辩。反对《为文艺正名》、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进行辩护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工具说”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在阶级社会,文艺本就带有阶级性;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主要是脱离生活造成的,与“工具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因为“四人帮”利用过“工具说”就否定工具说;“工具说”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过作用,不能一棍子打死等。这些观点虽有某些合理处,但大多缺乏新意,论证较为粗糙,逻辑漏洞较多。比较而言,拥护《为文艺正名》、反对“工具说”的文章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而且质量上也更胜一筹。如周宗岱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吗?——驳吴世常同志》(《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邱明正《一个不精确的口号——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等文章认为“工具说”是一个不科学、不精确的口号,应当废除;易符原《认识生活——为文艺的普遍功能——兼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徐中玉《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上海文学》1979年第11期)等文章在驳斥“工具说”的基础上,提出必须重新定义文艺的本质。\n由于阶级斗争属于政治领域,因此,论辩双方在论争中实际上触及到了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从属说”)、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服务说”)的问题,“工具说”的论争上升为“从属说”、“服务说”的论争,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全国性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在讨论中,维护派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是常识,坚持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而否定派则认为文艺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同为经济基础服务,它们之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但由于都是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依据,有时不免断章取义,尤其是对“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异很大,“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1](P8)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重新界定,为其定下了基调。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半年之后,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再次强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作为回应,《人民日报》于1980年7月26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至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场波及甚广的大讨论解除了文艺与政治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绑定关系,将文艺从阶级斗争和狭隘的政治领域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自由。虽然讨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的工具属性和服务属性,但它能够走出政治对文艺的控制,探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方式、关注文艺作品的艺术特色,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学界进一步思索文艺的特殊规律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2)阐发文艺的特殊规律,确立文艺的自身特色\n新时期文艺学界在破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后,基本上采用的是“反映论”,认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特征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当时流行的两大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79年修订版)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都持这一观点。不过,在反对“工具说”的论争中,很多参与者也开始着手反思和纠正“形象反映论”。如《为文艺正名》的作者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显然比“形象反映”更能揭示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它强调文学作品的形象不是概念化、符号化形象,而是审美的、艺术的形象。这就突破了文革时期模式化、脸谱化的文学形象,为文学在塑造形象上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这是《正名》的贡献,但它未能进一步思考文学塑造审美形象的方式。有了审美形象,但若仍采用政治反映的方式,那么,审美形象也会板起政治的僵硬面孔。因此,刘再复于1980年提出的“美感的规律”就具有重要意义。刘再复将艺术活动视为“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2](P173)认为“就其具体的反映形式来说,它又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一特殊规律,就是美感的规律,即艺术必须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具备美的特征的作品,创造出作品后又必须给人以美感,然后经过美感作用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2](P188)并对艺术美感的本质特征——形象性和情感性进行论说,揭示了艺术活动的特殊性。刘再复对美感规律的探讨虽然是在真善美的统一中进行的,认为艺术应当具有认识价值和功利价值,但又强调这些价值“必须通过美的形态显示出来。如果艺术失去美的价值,艺术的其他价值也将全部丧失”,[2](P187)据此,他认为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应该从美学标准出发,而不应该从政治标准出发,这在当时是相当前卫且深刻的。对“美感的规律”进行补充拓展并加以论证的是童庆炳和钱中文。童庆炳于1984年提出“审美反映”的概念,认为“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是文学的基本特征”。[3](P65)童庆炳的“审美反映”不仅涉及文学反映的独特形式——艺术形象,更涉及文学反映的独特内容——具有审美属性的社会生活,从而将文学反映生活的独特性揭示出来。钱中文则细致区分了一般反映论与审美反映论的不同,认为“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命体的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是脱离现实的幻想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变化。”审美反映论由“心理层面、感性的认识层面、语言结构层面和实践功能层面”构成。[4](P9)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情感性;强调语言形式在审美反映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超越了一般的文学反映论,也丰富了文学表现论的内涵。可见,对文学反映论的探讨经历了从“形象反映”→“审美的艺术形象反映”→“美学的反映”→“审美反映”的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本质属性——审美性得以确立,虽然文学还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工具,但反映的对象和方式都是审美的,是遵循文学自身规律的,这是新时期初文艺学界“为文艺正名”的重要收获。除此之外,文艺学界在探索文艺自身特殊规律时,还试图从表现论和形式论角度来突破“形象反映”的局限。尽管表现论和形式论发出的声音很微弱,还不够明确和清晰,但也不可忽视。\n在反对“工具说”中,徐中玉提出了“文艺的本质是生活的形象表现”的观点,认为“只要生活里真实存在的,作者熟悉的,不管什么事情,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应该写。而且还应该允许作者觉得怎样写有益就怎样写。”[5](P78)“形象反映”与“形象表现”虽然仅一词之差,但内涵差别很大:“形象反映”强调的是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被动反映,忽视了文艺创作者在文艺反映生活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形象表现”强调的则是主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文艺反映生活不是被动地摄取,而是包含着创作主体对生活的选择、加工和整理。“作者觉得怎样写有益就怎样写”强调的正是文学书写的自由,是对“工具说”的彻底否定。所以,徐中玉对“工具说”的否定是通过解放文学创作主体、给予创作主体书写自由的权利而实现的。与徐中玉的“形象表现”说从文学创作的能动性和个体性角度来阐释文艺的特殊规律不同,刘纲纪则从艺术形式美的角度揭示了文艺的特殊价值。刘纲纪认为:“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形式更是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艺术家不同于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把某种思想表现在美的、动人的形式之中。”[6](P41)不仅如此,刘刚纪甚至将艺术形式置于思想内容之上,将艺术形式所体现出的审美价值视为文学的主要价值。在他眼中,“一部艺术作品,不论它的思想如何正确,如果形式拙劣不堪的话,作为艺术作品来看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相反,有些作品,即使没有什么重大的、深刻的思想内容,甚至还包含有某些不正确、不健康的内容,但只要它能把这种内容表现在优美的、新颖的、精致的艺术形式之中,那我们还得承认它是难得的真正的艺术作品。”[6](P42)这样的话语已经完全将作品的思想内容放置一边,完全从艺术形式出发,将形式美提升到不容否定的高度,这在1980年代确实是一个惊人之论,从中已然可以窥见80年代中期“文学形式论”的身影,所以刘锋杰将刘纲纪对形式美的论述称作是“新时期初中国文论中的形式论的初现”。[7](P347)童庆炳、钱中文等提出的“审美反映”、徐中玉提出的“形象表现”和刘纲纪提出的“艺术形式美”,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语义指向,那就是对文学艺术特殊规律的探寻。这个最初的探寻使文学批评摆脱了“政治标准第一”甚至“唯一”的束缚,逐渐向艺术标准倾斜,并最终实现了艺术标准的主导地位,从而为80年代中期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出现和文学语言学批评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语言学界“为语言正名”在文艺学界忙于“为文艺正名”的同时,语言学界也力争“为语言正名”。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与语言休戚相关,语言观念必然影响文学观念。所以,新时期初文艺学界开展的“文学工具论”论争与语言学界对“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质疑紧密相连,相辅相成。\n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使社会各领域都充满了反思和质疑的声音。语言学界也开始重新思考语言的本质问题,对文革时期“语言的阶级性”及“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观点提出质疑。这种质疑实际上是70年代末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进行驳斥的一种深化。“四人帮”之所以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因为在阶级社会“语言具有阶级性”、“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一定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破除“语言具有阶级性”的迷信,还语言的社会性本质,是文学创作常态化的基础。徐荣强率先批判了文革时期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语言的错误做法,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来指导语言研究;并认为应该借鉴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观念建立符号语言学体系。[8](P86~89)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肯定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语言学观念,同时也为文学语言的形式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对“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批判得比较彻底的是李行健的《关于语言社会本质的一个问题——“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质疑》。文章认为新时期虽然某些报刊已经痛击“语言具有阶级性”的谬论,但力度和深度还不够,还未触及“语言具有阶级性”这一谬论的基础——即“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因为,“阶级斗争工具论”是“语言无阶级性”到“语言有阶级性”的桥梁,因此需要对“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进行彻底清理,以正本清源。[9](P62~66)文章从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特点和语言自身的特点两大方面论证了语言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交际的工具,社会性、全民性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虽然将“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原为“语言是人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并没有改变语言的工具属性,但对新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从根本上斩断了阶级分析对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干预和钳制,使两者获得了学科的独立和自由。语言学界在批判旧的语言观念的同时,也在努力探求新的语言理论。胡明扬有感于我国语言科学的落后,大声呼吁“广泛而又认真地学习国外语言科学中一切先进的成就”,并认为这种学习和借鉴“恐怕是我们的语言科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0](P18)在这条必由之路上,语言学界发现了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并积极地将其引介到中国来。1980年11月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是语言学界的高名凯先生。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国内影响甚大,成为学界了解和研究现代语言学理论的重要资料。\n虽然语言学界的“为语言正名”运动并未在文艺学界激起有力的反响,但文艺学界的“为文艺正名”本身就内蕴着对语言工具性的反思。这是因为文艺学界也在积极引进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将其作为理论基础,建构新的语言观念,而他们对索绪尔的介绍和研究大多建基于高名凯翻译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是语言学界和文艺学界在语言问题上的一个交汇点,也是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个证明。语言学界和文艺学界不约而同地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作为共同的开发领域,显示出两者在语言观念上的趋同和转变,由语言的工具性向语言的符号性、结构性转变,从而为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因为,“通过为文艺正名,再到为语言正名,既蕴含了强化形式批评的可能性,也蕴含了建构语言学批评的可能性,为文学批评将语言形式作为批评的基本任务之一,提供了理论的空间与依据。”[11](P4)二、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确立(1985~1989)1.文艺学界:外在引进与内在反思1985年,刘再复在总结我国近年来文学研究的趋向时指出,其中一个趋向就是“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12](P134)这一转移与80年代中期我国对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引进密切相关。(1)引进西方语言学批评西方语言学批评主要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及叙事学批评构成,这三大批评流派尽管所处的国度不同,发生的时间先后不一,理论的侧重点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理论倾向是一致的:第一,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自足体,与创作者和接受者无关,也与外在的政治、历史、宗教等无关,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本身(即“文学性”)。第二,认为语言形式在文学中具有本体论价值,文学批评应该专注于文本自身,充分研究其表层的语音构成、深层的语法结构以及文本所包含的复杂语义。第三,主张文学批评应该采取精细的、科学化的方式,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排除作者因素和读者因素的影响,努力追求批评的纯正与客观。西方语言学批评的这些观点虽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它对文学语言审美价值的重视、对科学化文学批评方法的实践以及对文学批评向文本自身转移的推动,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中国学者打开了一扇崭新的批评视窗,而且促使他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学批评的弊端、反思语言的性质以及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2)反思语言的性质和功能\n经过新时期初对“文学和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批驳,以及对文艺自身特殊规律的探寻,人们意识到文学及语言的审美属性和审美价值。文学语言审美价值的确认是语言观念由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的关键,因为“语言对于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生成又必须通过文学语言本体的审美品性才能实现”。[13](P77)只有肯定和承认文学语言的审美本质,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语言对文学作品的生成功能,才能确立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因此,从整体上看,新时期对语言性质的探索经历了从工具论→审美论→本体论的发展阶段:新时期初的目标集中于前半段,由工具论向审美论转变;新时期中后期的目标集中于后半段,由审美论向本体论转变,审美论成为连接前后期的中介和桥梁。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语言是怎样成为文学的本体以及文学研究的中心的呢?其中既有文学创作界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语言创新实验的推动,也有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对语言问题的多方深度思考,主要表现在:第一,继续对工具论语言观展开批评,探索语言的多重性。1987年唐跃、谭学纯发表《语言功能:表现+呈现+发现》一文,对传统的“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工具”理论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文学语言不是载体而是本体,不仅具有表现功能,还具有呈现和发现功能,这是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文学语言论,它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用途,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不同的功能。在作者的创作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表现作者的意图,因之具有表现功能;在文本的实现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呈现文本的意义,因之具有呈现功能;在读者的接受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发现读者的意味,因之具有发现功能。”[14](P33)谭学纯、唐跃并没有否认文学语言具有表现功能,不过这个表现功能不是工具意义上的,而是本体意义上,它具有艺术化价值、风格化价值和内容化价值。[15](P59~66)由于超越了工具论的狭窄视野,文学语言自身多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得以显现。1988年《文学评论》第1期以“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为主题,推出了一组笔谈,其中很多学者对语言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探讨。如伍晓明认为:关于语言有三个命题,语言是表现,语言是创造,语言是模式。第一个命题是一种工具论语言观,即认为语言仅仅是“描写”现实或“表现”思想的工具、手段,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第二个命题其实是对第一个命题的否定:现实不是被语言所反映,而是被语言所创造的。文学语言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创造的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是,创造不是任意的。“语言是模式”强调的就是作为先在系统的“语言”(包括一切类语言和准语言的符号系统)对于作为创造活动的“言语”的规定作用和制约作用。因此,伍晓明认为“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语言角度应该以语言作为模式来研究语言。”[16](P61)与伍晓明一样,程文超也把语言作为结构或模式来看待。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是人的特征。……语言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结构、思维方式、思维模式。这种制约是内在的。”[17](P57)语言作为模式或结构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观,是对工具论语言观的彻底否定。\n第二,探讨语言的文学性和文学的语言性。语言的文学性指的是语言的艺术性或审美性,这一点在新时期初探索文学艺术自身的特殊规律时已有涉及,“审美反映论”和“形式美”都指出文学表现形式的审美性特征,但没有明确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审美性的语言。80年代中期随着“语言热”和“美学热”的兴起,文学语言的审美本质得到了确认。如向新阳认为:“构成文学作品的文学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它是一种个性得到高度尊重、情感享受充分自由、主观被尽量物化了的语言,是一种美的语言。”[18](P79)承认文学语言的审美本质是迈向语言本体论的关键,因为审美性指向的是文学语言自身,它将文学看作是一个美的叙述,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不是将文学看作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思想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研究专注于文学本身。但是仅仅探讨语言的文学性还不够,还必须探讨文学的语言性,只有将文学的审美性落实到语言上,才能真正体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内涵。新时期对文学的语言性的探讨正是从反思“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经典命题开始的。1985年,黄子平率先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行重新审读,对“得意忘言”式的文学研究进行批评。他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语言被当作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放到‘最后’来说,更多的时候连这‘最后’也没有。”黄子平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把诗(文学作品)看作自足的符号体系。诗的审美价值是以其自身的语言结构来实现的。”基于此,他提出“文学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的文学性’,更注重研究‘文学的语言性’。”[19](P88)(着重号为原文所有)黄子平对“得意忘言”式批评模式的批判以及对“文学的语言性”的强调对中国文学批评向“语言”转向,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文学来说,语言不仅是构成文学的材料,而且对文学产生影响和制约;语言不仅是文学传达内容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构成文学审美效果的本质内容。[20](P78)文学的审美效果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不仅将文学所要表达的内容用符号呈现出来,而且还参与了文学审美性的建构,语言在文学中具有本体论价值。因此,从探讨语言的文学性到肯定文学的语言性,为语言本体论的出场积蓄了巨大能量,语言本体论呼之欲出。\n第三,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观点,确立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1987年,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鲜明提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的观点,他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21](P1~2)如果说汪曾祺是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论证语言之于文学的本体价值,那么,李劼则站在理论高度阐发了文学语言的本体意味。李劼指出:“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22](P79)李劼把文学的生成看作是语言的生成,离开语言,文学无法成为一个自足体,语言的本体意味由此产生。新时期后期文艺学界通过外在引进和内在反思,终于把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文学语言,把文学看作是一个由语言建构的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语言构成了文学的本质存在,确立了本体论的文学语言观,从而为文学语言学批评的确立夯筑了坚固的基石。1986年,唐跃、谭学纯呼吁“寄希望于语言学文学批评”,[23]正式提出建立语言学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构想,这一理论构想随着文艺学界对语言的关注和反思、对本体论语言观的阐释和建构,以及文学批评向作品本体的回归而成为现实,于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语言学批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也有学者敏锐地发现虽然语言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突破口,“但是,当我们试图通过语言学去深化文学研究时,就发现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首先我们会感到自己的家产太贫匮。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汉语,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严格来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在哲学和本体意义上的语言学理论。”[24](P65)与此相对照,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有深厚的语言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作为基础,从事语言学批评的学者也大多具备良好的语言学素养,拥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储备,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主要成员都兼有语言学家的身份,因此,他们在进行语言学批评时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语言与文学之间。而中国文艺学界从事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学者大多不具备语言学的知识背景,对语言学知识较为隔膜或一知半解,在进行语言学批评时常常因语言学理论的匮乏而显得捉襟见肘。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不在于语言学界的过错,而在于文艺学界自身拘束于学科之界,未能及时关注和汲取语言学的新成果,没有与语言学界形成有效的互动。其实,在文艺学界致力于建构本体论语言观时,语言学界也在探索语言的本体性,不过两者的方式不同:文艺学界对语言本体性的探索是以语言审美性为中介,语言学界则以语言文化性为中介。2.语言学界:探索语言的文化性\n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本身就是文化,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同一性,不同民族的语言内蕴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与印欧语言拥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受各种语法形式规则的制约不同,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较少受形式规则的约束,常常根据逻辑事理和主体选择来组词成句,显得灵活、自由,充满人文气息。但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以《马氏文通》为先导,“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文感受。它使中国语言学在精密化、形式化、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大步,然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这是‘五四’以来文化断层在汉语研究领域的又一典型表现。”[25](P97)痛感于当前汉语研究中对汉语人文性的漠视,语言学家申小龙力倡“文化语言学”,认为汉语不仅仅是传情达意的工具,更是汉文学、汉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内在形式。“文化语言学”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把汉语从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中解救出来,揭示汉语本身所含蕴的文化内质,建构属于汉语自身的中国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语言本体论。在申小龙看来,“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不仅对于思维的表达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媒介,而且它就是思维过程本身的一部分。这表明语言并非只是消极地表达或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它还是世界的条理化、组织化、结构化与有序化的呈现。没有这种呈现,世界对于人就不存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世界观深埋在语言结构之中,语言分析成为人类文化研究的深层结构分析。”[26](P128)正是秉持着语言本体论的观念,申小龙将汉语置放于中国文化、民族思维的宏阔背景中,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同构关系,揭示汉语及汉文化的独特性,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文化学视角。语言与文化的同构关系表明,以汉语作为本体的中国文学必然呈现出与西方文学不同的文化内涵。那么,文学研究将如何以语言为观照点来开掘中国文学的文化底蕴,把语言分析与文化阐释紧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新时期,文学创作界的“文化寻根小说”是文学对文化领域的一次探索和开掘,文学批评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阐述其中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但较少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切入,表现出文化阐释有余、语言分析不足的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艺学研究缺少语言学的理论视界。\n综上而言,80年代中后期,文艺学界在对语言工具性的反拨中发现语言的文学性(审美性),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美的叙述;语言学界在对语言工具性的反拨中发现语言的文化性,把语言看作是文化本身,两者都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语言本身,使语言自身的价值得以呈现,最终指向语言本体论。语言本体论的确立不仅是文化语言学建立的基础,更是文学语言学批评成立的基石。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学界和语言学界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交流与合作,但间接影响和隐性交流还是存在的,表现在:第一,两者的语言本体论思想都来源于西方的语言哲学。无论是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坦的“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还是洪堡特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它们都在传达着“语言是人类本体”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为国内文艺学界和语言学界重新认识和思考语言的性质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有些学者兼具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双重学科身份,能够对文学语言作多维观照。如在学科归属上,谭学纯属于语言学科,王一川属于文艺学科,但他们在80年代中后期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没有局限于自身的学科视野,而是打破学科界限,向相关学科延伸,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态势:谭学纯由语言学向文艺学延伸,王一川则由文艺学向语言学延伸,两者在语言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双重视域中展开文学语言研究,为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带来了丰富启示。[27](P54~58)这种跨学科研究正是语言学与文艺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例证。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是文艺学和语言学共同介入的学术活动,两者几乎同时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语言问题,探讨语言自身的价值,虽然在行进途中,文艺学界的参与度更多,贡献的力量更大(这与文学语言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活动有关),但语言学界的努力与付出也不可漠视。它对“语言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的批判、对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理论以及西方文化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引进和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艺学界的语言反思提供了理论支撑。虽然从表面上看,文艺学界和语言学界两者似乎各行其事,较少开展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但两者的关注对象以及理论渊源几乎相同。这也说明,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与确立离不开语言学界的参与,它是两者合力推动的结果。原文参考文献:[1]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概说[J].江西社会科学,2005(5).[2]刘再复.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1980(6).[3]童庆炳.文学概论[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4.[4]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也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J].文艺理论研究,1986(4).[5]徐中玉.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J].上海文学,1979(11).[6]刘纲纪.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J].文学评论,1980(2).[7]刘锋杰,薛雯,尹传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徐荣强.语言研究必须解放思想[J].江汉论坛,1980(1).\n[9]李行健.关于语言社会本质的一个问题——“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质疑[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1(5).[10]胡明扬.语言科学的现代化——学习和借鉴[J].国外语言学,1980(1).[11]肖翠云.从文学的政治性到文学的语言性——新时期文学批评去政治化策略之一[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4).[12]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J].读书,1985(2).[13]阳友权.文学语言的本体论思辨[J].求索,1990(2).[14]唐跃,谭学纯.语言功能:表现+呈现+发现——对“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工具”质疑[J].文艺争鸣,1987(5).[15]唐跃,谭学纯.语言表现:创造性外化活动[J].文学自由谈,1988(1).[16]伍晓明.表现·创造·模式[J].文学评论,1988(1).[17]程文超.深入理解语言[J].文学评论,1988(1).[18]向新阳.略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J].武汉大学学报,1987(3).[19]黄子平.得意莫忘言[J].上海文学,1985(11).[20]寇显.试论文学的语言性[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2).[21]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A].汪曾祺文集·文论卷[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22]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J].上海文学,1987(3).[23]唐跃,谭学纯.寄希望于语言学文学批评[N].文论报,1986~11~01.[24]潘凯雄,贺绍俊.困难·分化·综合[J].文学评论,1988(1).[25]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26]申小龙.语言的人性和人的语言性——论人类语言符号的文化视界[J].学术交流,1989(4).(原文出处:《中国文学研究》(长沙)2015年第20153期第17-23页)查看更多